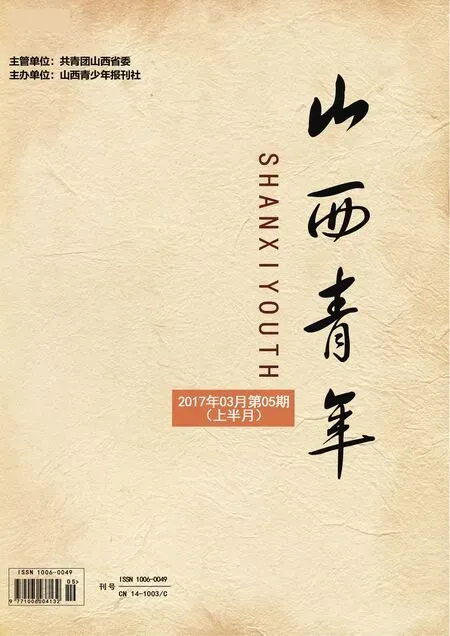對晚清時期外交新思考
劉珊珊
天津商業大學,天津 300134
對晚清時期外交新思考
劉珊珊*
天津商業大學,天津 300134
晚清時期的外交主旋律明顯,那便是一味求和,喪權辱國,而外交新思想則為中國晚清外交打開了一路分支,盡管并未給晚清的中國帶離屈辱的道路。外交家的個人外交風格并不能改變整體的外交局勢,國內矛盾、國際局勢等等均在左右著外交走向。但是,我們也可以從中看到,晚清時期的這種新思想是有利于改變當時復雜多變的外交環境,在某種程度上維護了晚清政府形象。這種新舊的碰撞也有利于拓寬中國的外交視野,為當時及以后的外交研究提供一定的經驗與教訓。
晚清外交;新思考;東西方碰撞;晚清外交家
縱觀中國的外交史,晚清時期的外交可謂是最黑暗的一筆,壓迫式的對外交往主導前后近100年的對外活動。長久以來閉關鎖國的思想封閉了中國的對外交往,而兩次鴉片戰爭也使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一蹶不振,因此,“妥協”外交也就成為了當時最適合的外交方式。然而,曾國藩辦理天津教案,曾紀澤伊利交涉,左宗棠收復新疆,一小部分活躍在國際舞臺上的中國外交家們,用自己獨特的外交方式維護國家尊嚴,爭取國家利益。
一、國際形勢下的“妥協”外交
在晚清時期,中國的對外交往活動更多的是被動的,這一情況也是中國“妥協”外交的最根本原因。以英國為例,急于打開中國市場的英國兩次派出訪華使團,但中國長期閉關鎖國政策使得急功近利的英國人不得不采取另外的方式逼迫中國妥協,鴉片正是一利器。兩次鴉片戰爭,反映了東西方兩種國際關系體系的碰撞。歐洲列強為了打通中外貿易往來渠道,獲取巨大的經濟利益,試圖將一系列政策強加于中國;而晚清政府卻并不在乎貿易往來,以天朝上國自居,并要求西方人遵守朝貢體制的規矩。
從上述表述中可以看到,晚清政府的政策直接影響著中國的對外交往活動,所以晚清時期的外交所呈現的這種局面,事實上也是可以預見的。中國,華夏文明和封貢體系主導,與周邊國家接觸甚少。這種局面直到19世紀資本主義經濟在全球興起時才被迫打破。因此,“妥協”外交是無法避免的趨勢,晚清外交家的新思想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孕育成熟的。
二、晚清外交新思想——“爭取”外交
晚清政府的腐敗與無能,使得中國外交近代化的進程還未起步就停滯不前,但一批自學成才,立志于改變中國現狀的外交人才肩負起了改善中國外交困境的重擔,正是他們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外交思想,并成功地運用到對外交往中,其產生的深遠影響不可預估。
(一)外交政策服務于國家,國家利益高于一切
對于晚清政府而言,個人利益居首,而領土最末。但近代外交思想的核心卻是截然相反,即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是近代外交的宗旨和原則。近代外交家們正是秉持著這一核心原則,在國際舞臺上斡旋談判。國家和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甚至超越個人的生命。但是,這種“爭取”的外交理念卻與外國在華利益發生了沖突,從而引起了日益加劇的侵略。但秉持新思想的外交家們不懼艱難,通過分析當時的世界及國內外的形勢,采取了種種務實的應對策略,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的目標,同時體現了中國外交官“身臨危難,無一失體”的風范。
(二)靈活多變的外交新理念
天朝上國的思想禁錮了中國外交思想的發展,而新外交思想則恰恰改變了這一觀點,采取靈活、務實的多方位對外交往方式,維護國家與民族利益。
1.利用西方外交準則進行對外交往
近代西方外交慣例主要體現在國際法中。國際法是近代西方國家處理相互之間外交關系的重要準則和規范國際社會關系和國際行為的重要機制之一。正是基于此,中國的外交新思想就要融于其中,而不是一味的只遵照自己的意愿,要將中西雙方均處于平等地位才能更好的進行對外交往。例如,晚清時期外交家曾紀澤在《中俄伊犁條約》談判正是成功運用國際公法,才得以維護了國家主權和民族權益。
2.利用談判斡旋,爭取和平外交
晚清以來,外國列強對于中國的對外交往基本采用的強制乃至暴力的手段,從屢次簽署的不平等條約便能看出一二。但是,新外交思想從維護中華民族的尊嚴和國家主權獨立的立場出發,對西方列強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及其所攫取的侵略特權進行了揭露和批判,提出了有關修約、廢約和取消列強在華某些特權的主張,竭盡全力的與西方列強斡旋談判,努力地為晚清時期的中國爭取相對和平的環境進行對外交往。
三、晚清時期“爭取”外交的局限性
“爭取”外交新思想的傳播與應用雖然給中國對外交往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局面,是符合歷史潮流的對外交往方式,但是在晚清這一特定的歷史時期下,仍然未能得到晚清政府的認可,也未能使得中國免于西方堅船利炮的攻擊,因此,“爭取”外交在理論上看是成功的,可是在實踐上看卻是失敗的。
首先,中國延續2000多年的傳統思想已經根深蒂固在每個人的內心,即便是秉持新思想的外交家們也不外如此。“爭取”外交只能進行一番掙扎,卻無法改變其軌跡。其次,國際形勢的束縛使得更合適的外交理念無法施展,即弱國無外交。當時的中國近貧極弱的現象已經無力回天。縱然外交官們有天大的本事,卻也是無法逆歷史潮流而為之的。最后,是主權與王權概念的混淆。這與傳統思想的禁錮是分不開的。一國的對外交往是要求對一國的主權負責,但是在中國,王權向來是一國主權的象征,因此導致在外交理念上存在偏頗。
綜上所述,晚清外交確實取得了某種成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國的國際聲譽。即便是由于時代和階級的局限,這些外交思想與實踐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局限與不足,外交思想還夠不上完全意義的近代外交思想,但它對中國外交的近代化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在中國近代外交史上仍具有重要地位。
[1]熊志勇等.中國近現代外交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2]石原華.中華民國外交史[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4.
[3]張立真.曾紀澤本傳[M].沈陽:遼寧古籍出版社,1997.
[4]吳寶曉.初出國門——中國早期外交官在英國和美國的經歷[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
[5]楊公素.晚清外交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
[6][美]費正清.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M].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室.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1985.
[7]蔣躍波.曾紀澤的外交原則與策略[J].淮北煤炭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4).
[8]李開盛,吳昊,金欣.晚清外交中的尚爭思想及其實踐[J].國際關系學院學報,2012(6).
劉珊珊(1992-),女,漢族,北京人,天津商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中國近現代史基本問題研究專業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近現代史政治發展。
K
A
1006-0049-(2017)05-014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