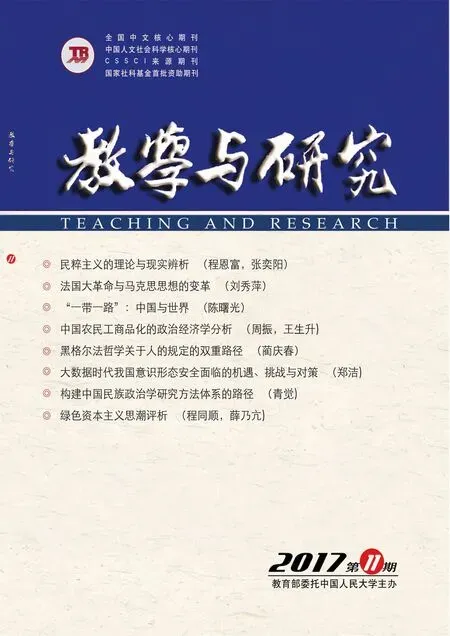文化與建設(shè)和平:文化分層的視角*
文化與建設(shè)和平:文化分層的視角*
王學(xué)軍
文化;世界觀;政治規(guī)范;沖突解決;建設(shè)和平
理解文化對(duì)建設(shè)和平的影響,需要對(duì)文化概念進(jìn)行分層。作為世界觀的文化影響著和平的基本概念和建設(shè)和平的根本方式;作為政治規(guī)范的文化決定了具體以何種政治組織形式和路徑來(lái)重構(gòu)國(guó)內(nèi)秩序與和平;作為社會(huì)習(xí)俗的文化則在微觀互動(dòng)層次上影響著宏觀層次總體和平進(jìn)程的成敗。忽略任何層次文化的作用,對(duì)脆弱國(guó)家國(guó)內(nèi)沖突解決與建設(shè)和平都是淺薄和危險(xiǎn)的,準(zhǔn)確理解文化因素的作用對(duì)國(guó)際和平行動(dòng)具有重要戰(zhàn)略價(jià)值與政策意義。
后冷戰(zhàn)時(shí)期,脆弱國(guó)家或失敗國(guó)家及其引發(fā)的國(guó)內(nèi)沖突構(gòu)成了國(guó)際和平與安全的重要威脅。針對(duì)這類國(guó)家的維持和平與建設(shè)和平行動(dòng)成為全球安全治理的一項(xiàng)重要內(nèi)容。如何通過建設(shè)和平在脆弱國(guó)家實(shí)現(xiàn)可持續(xù)和平,成為國(guó)際社會(huì)面臨的一項(xiàng)基本安全治理問題。在探討這一問題時(shí),文化的地位與作用成為研究者不得不思考的重要學(xué)術(shù)命題。本文將在研究述評(píng)基礎(chǔ)上,系統(tǒng)深入地探究文化因素在當(dāng)今脆弱國(guó)家國(guó)內(nèi)沖突解決與建設(shè)和平中的基本作用。
一、國(guó)內(nèi)外研究述評(píng)
自中國(guó)參與國(guó)際維和行動(dòng)以來(lái),官方一直強(qiáng)調(diào)不同國(guó)家、不同文明的社會(huì)文化背景對(duì)當(dāng)事國(guó)國(guó)內(nèi)沖突解決與建設(shè)和平具有重要意義,但國(guó)內(nèi)學(xué)術(shù)界對(duì)文化究竟如何影響維和建和的探討卻非常有限。國(guó)內(nèi)關(guān)于維和的研究大致沿著聯(lián)合國(guó)及地區(qū)維和機(jī)制的發(fā)展變化、中國(guó)與國(guó)際維和的關(guān)系、其他國(guó)家的維和政策等三個(gè)方向展開。僅有少數(shù)學(xué)者在討論中國(guó)參與國(guó)際維和時(shí)涉及中國(guó)與西方維和建和的文化理念差異。[1]還有個(gè)別學(xué)者對(duì)聯(lián)合國(guó)維和任務(wù)區(qū)的文化差異問題做過初步的探討。[2]
國(guó)外學(xué)術(shù)界對(duì)此問題研究頗豐,主要表現(xiàn)在沖突解決領(lǐng)域的研究。西方?jīng)_突解決研究者對(duì)文化與沖突解決的關(guān)系給出了三種不同的回答。一是文化無(wú)用論,認(rèn)為文化變量與沖突解決沒有相關(guān)性,其代表人物是伯頓(John Burton)、扎特曼(Wiliam Zartman)。伯頓認(rèn)為,沖突的根源在于社會(huì)和政治制度未能滿足人們對(duì)承認(rèn)、安全、發(fā)展等必要的本體性需求。[3]在伯頓的模式中,文化僅在很淺的價(jià)值層次上發(fā)揮作用,它并不影響沖突解決的根本規(guī)則即應(yīng)對(duì)人根本層次的需求。有學(xué)者指出,伯頓的理論將文化的作用極度邊緣化,像以權(quán)力為中心的現(xiàn)實(shí)主義范式一樣極度忽略或壓制了文化因素。[4](P89-90)扎特曼主要關(guān)注的是如何將沖突各方的非理性行為轉(zhuǎn)變?yōu)楦永硇缘男袨椤K州p視文化在解決沖突的國(guó)際談判中的作用。他認(rèn)為,談判是一個(gè)普適性的進(jìn)程,文化差異不過是語(yǔ)言與風(fēng)格的差異,無(wú)論如何都有一個(gè)通適性的外交文化,而文化差異在權(quán)力考慮面前作用微乎其微。[5](P266)二是文化變量論,它承認(rèn)文化的重要性,但僅把文化看作是眾多變量之一,沒有重要到需要改變通用性方法的地步。古里弗(Gulliver)最早對(duì)跨文化談判分析認(rèn)為,在談判和對(duì)話中,雙方都不得不盡力互相學(xué)習(xí)對(duì)方的語(yǔ)言和文化。[6]庫(kù)亨(Cohen)在研究埃及與以色列關(guān)系時(shí)認(rèn)為,文化誤解和隔閡導(dǎo)致了一種類似“聾子之間的對(duì)話”。[7]三是文化決定論,認(rèn)為文化對(duì)沖突解決具有非常關(guān)鍵的意義,乃至于決定著沖突解決最終的成敗。持這一觀點(diǎn)的主要有三個(gè)代表人物。首先,艾烏路齊(Avruch)對(duì)忽視文化的沖突解決方法進(jìn)行了全面而有力的批評(píng);[4](P42)其次,李德拉齊(Lederach)的沖突轉(zhuǎn)型理論將沖突轉(zhuǎn)型定義為一種文化敏感型的誘導(dǎo)方法,而不是外部輸入型的開處方式方法;[8]再次,加爾通(Galtung)將西方的思維方式與東方和印度的宇宙論和傳統(tǒng)文化進(jìn)行了比較,指出了前者的缺陷與不足。[9](P291-305)
文化無(wú)用論雖然抓住了沖突的本體性根源,但卻忽略了不同文化與文明背景下人們對(duì)這些本體性需求的理解是存在差異的,也就是說(shuō),文化可以通過影響對(duì)承認(rèn)、安全、發(fā)展等所謂本體性需求的認(rèn)知,從而影響沖突的發(fā)生與解決。文化變量論僅僅將文化理解為影響沖突解決的眾多變量之一,而忽略了文化更為基礎(chǔ)性的作用,其原因在于其對(duì)文化的理解僅僅停留于語(yǔ)言、習(xí)俗的層次。文化重要論抓住了文化作為沖突解決的具體發(fā)生環(huán)境的基礎(chǔ)性作用,但也有兩點(diǎn)不足,一是矯枉過正,過于貶低西方文化而推崇東方文化,二是忽略了文化不僅作為環(huán)境因素發(fā)揮結(jié)構(gòu)性作用,而且在互動(dòng)進(jìn)程中也是不可忽視的變量之一。
以上三種論點(diǎn)還存在一個(gè)共同的缺陷,它們都沒有對(duì)文化做系統(tǒng)和明確的界定。本文的文化概念是指沖突后建設(shè)和平所發(fā)生的社會(huì)歷史環(huán)境構(gòu)成的文化,它既包括沖突后重建所發(fā)生的東道主國(guó)家和社會(huì)的文明與文化,也包括參與沖突后建設(shè)和平的外部行為體所體現(xiàn)的文明與文化。影響沖突解決與建設(shè)和平的文化可以進(jìn)一步分層,大致分類為哲學(xué)視野下的文化即作為世界觀的文化、政治學(xué)視野下的文化即作為政治規(guī)范的文化和人類學(xué)視野下的文化即作為社會(huì)習(xí)俗的文化。而現(xiàn)有的三種論點(diǎn)僅僅是在某種意義層次上使用文化概念,因而未能對(duì)文化與沖突解決及建設(shè)和平的關(guān)系形成系統(tǒng)的、整體性的理解和把握。文化無(wú)用論和文化變量論大致都是在宗教和社會(huì)習(xí)俗意義上使用文化這一概念。持文化重要論的艾烏路齊區(qū)分了主位視角和客位視角,從人類學(xué)意義上使用文化概念。李德拉齊某種程度上是在政治規(guī)范和人類學(xué)交融視角下使用文化概念,加爾通大致是在不同文明的宇宙論概念上使用文化概念。這就使他們的觀點(diǎn)或者完全錯(cuò)誤,或者有失偏頗。事實(shí)上,我們需要從各個(gè)層次來(lái)進(jìn)行系統(tǒng)考察,才能較為完整地理解文化對(duì)弱國(guó)國(guó)內(nèi)沖突解決與建設(shè)和平的作用。
下文將從世界觀、政治規(guī)范和社會(huì)習(xí)俗等三個(gè)層次對(duì)文化在脆弱國(guó)家沖突解決與和平建設(shè)中的作用進(jìn)行具體討論。最后簡(jiǎn)要討論了在弱國(guó)沖突治理與維和建和實(shí)踐中忽略文化的危害以及關(guān)注文化因素可能帶來(lái)的戰(zhàn)略和政策意義。
二、作為世界觀的文化與建設(shè)和平
世界觀是“人們對(duì)于世界總體的看法,包括人對(duì)自身在世界整體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看法,亦稱宇宙觀,它是自然觀、社會(huì)歷史觀、倫理觀、審美觀、科學(xué)觀等的總和。哲學(xué)是它的表現(xiàn)形式”。[10](P810)在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中,世界觀相當(dāng)于宇宙論。它是文明與文化的核心構(gòu)成部分。世界觀相對(duì)于文明,猶如個(gè)性相對(duì)于個(gè)人,一旦個(gè)性牢固形成后,其基本特征傾向于是每天、每月、每年、終生都按某一固定節(jié)奏擺動(dòng)。[11](P311)不同世界觀對(duì)世界的基本假定不同,從而影響對(duì)和平與沖突的基本理念,進(jìn)而從根本上影響沖突治理的方式。
不同文明模式下的文化傳統(tǒng)對(duì)世界的基本哲學(xué)假定不同,因而其世界觀也存在差異。加爾通從人與自然、人與社會(huì)、人與世界、人與自我、人與超人、認(rèn)識(shí)論等七個(gè)維度討論了六種不同文明的世界觀之差異,以及不同文明的文化傳統(tǒng)對(duì)和平與沖突的不同哲學(xué)理念。他認(rèn)為,西方世界觀包含有二元對(duì)立和線性發(fā)展兩個(gè)基本假定,并奉行反整體主義和反辯證法的認(rèn)識(shí)論。世界和社會(huì)被劃分為中心、邊緣和邪惡三個(gè)部分。在此世界觀下,和平即意味著消滅異己和差異。[11](P325)民主和平論就帶有這種目的論和消滅差異的傾向。[12](P181-211)印度教文明信奉社會(huì)和世界的輪回,人與社會(huì)的發(fā)展有四個(gè)階段,即法(道德責(zé)任)、利(財(cái)富與生計(jì))、伽摩(幸福)和解脫(解放)。阻礙解脫的只有自我而不是邪惡的他者,因而和平基本在于自己。印度圣雄甘地倡導(dǎo)的非暴力不合作的和平解放思想即反映了這種和平哲學(xué)。中國(guó)文化傳統(tǒng)信奉“多元共存”與“和合主義”的世界觀,中國(guó)在當(dāng)代弱國(guó)沖突治理中所倡導(dǎo)的“自主發(fā)展和平”理念[13]則反映了這種哲學(xué)文化理念。阿爾伯特討論了西方與非洲關(guān)于和平的不同哲學(xué)理解。他指出,西方的和平概念十分強(qiáng)調(diào)繁榮與秩序,但非洲的和平概念是基于道德與秩序,非洲和平的根基可能在于其文化價(jià)值、信念、規(guī)范和社會(huì)角色的期待。[14](P31-45)
不同世界觀對(duì)和平的不同理解對(duì)建設(shè)和平的根本路徑產(chǎn)生了深刻影響。在西方文明中,“和平”同條約相聯(lián)系,即“條約必須被遵守”。這里隱含的假定是,和平是一種契約性的、有意識(shí)的、彼此同意的相互關(guān)系。[11](P328)因而在西方世界觀的和平概念里,解決沖突、建設(shè)和平的根本路徑在于制訂和遵守契約。當(dāng)前西方主導(dǎo)的敦促后沖突國(guó)家簽訂停火協(xié)議、制訂時(shí)間表并按照時(shí)間表制訂新憲法、舉行大選這種模版化的維和建和程序,即體現(xiàn)了這種契約性和平理念。在非洲的傳統(tǒng)文化中,解決沖突、建設(shè)和平的關(guān)鍵在于“共識(shí)建設(shè)”。這種沖突解決與追求和平的范式是基于非洲傳統(tǒng)精神。烏班圖精神就是南部非洲傳統(tǒng)哲學(xué)的集中體現(xiàn)。烏班圖(Ubuntu)一詞來(lái)自南非祖魯語(yǔ),它是非洲社會(huì)的精神基礎(chǔ)。其世界觀體現(xiàn)在其傳統(tǒng)格言“一個(gè)人之所以為人,是因?yàn)槠渌说拇嬖凇薄醢鄨D精神有三個(gè)信條。第一,烏班圖是人們內(nèi)心深深的宗教信仰,這種宗教認(rèn)為,人因?yàn)槠渥嫦榷嬖冢吲c死者共在并相互依存,祖先是他們與神之間的中介人。第二,強(qiáng)調(diào)共識(shí)建設(shè)。沖突與爭(zhēng)執(zhí)事務(wù)與每個(gè)人都相關(guān),并賦予每個(gè)人表達(dá)的權(quán)利,在漫長(zhǎng)的討論中追求共識(shí)。第三,強(qiáng)調(diào)和依靠對(duì)話。烏班圖鼓勵(lì)每個(gè)人向他人真實(shí)地表達(dá)自己的觀點(diǎn),直面差異,在對(duì)話過程中,尊重特殊性、個(gè)體性和歷史性。[15](P201-203)從烏班圖精神可以看出,非洲世界觀表現(xiàn)為社區(qū)主義的集體主義精神,承認(rèn)復(fù)雜性和多元性,這不同于西方世界觀的二元對(duì)立和個(gè)體主義的思維方式。這種世界觀指導(dǎo)下的沖突解決根本方式也不同于西方。烏班圖精神指導(dǎo)下的非洲沖突解決的傳統(tǒng)機(jī)制往往分為五個(gè)階段:首先查明真相和事實(shí),鼓勵(lì)受害者、侵犯者和目擊者在傳統(tǒng)沖突解決論壇上表達(dá),承認(rèn)責(zé)任或罪行;其次,鼓勵(lì)侵犯者表達(dá)懺悔;第三,鼓勵(lì)侵犯者請(qǐng)求原諒,受害者表示寬容和仁慈;第四,長(zhǎng)老委員會(huì)要求侵犯者為其罪行和錯(cuò)誤行為做出補(bǔ)償或賠償;最后鼓勵(lì)各方進(jìn)一步真心和解以鞏固整個(gè)過程。[16]除了南部非洲的烏班圖式和解,非洲不同地區(qū)不同民族都有自己傳統(tǒng)的沖突調(diào)解和解決制度,它們都強(qiáng)調(diào)通過寬恕、和解及恢復(fù)性正義來(lái)實(shí)現(xiàn)和平。這不同于西方主導(dǎo)的基于理性、懲罰性正義的沖突和解方式。總之,不同世界觀對(duì)和平的不同理解,深深影響了沖突解決與建設(shè)和平的根本方式。
三、作為政治規(guī)范的文化與建設(shè)和平
通過何種政治組織形式來(lái)建構(gòu)特定領(lǐng)土范圍內(nèi)的秩序,實(shí)現(xiàn)某一社會(huì)內(nèi)部的和平,在不同歷史階段或同一歷史階段的不同地區(qū),有不同的政治規(guī)范假定。歷史上,主權(quán)國(guó)家這一制度形式在歐洲起源并擴(kuò)散到全球成為一項(xiàng)普遍性規(guī)范之前,先后出現(xiàn)過部落、城邦國(guó)家、帝國(guó)、殖民地和封建領(lǐng)主制等不同的人類社會(huì)組織形式。只是在近代以后,民族國(guó)家才在眾多政治規(guī)范競(jìng)爭(zhēng)中勝出,幾乎主導(dǎo)了人類治理社會(huì)共同體內(nèi)部沖突的想像。即便如此,在當(dāng)今的非洲、大洋洲等部分地區(qū),傳統(tǒng)部族政治規(guī)范和政治文化依然根深蒂固地影響著人們的政治生活。也就是說(shuō),當(dāng)前至少存在兩種影響建設(shè)和平的政治規(guī)范文化,一種是處于全球支配地位的民族國(guó)家規(guī)范,一種是處于地方邊緣性地位的部族政治規(guī)范。它們?cè)诓煌潭壬嫌绊懼ㄔO(shè)和平的路徑選擇。
首先,民族國(guó)家政治規(guī)范在全球的盛行和文化霸權(quán)地位從根本上決定了國(guó)際社會(huì)在后沖突國(guó)家開展建設(shè)和平工作時(shí)始終以國(guó)家建設(shè)為根本路徑。無(wú)論是冷戰(zhàn)期間的傳統(tǒng)維和還是后冷戰(zhàn)時(shí)期的和平行動(dòng),都是如此。在冷戰(zhàn)時(shí)期,國(guó)際社會(huì)關(guān)于兩項(xiàng)原則有著總體性共識(shí),即主權(quán)國(guó)家是世界政治中基本的合法行為體,民族自決與去殖民化成為符合國(guó)際道德的重要國(guó)際規(guī)范。在美蘇為首的資本主義國(guó)家與社會(huì)主義兩大陣營(yíng)對(duì)壘情況下,關(guān)于國(guó)內(nèi)治理制度形式完全沒有國(guó)際共識(shí)。冷戰(zhàn)時(shí)期的維和戰(zhàn)略深受這一全球主導(dǎo)性文化規(guī)范的影響,這主要體現(xiàn)在三個(gè)方面:對(duì)主權(quán)國(guó)家作為國(guó)內(nèi)秩序模式的堅(jiān)定支持、對(duì)去殖民化的積極支持以及對(duì)國(guó)內(nèi)治理問題的中立態(tài)度。[17](P441-473)冷戰(zhàn)后,國(guó)際和平行動(dòng)繼承和延續(xù)了以國(guó)家建設(shè)為中心的建設(shè)和平戰(zhàn)略,因?yàn)闊o(wú)論是歐美等西方國(guó)家還是中國(guó)等新興大國(guó)都深受主權(quán)國(guó)家規(guī)范的持續(xù)性影響,在脆弱國(guó)家建設(shè)和平時(shí)都支持國(guó)家建設(shè)為中心的方法。
其次,民族國(guó)家政治規(guī)范對(duì)后沖突建設(shè)和平的影響還充分體現(xiàn)在自由和平理念在冷戰(zhàn)后建設(shè)和平領(lǐng)域的盛行。冷戰(zhàn)期間,關(guān)于國(guó)內(nèi)治理何種制度形式為優(yōu)幾乎沒有國(guó)際共識(shí)。冷戰(zhàn)后,和平行動(dòng)的最突出的特征是,試圖將戰(zhàn)亂失序的國(guó)家重建為自由民主國(guó)家。其前提理念是,自由民主才是這些國(guó)家合適的國(guó)內(nèi)政治組織模式。[18](P637-655)國(guó)際和平行動(dòng)從不愿意參與國(guó)內(nèi)事務(wù)到積極支持某種特定的國(guó)內(nèi)治理模式這一轉(zhuǎn)變反映了全球政治文化的變化,即出現(xiàn)了合法性國(guó)家的新標(biāo)準(zhǔn)。這一標(biāo)準(zhǔn)將自由民主制度視為國(guó)內(nèi)治理的最合適模式,自由民主成為唯一具有意識(shí)形態(tài)合法性的國(guó)內(nèi)治理模式。與此相應(yīng),國(guó)際維和戰(zhàn)略不僅繼續(xù)推進(jìn)威斯特伐利亞國(guó)家制度,而且開始在東道國(guó)兜售自由民主制度。建設(shè)和平戰(zhàn)略的這一變化其實(shí)是民族國(guó)家政治規(guī)范的變化在國(guó)際維和領(lǐng)域的反映。
再次,在非洲等維和建和主要地區(qū)根深蒂固存在的部族政治規(guī)范決定了建設(shè)和平的另一條替代性路徑選擇,即本土和平路徑。所謂“本土和平路徑”是指以沖突地區(qū)的本土知識(shí)、傳統(tǒng)資源為基礎(chǔ)的沖突解決與建設(shè)和平范式。其根本特點(diǎn)是“非國(guó)家中心”,不把現(xiàn)代國(guó)家模式強(qiáng)加于本地社會(huì),而是利用部族社會(huì)現(xiàn)存的暴力控制與沖突解決機(jī)制,在建設(shè)和平進(jìn)程中避開或推遲國(guó)家建設(shè)。索馬里蘭和盧旺達(dá)的沖突后重建是經(jīng)常被用以證明非洲本土和平規(guī)范成功的兩個(gè)典型案例。索馬里蘭地區(qū)在索馬里內(nèi)戰(zhàn)、中央政權(quán)崩潰后的1990—1997年,不僅通過本土和平路徑實(shí)現(xiàn)了沖突解決與氏族間和解,并且經(jīng)過兩屆政府的努力逐步建立起政府權(quán)威。在此基礎(chǔ)上,1997年后索馬里蘭進(jìn)一步將傳統(tǒng)社會(huì)結(jié)構(gòu)與現(xiàn)代民主制度相融合,建立起頗具特色民主社會(huì),成為索馬里最穩(wěn)定有序的地區(qū)。[19]盧旺達(dá)1994年大屠殺后的民族和解與國(guó)家重建的成功被稱為“盧旺達(dá)新生奇跡”。其和平重建之所以取得成功,不僅因?yàn)榭用吠ㄟ^憲法法律和教育手段強(qiáng)化統(tǒng)一的國(guó)民認(rèn)同,更基礎(chǔ)性的原因在于盧旺達(dá)將民族和解與發(fā)展建立在傳統(tǒng)社會(huì)結(jié)構(gòu)之上,動(dòng)員自下而上的民眾廣泛參與,具體實(shí)施中充分利用了基于傳統(tǒng)的團(tuán)結(jié)和解營(yíng)、蓋卡卡(Gacaca)法庭、村落互助共存文化等本土化解決方案。[20]
正是在當(dāng)前兩種不同政治規(guī)范文化的影響下,建設(shè)和平領(lǐng)域一直長(zhǎng)期存在兩條路徑或兩種文化模式之爭(zhēng),即內(nèi)部主導(dǎo)的傳統(tǒng)戰(zhàn)略與外部主導(dǎo)的現(xiàn)代戰(zhàn)略的爭(zhēng)論。[21](P1-16)前者強(qiáng)調(diào)“自下而上”路徑、“草根和平”、恢復(fù)“傳統(tǒng)社會(huì)力量”作用等要素,而后者則堅(jiān)持“自上而下”地推進(jìn)國(guó)家機(jī)構(gòu)和組織制度建設(shè)。兩種不同的方法和偏好反映了世界政治規(guī)范中兩種不同的文化。一種是“民族國(guó)家”政治規(guī)范文化,另一種是非洲傳統(tǒng)“部族社會(huì)”的政治組織文化。兩種文化對(duì)如何建立人類共同體的秩序與和平有不同的經(jīng)驗(yàn)。歐洲經(jīng)過數(shù)百年的戰(zhàn)爭(zhēng),建立起了現(xiàn)代民族國(guó)家。這些國(guó)家有固定的領(lǐng)土和疆界,有唯一的中央權(quán)威,存在一致的國(guó)家認(rèn)同基礎(chǔ),并通過中央政府、軍隊(duì)、警察、法院等對(duì)暴力手段的合法性壟斷來(lái)解決國(guó)內(nèi)社會(huì)沖突、建立內(nèi)部社會(huì)秩序。[22](P196-197)在非洲傳統(tǒng)社會(huì)中廣泛存在的卻是迥異于現(xiàn)代國(guó)家的傳統(tǒng)部族政治制度,即“無(wú)國(guó)家社會(huì)”[23](P6-11)或“無(wú)霸權(quán)國(guó)家”。[24](P10-23)在這種政治制度中,往往缺少可以在其疆域內(nèi)實(shí)現(xiàn)有效社會(huì)控制的中央權(quán)威,權(quán)力分散在各個(gè)部族或氏族之中。各部族間人們往往通過討論和共識(shí)來(lái)解決沖突或做出決策,傳統(tǒng)長(zhǎng)老在解決內(nèi)部沖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兩種政治規(guī)范文化所處地位的差距,當(dāng)前建設(shè)和平規(guī)范格局也出現(xiàn)嚴(yán)重失衡。一方面,自由和平規(guī)范雖然長(zhǎng)期受到質(zhì)疑,但卻始終處于支配地位,決定著脆弱國(guó)家沖突解決與建設(shè)和平工作的基本方向和議程。另一方面,傳統(tǒng)和平路徑雖然在非洲的某些地區(qū)和國(guó)家悄然取得了成功,但依然處于邊緣化地位和自發(fā)狀態(tài),并未得到國(guó)際社會(huì)足夠的重視。
四、作為社會(huì)習(xí)俗的文化與建設(shè)和平
如果說(shuō),世界觀意義上的文化,決定了沖突治理與和平建設(shè)的根本方式,政治規(guī)范意義上的文化決定了沖突治理與和平建設(shè)在何種政治組織框架內(nèi)進(jìn)行,那么,宗教規(guī)范與社會(huì)習(xí)俗意義上的文化則往往在微觀互動(dòng)層次上影響著“宏觀層次總體和平進(jìn)程的成敗”。[25](P142-168)也就是說(shuō),在特定世界觀框架下,在推進(jìn)某種政治組織恢復(fù)和重建或發(fā)揮特定政治組織優(yōu)勢(shì)開展沖突調(diào)停與和平建設(shè)過程中,宗教差異與社會(huì)習(xí)俗是一種不可忽視的文化變量。
首先,宗教和社會(huì)習(xí)俗影響國(guó)際和平干預(yù)行動(dòng)的合法性。針對(duì)脆弱國(guó)家建設(shè)和平的外部干預(yù)行動(dòng)都包含一個(gè)假定即其所做的事是正確的。這包含三層意思:其行動(dòng)與舉措是合法的;干預(yù)者是實(shí)施這些行動(dòng)的合適人或組織;干預(yù)者有權(quán)采取這一干預(yù)行動(dòng)。對(duì)合法性的判斷主要依賴于在特定環(huán)境中何種行動(dòng)合情合理且被允許的認(rèn)知與情感。這種判斷主要基于文化實(shí)踐所創(chuàng)造的、體現(xiàn)于習(xí)俗習(xí)慣的長(zhǎng)期文化傾向。也就是說(shuō),合法性是一種文化性建構(gòu)。[26](P528-543)在特定環(huán)境中不是每個(gè)行為體都可以合法地實(shí)施特定行動(dòng)。例如,調(diào)解已經(jīng)成為沖突解決領(lǐng)域的重要工具,但誰(shuí)有合法身份充當(dāng)調(diào)解者?在美國(guó),流行的觀點(diǎn)認(rèn)為,可以充當(dāng)調(diào)解者的干預(yù)者應(yīng)該是中立的,年齡及其他特征與沖突調(diào)解本身是不相關(guān)的。但在另一些傳統(tǒng)社會(huì),充當(dāng)調(diào)解者干預(yù)者必須是沖突的利益相關(guān)者,最好是一個(gè)受尊敬的部落長(zhǎng)老。
其次,宗教社會(huì)習(xí)俗對(duì)建設(shè)和平的影響更多時(shí)候表現(xiàn)為維和建和進(jìn)程中的文化沖突。干預(yù)者與被干預(yù)者往往是從自身的經(jīng)驗(yàn)與文化框架視角來(lái)解讀特定干預(yù)行動(dòng)的意義,因而理解會(huì)很不相同,從而導(dǎo)致錯(cuò)覺、誤解和沖突。例如,就女性割禮而言,西方干預(yù)者可能把幫助脆弱國(guó)家廢除這種風(fēng)俗的努力理解為支持普適性人權(quán),然而被干預(yù)者卻往往將其視為對(duì)自身身份認(rèn)同的侵犯與攻擊。[27](P1-41)再如,在索馬里多邊維和行動(dòng)中,國(guó)際社會(huì)的代表認(rèn)為其行動(dòng)是標(biāo)準(zhǔn)的人道主義行動(dòng),即通過食物分配挽救生命。相反,許多索馬里人認(rèn)為,國(guó)際行動(dòng)意在改變穆斯林民眾的信仰,使其皈依基督教,或者將其視為對(duì)其社區(qū)與政治領(lǐng)導(dǎo)的冒犯與攻擊。[28]很多研究都表明,國(guó)際干預(yù)者對(duì)索馬里政治與文化的無(wú)知是導(dǎo)致索馬里維和失敗的重要原因。[25](P142-168)[29](P254)由于干預(yù)的合法性與權(quán)威性都是一種文化建構(gòu),所以對(duì)試圖改變脆弱國(guó)家沖突情勢(shì)的干預(yù)者而言,了解他們所干預(yù)目標(biāo)國(guó)家的社會(huì)文化就顯得十分重要。它有助于干預(yù)者評(píng)估其干預(yù)的努力有多大可能被接受,有助于干預(yù)者調(diào)整其行為以更好地適應(yīng)干預(yù)對(duì)象的文化,提高其行動(dòng)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經(jīng)過數(shù)十年維和經(jīng)驗(yàn)與教訓(xùn)的積累,當(dāng)前,保持對(duì)干預(yù)目標(biāo)國(guó)文化的敏感性、妥善處理文化差異,已經(jīng)成為國(guó)際和平干預(yù)實(shí)踐者與研究者的一項(xiàng)普遍共識(shí)。
再次,文化習(xí)俗對(duì)建設(shè)和平的影響還體現(xiàn)在各種參與和平行動(dòng)的機(jī)構(gòu)人員內(nèi)部的文化差異與協(xié)調(diào)。首先,維和部隊(duì)貢獻(xiàn)國(guó)日益增多,維和人員來(lái)自眾多不同的國(guó)家,他們都各自帶來(lái)了自己國(guó)家的文化、信念和習(xí)俗,需要協(xié)調(diào)溝通。其次,歷次維和行動(dòng)中都有外交機(jī)構(gòu)、人道主義機(jī)構(gòu)、軍事機(jī)構(gòu)、民事組織的參與。每一個(gè)機(jī)構(gòu)對(duì)沖突及其解決都有自己的視角、價(jià)值觀、態(tài)度、信念和行為風(fēng)格,形成了自己特定的組織文化。[25](P142-168)這很容易導(dǎo)致各機(jī)構(gòu)之間工作相互隔離甚至對(duì)立,妨礙各機(jī)構(gòu)之間在沖突解決與和平建設(shè)中形成合力,實(shí)現(xiàn)和平目標(biāo)。這種體現(xiàn)于維和機(jī)構(gòu)內(nèi)部之間微觀層次的文化傾向也同樣構(gòu)成了影響弱國(guó)沖突解決與和平建設(shè)的重要因素。
結(jié) 語(yǔ)
文明和文化因素在世界觀、政治規(guī)范和社會(huì)習(xí)俗等不同層次影響著當(dāng)代國(guó)內(nèi)沖突的治理。在任何層次輕視或忽略文化因素都是膚淺和危險(xiǎn)的。忽略作為沖突治理對(duì)象的被干預(yù)者與干預(yù)者世界觀的差異,國(guó)際干預(yù)的和平效果不僅難以持續(xù),甚至?xí)l(fā)文明間的沖突與對(duì)立。忽略現(xiàn)代國(guó)家作為一種政治規(guī)范的文化霸權(quán)傾向及其局限性,可能會(huì)限制國(guó)際社會(huì)建設(shè)和平行動(dòng)的策略性和本土適應(yīng)性,造成事倍功半的結(jié)果。忽略社會(huì)文化習(xí)俗差異,在具體政策中就可能直接遭遇失敗,更毋庸說(shuō)宏觀和平目標(biāo)的實(shí)現(xiàn)。社會(huì)習(xí)俗差異和世界觀因素,因幾十年的經(jīng)驗(yàn)累積、人類文明互動(dòng)的日益頻繁以及人們對(duì)文明沖突的危機(jī)意識(shí),已經(jīng)開始在理論和實(shí)踐中日益引發(fā)關(guān)注。然而,國(guó)家中心主義的文化模式因民族國(guó)家的霸權(quán)地位在實(shí)踐中仍然在偏執(zhí)地盛行。其不良后果顯而易見,不僅表現(xiàn)在維和過程中文化沖突引發(fā)的直接軍事沖突及維和失敗,而且還表現(xiàn)在當(dāng)代以威斯特伐利亞民族國(guó)家模式和自由民主模式為指導(dǎo)的沖突后建設(shè)和平行動(dòng)差強(qiáng)人意的效果。[30](P106-139)
在此背景下關(guān)注和研究文化因素具有重要戰(zhàn)略價(jià)值和政策啟示意義。第一,關(guān)注文化有助于國(guó)際社會(huì)反思當(dāng)前國(guó)際和平行動(dòng)中暗含的文化霸權(quán),拋棄原有政策的西方文化中心主義,超越放之四海而皆準(zhǔn)的標(biāo)準(zhǔn)配方與固定程序,拓寬國(guó)際和平行動(dòng)政策制定者的想像空間。第二,關(guān)注文化有利于超越國(guó)際和平行動(dòng)中僵化的、“自上而下”的、國(guó)家中心主義思維定勢(shì),充分發(fā)掘沖突國(guó)家的沖突治理的“地方性知識(shí)”和本土資源,尊重和發(fā)揮“自下而上”的、傳統(tǒng)社會(huì)力量的作用,從而形成更具整體性、可行性的和平行動(dòng)新戰(zhàn)略。第三,關(guān)注文化有助于打破全球安全治理體系中西方支配的單一結(jié)構(gòu),促進(jìn)西方與非西方等多種文化文明的對(duì)話交流,構(gòu)筑更加合理的、多元共存的安全治理文化體系。第四,關(guān)注文化勢(shì)必推動(dòng)人們將社會(huì)學(xué)、人類學(xué)、政治學(xué)、歷史學(xué)、地理學(xué)等多種學(xué)科引入國(guó)際和平行動(dòng)的研究,不僅拓寬沖突解決與和平研究的理論視野,而且使政策研究更接地氣、更貼近發(fā)生沖突國(guó)家的社會(huì)政治生活的現(xiàn)實(shí),從而切實(shí)提升沖突解決與建設(shè)和平的實(shí)踐效果。
[1] 李東燕.中國(guó)參與聯(lián)合國(guó)維和建和的前景與路徑[J].外交評(píng)論,2012,(3).
[2] 胡建國(guó),辛越. 聯(lián)合國(guó)維和任務(wù)區(qū)文化差異研究[J].武警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2,(11).
[3] John Burton. Conflict: Human Needs Theory [M]. London: Maclillan,1990.
[4] Kevin Avruch. Culture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M].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ititute of Peace Press,1998.
[5] Wiliam Zartman, M. Berman.The Practical Negotiator[M].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2.
[6] Gulliver. Disputes and Negotiations:A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1979.
[7] R. Cohen. Culture and Conflict in Egyptian-Israeli Relations:A Dialogue of the Deaf[M].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0.
[8] J. Lederach. Preparing for Peace: Conflict Transformation across Cultures[M]. N.Y.: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95.
[9] J. Galtung. Cultural Violence[J].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1990,27(3).
[10] 中國(guó)大百科全書(哲學(xué)卷)[M].北京:中國(guó)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4.
[11] 約翰·加爾通.和平論[M].陳祖洲譯.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
[12] Marshall Bei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Uncommon Places:Indigeneity,Cosmology,and the Limits of International Theory[M].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2005.
[13] 王學(xué)軍.從國(guó)內(nèi)經(jīng)驗(yàn)看中國(guó)對(duì)非洲的和平與安全政策[J].非洲研究,2012,(1).
[14] Isaac Albert.Understanding Peace in Africa [A]. in David Francis (eds.).Peace and Conflict in Africa[C]. London and New York: Zed Books, 2008.
[15] Abdul KarimBangura. African Peace Paradigms[M]. Dubuque, IA: Kendall/Hu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8.
[16] Timothy Murithi. Practical Peacemaking Wisdom from Africa: Reflections on Ubuntu[J].The Journal of Pan African Studies, Vol. 1, No.4, June 2006.
[17] Roland Paris. Peacekeeping and the Constraints of Global Culture [J].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9,No.3, 2003.
[18] Roland Paris. International Peacebuilding and the “Mission Civilisatrice”[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8.No.4,2002.
[19] 王學(xué)軍.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混合:索馬里蘭沖突治理的歷史與理論反思[J].非洲研究,2014,(1).
[20] 莊晨燕.民族沖突后的和解與重建:以盧旺達(dá)1994年大屠殺后的國(guó)族建構(gòu)實(shí)踐為例[J].中央民族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4,(3).
[21] Samuel GbaydeeDoe. Indigenizing Postconflict State Reconstruction in Africa: A Conceptual Framework[J].Africa Peace and Conflict Journal, Volume 2, Number 1, 2009.
[22] 馬克斯·韋伯.韋伯作品集:學(xué)術(shù)與政治[M].錢永祥等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4.
[23] Christian Potholm.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frican Politics[M].Lanham, Marylan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8.
[24] Alex Thomson.An Introduction to African Politic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25] Tamara Duffey. Cultural Issues in Contemporary Peacekeeping[J].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Vol.7,No.1, 2000.
[26] Robert Rubinstein. Intervention and Culture: 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to Peace Operations[J].Security Dialogue, Vol. 36, No. 4, 2005.
[27] Sandra D. Lane, Robert A. Rubinstein. Judging the Other: Responding to Traditional Genital Surgeries[J].Hastings Center Report, 1996,26(3).
[28] John L. Hirsch, Robert B. Oakley. Somalia and Operation Restore Hope: Reflections on Peacemaking and Peacekeeping[M].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1995.
[29] 劉易斯. 索馬里史[M].趙俊譯.北京:中國(guó)出版集團(tuán),2011.
[30] Pierre Englebert, Denis M. Tull. Postconflict Reconstruction in Africa: Flawed Ideas about Failed States[J].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2, No. 4, 2008.
[責(zé)任編輯劉蔚然]
CultureandPeacebuilding:fromPerspectiveofCulturalStratification
WangXuejun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Zhejiang 321004)
culture; world outlook; political norms; conflict resolution; peacebuilding
To understand the influence of culture on peacebuilding, it is necessary to stratify the concept of culture. As a world outlook, culture influences the basic concept of peace and the fundamental way of building peace. As a political norm, culture determines the specific form and path of political organization to reconstruct domestic order and peace. As a social custom, culture affects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the macro level peace process through the micro level of interaction. Ignoring the role of any level of culture is both superficial and dangerous for resolving conflicts and building peace in vulnerable countries.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 of cultural factors has important strategic value and policy significance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operations.
* 本文是浙江省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重點(diǎn)研究基地非洲研究中心課題“非洲沖突管理機(jī)制發(fā)展現(xiàn)狀對(duì)中國(guó)參與非洲和平安全建設(shè)的影響及對(duì)策研究”(項(xiàng)目號(hào):14JDFZ01Z)和浙江省2011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中心“非洲研究與中非合作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中心”項(xiàng)目(項(xiàng)目號(hào):15FZZX26YB)的研究成果。
王學(xué)軍,浙江師范大學(xué)非洲研究院副研究員,法學(xué)博士(浙江 金華32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