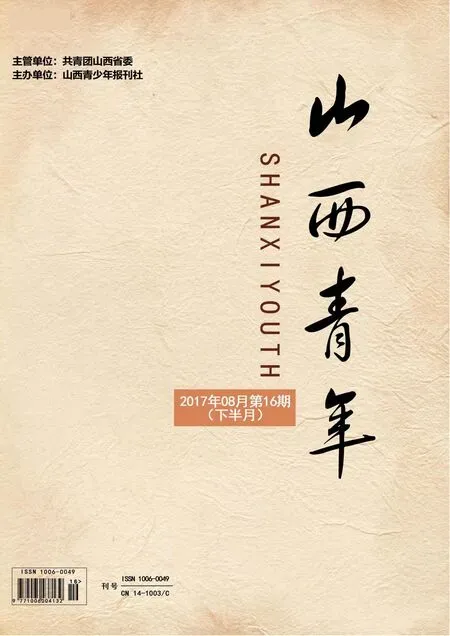信息時代下對人異化的探析
周奕鋒
信息時代下對人異化的探析
周奕鋒*
武漢紡織大學,湖北 武漢 430000
二十一世紀是個信息爆炸的時代,人們面臨的誘惑越來越多。人們開始變得不受控制,甚至被自己創造的東西反過來控制,人逐漸異化了。馬克思通過異化概念來說明人與勞動的關系,從而逐步揭示人與人的社會關系。本文以《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異化概念為基礎,著重討論在信息時代下勞動者與勞動產品相異化進而分析人與人相異化,并對此提出相應的解決措施,希望對我們的社會生活有所裨益。
信息時代;異化;異化勞動
一、“異化”概念及其特征
異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哲學概念,它從提出到成熟經歷了一個過程。在人類發展的歷史上,異化被賦予了不同的定義:盧梭認為“異化”就是權力的讓渡;黑格爾把“異化”理解為主體從事活動的結果反而成為制約你的東西;費爾巴哈則認為“異化”是把人的本質異化為上帝。馬克思的異化理論主要是指異化勞動理論,馬克思把哲學的“異化”概念與經濟學的“勞動”概念合并起來,構成“異化勞動”的概念。他認為“異化”是人與其勞動產品之間的一種相異的關系。即人的勞動產物,不隨人意志的改變而改變,成為一種與自身相異的東西。
根據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內容,異化勞動理論有四個方面的規定:勞動者的勞動同他的勞動產品相異化;勞動者同他的勞動相異化;勞動者同他的類本質相異化;人同人相異化。[1]
(一)勞動者的勞動同他的勞動產品相異化
18世紀60年代興起的工業革命促進了社會化大生產,給人類物質文明帶來了極大發展。但物質文明的極大豐富并沒有給工人帶來幸福感,相反的,工人階級陷入了前所未見的苦難。工人創造財富的同時被資本家剝削,他們住的條件差,往往地方狹小,陰冷潮濕,沒有床,兩張板凳、一個桌子是他們的生存常態。勞動產品是由勞動創造的,勞動產品理當由勞動者占有。但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工人創造出來的勞動產品不僅不由工人支配,獨立于工人之外而存在,相反走向工人的反面,成為與工人相異的東西,最終變成與工人相對立的敵對力量。工人創造的財富越多,卻遭受更嚴重的剝削,而變得更窮。工人們創造的價值與其理應獲得的財富是不成正比的,相反是處于被剝削的境地。這種完全不對等的關系讓工人們生活困頓。正如馬克思所論述的:“凡是成為他的勞動的產品的東西,就不再是他自身的東西。因此,這個產品越多,他自身的東西就越少。”[2]工人同他的勞動產品相異化,即勞動對象的異化。
(二)勞動者同他的勞動相異化
工業革命盡管帶動了生產力的飛速發展,整個社會的進程極速向前,但工人對勞動的態度卻發生巨變。隨著現代工廠的出現,資本家找到了剝削工人階級的場所,工人的身體和精神都受到了不同程度上的摧殘。社會化大生產給工人階級帶來了苦難。工人幾乎成了機器的簡單附屬品,不僅被廠主、監工監視,而且被廠主進行各種罰款。勞動本該是人自覺自愿的行為,現在卻變成了一種謀生手段,更不用說給工人帶來幸福的感受了。工人一方面很想逃離工廠,逃離勞動,一方面又不得不為了生存而勞動。在這種情形下,人與動物無異。人在勞動時,完全感受不到勞動帶來的滿足感。人們不再有發揮主觀能動性去創造價值的沖動。工人的勞動不再屬于自己,而是被強制的行為。就像馬克思描述的那樣:“勞動的異己性完全表現在:只要肉體的強制或其他強制一停止,人們就會像逃避瘟疫那樣逃避勞動。”[3]工人的勞動不再是工人本人的意志,即工人與其勞動自身發生了異化。
(三)勞動者同他的類本質相異化
馬克思強調,“勞動這種生命活動、這種生產活動本身對人來說不過是滿足一種需要即維持肉體生存的需要的一種手段,而生產生活就是類生活。一個種的整體特性、種的類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動的性質,而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恰恰就是人的類特性。”[4]在現代社會,物質產品的極大豐富使人的類本質失去在物質世界里。人們開始背離自己的本質生活,并且漸漸地迷失在自己的生活里。我們征服了自然,卻臣服于自己所創造的機器。由于勞動本身發生異化,導致人類不能進行肯定自身、發展自身的勞動,人們失去了自身的類生活和類本質。人們不能開展有益于自身的勞動,即人與自身類本質發生異化。
(四)人同人相異化
馬克思認為:“人同自己的勞動產品、自己的生命活動、自己的類本質相異化的直接結果就是人同人相異化。當人同自身相對立的時候,他也同他人相對立。”[5]十九世紀三四十年代,三大工人運動在歐洲發展起來。法國里昂工人打出“不能勞動而生,就要戰斗而死”的口號,起義情緒高漲;英國工人為推翻富人政權,爭取民主共和國進行憲章運動;德意志西里西亞織工要求取得普選權,參與國家管理而進行起義。工人階級覺醒起來與資產階級相抗爭,就是人與人異化的結果。兩大階級的矛盾激化,人與人之間相互對立、相互敵視,即人與人相異化。
二、信息時代下的異化表現
信息時代下,人的異化又呈現出新的特征:
(一)信息時代下人與手機相異化
在信息時代,人們生存、生活的環境,思維方式等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并且發展日新月異,不可阻擋。這對人與社會的自由全面發展既是一次新的機遇,也提出了新的挑戰,甚至加快了人的新異化。尤其突出的是手機的影響。人們創造出手機的本意是為了更方便人們的交流,結果卻導致現在人們離開手機簡直不能生存,人們之間面對面的交流更少了。人們變得更孤獨了。人們漸漸成為了手機的奴隸,被手機役使。人逐漸與手機異化了。
(二)信息時代下人同他的勞動相異化
在現代社會,尤其是在人工智能逐漸融入我們的生活后,我們發現自己越來越依賴科技了,甚至于都忘記了自己的本能。現代的人家里都有洗衣機、洗碗機、微波爐等,有的還有掃地機器人,當這些東西全部派上用場之后,大抵就沒我們人類什么事兒了。有些人變得好吃懶做,不僅僅表現在行為上,而且體現在對信息的攝取上。大多人只想著獲取有用的信息,而不進行更多的編輯、思考,人們的思維模式受到了禁錮,人們對事物的態度變得消極。我們在享受便捷生活的同時,似乎也逐步喪失了人之所以為人的最重要的東西,那就是勞動。有的人或許會辯駁,科技的運用就是為了人們更好的生活,更好的享受生活。但是他們忘記了生命在于運動,我們的人生只有在不斷地改進,不斷地創造,不斷地勞動中才能獲得美好的、有價值的生活。
(三)信息時代下人同他的類本質相異化
現代文明作為人的實踐活動的載體,為人們的生產、生活提供了相對舒適的環境。人們卻無法在勞動中找到自我。人們認為自己的勞動是生存的需要,而不是生產發展的需要,更不是發展自己的需要。人的類本質是追求自由自在,是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而現在,我們無法在勞動中找到自己想要的東西,無法在勞動中實現自我的價值。我們不是進行有意識的、自由的活動,而是做著機械性的活動,過著得過且過的生活。
(四)信息時代下人與人相異化
在信息時代,人們變得越來越冷漠、越來越功利了。精致的功利主義者、精致的利己主義者數見不鮮。有些人就是可以做到為了一個出國機會要找教授簽名而積極表現,在得到簽名后立刻消失無蹤。這種事情不是個案,折射出當前國人為人做事極強的目的性。在事業前程上心態急躁一些或許還勉強可以理解,但是如果連感情也套上利益的鎖鏈,和利益捆綁在一起的話,就未免讓人擔心。男女之間的感情本是天然的,純粹的。我們可以因為共同的價值觀、興趣愛好或者一些其它的因素在一起,卻不能因為條件適合而在一起。感情是不能用一堆指標去衡量的。男生都不再追女生了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悲哀。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大家整日奔波于各種社交場所,進行著毫無真誠的對話,還自嘲到大家都一樣。我們慢慢開始不再談論感情了,仿佛那是一件可笑的事情,大家各取所需,人們的關系變得只剩下利益關系。人與人的關系被利益代替了。
三、信息時代下對人異化的解決措施
信息時代,人怎樣才能消除異化或減輕異化?
(一)發掘自身興趣
當人們沉醉在自己感興趣的事情中時,人們會漸漸忽略周圍的其他事情。當你成功培養出自己對某一項事情濃厚的興趣時,手機依賴癥就已經治愈了一半了。我們發掘自身的興趣對我們忘掉一些東西有奇效。比如看一本好書,參加一項體育活動,學會燒一手好菜,接觸一門樂器等。
(二)加強人與人的交流溝通
溝通交流對于人是必需的。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應該注意培養自己的溝通技巧,有針對性的,自覺的與人多做交流。不要害怕與人交往,我們應該敞開心扉,去接納外面的人和事,去接受、去感受和自己不一樣的人。我們可以試著每天預留一段固定的時間跟家人說說話,并規定在這段時間內不受外界其它因素的干擾,尤其不能玩手機。我們可以多參加一些同學聚會之類的場合,可以增進感情。
(三)改變看待事物的角度眼光
馮友蘭的《中國哲學簡史》明誠篇里有這樣一句話,“成己的同時,一定要看到還要成人。”[6]這句話是說,我們不僅要實現個人的價值,也要努力實現社會價值,要做到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的統一。因為在很多時候,成全自己就是以成全他人為前提的。我們應該學會做一個胸懷寬廣的人,畢竟幫助他人是自身快樂的源泉。改變看待事物的眼光角度,我們可以收獲更多的幸福,也能夠達到更高的境界。
(四)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人的異化其實表現為一種人的自我迷失,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人們提供了一個怎樣做的標準,因此,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減輕人的異化有所幫助。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公民個人層面要求做到愛國、敬業、誠信和友善。如果朝著這個方向一起努力,那么人們之間的關系勢必會改善,同時減輕人的異化也成為可能。
信息時代下人的異化是人性逐漸趨于功利所致。人們希望可以便捷的獲取信息的同時,也希望可以快速的交到朋友。但是我們往往忽略了最重要的一點,那就是情感的交流需要花費時間、需要花費精力更需要付出感情。我們不能正確的認知和對待現代科技所帶給我們的東西,實質上是我們不能正確看待人與人之間的感情,沒有真正明白情感交流的意義。面對現代科技的沖擊,我們應該堅定自己的信念,使科學技術真正造福人類。我們需要的是讓科技融入我們的生活,而不是讓科技代替我們生活。克服現代性異化,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有積極意義。
[1]鄭智尹.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異化勞動理論的具體規定[J].學理論,2013(31):50-51.
[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57.
[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59.
[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62.
[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63.
[6]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170-171.
周奕鋒(1994-),女,漢族,湖北麻城人,武漢紡織大學,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C
A
1006-0049-(2017)16-007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