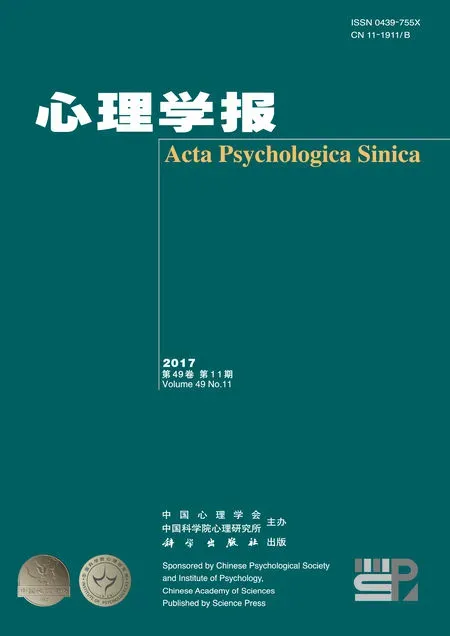先苦后樂:英語樂學大學生在英語學習時情緒反應的腦認知特點*
劉潞潞 盧家楣 和 美 周建設 肖 晶 羅 勁 ,
(1首都師范大學心理學院, 北京市“學習與認知”重點實驗室, 北京 100048) (2上海師范大學教育學院, 上海 200234)(3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 北京 100872) (4首都師范大學北京成像技術高精尖創新中心, 北京 100048)
1 引言
樂學情感, 簡稱樂學感或樂學, 是個體樂于學習的情感, 屬于理智情感大類中的一種, 具有內隱和相對穩定的特點(盧家楣, 2009; 盧家楣等,2017)。像其他情感一樣, 樂學情感雖是內隱的, 但會在個體具體情境中, 即學習活動中以情緒的形式表現出來, 并為個體所體驗到(盧家楣, 1986)。因此,具有樂學情感的個體在學習活動中, 當學習滿足其需要時會產生各種正性情緒體驗, 如高興、自豪、希望等; 當學習不滿足其需要時則會引發各種負性情緒體驗, 如厭倦、焦慮、失望、氣憤等(Pekrun,Goetz, Titz, & Perry, 2002a)。這種情緒表現也就類似于西方學者提出的學業情緒(academic emotion)。學業情緒的研究至今已有十幾年的歷史, 研究者探索了學業情緒的結構及測量方法(Pekrun et al.,2002a; 董妍, 俞國良, 2007), 影響因素(Pekrun et al.,2002a; Perry, Hladkyj, Pekrun, & Pelletier, 2001;Pekrun, Elliot, & Maier, 2006; Goetz, Preckel,Pekrun, & Hall, 2007; Frenzel, Pekrun, & Goetz,2007; Goetz, Pekrun, Hall, & Haag, 2006), 領域特異性(Goetz, Frenzel, Pekrun, & Hall, 2006; Goetz,Frenzel, Pekrun, Hall, & Lüdtke, 2007)以及年齡特征(俞國良, 董妍, 2006; 馬惠霞, 聶勝昀, 蘇世將,2010; 趙淑媛, 蔡太生, 陳志堅, 2012; 楊憲華, 徐淑燕, 2014)。
但長期以來, 此類研究存在兩方面的不足。首先, 是有關研究多致力于對特定的負性情緒(如考試焦慮)的探討, 而對正性情緒如高興、自豪、希望的研究相對比較少(Pekrun, Goetz, Titz, & Perry,2002b)。正性情緒是學習動機的基本構成要素, 它與學生學業成績密切相關(Goetz, Frenzel, Hall, &Pekrun, 2008)且能影響其后的學習行為(俞國良,董妍, 2007), 而只有當學生的學業情緒為正性時,其自我調節能力才能成為有效地轉化為促進學業成就的因素(Villavicencio & Bernardo, 2013)。理論上, 正性情緒對認知的作用及其機制近年來得到了較多的研究和論證, 如 Fredrickson提出的正性情緒的擴展和建設假說認為, 正性情緒能夠促使個體突破思維限制發現更多可能性, 擴展注意范圍, 增強認知靈活性, 從而使問題解決的效率更高。正性情緒還有利于增進個人資源(身體資源、智力資源、人際資源、心理資源) (Fredrickson & Branigan, 2001;Fredrickson, 2001; Fredrickson & Branigan, 2005)。因此, 研究正性學業情緒對于促進學生的學習具有重要的意義。
其次, 是以往此類研究多采用行為和問卷的方法, 而缺乏對腦認知過程深入探索。相比于與學業相關的其他認知過程, 此類情緒是具有內隱的相對穩定的樂學情感的情境性表現, 因此, 如能借助于認知神經科學手段直接探測腦內情緒區和獎賞區的變化, 無疑將有助于我們加深對于樂學情感的心理特征的認識和理解。例如, 一項關于數學焦慮的認知神經科學研究表明, 當具有數學焦慮的人在得知自己將被要求完成數學任務時, 與疼痛和厭惡感覺相關的后部腦島就會激活, 而該腦區在實際解決數學問題的過程中卻反而并未呈現激活, 這說明數學焦慮實際上發生于人們對于數學任務的想象和心理準備狀態, 而并非實際的思考和問題解決過程(Lyons & Beilock, 2012)。但遺憾的是, 人們卻并不清楚這種正性情緒的腦認知特點, 這影響了我們對樂學情感及其在解題過程中表現出的正性情緒的心理學原理的認識, 也影響對樂學情感的培養和促進。
鑒此, 在本項研究中, 我們選取了對英語學習懷有樂學情感的大學生被試, 采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技術研究他們的樂學情感在具體的英語學習時的情緒反應和腦認知特點。為了能在語義和熟悉性上對實驗材料進行控制, 實驗編制了外國地名要求被試進行記憶和測驗, 并以同樣的漢語文字材料(即用漢字拼寫地名和國名的詞對)作為參照條件, 研究和比較了英語樂學被試在針對英文(或中文)材料的學習準備階段(即告知被試其將學習中文或英文的提示線索)、學習階段(即被試實際學習系列呈現的中文或者英文材料)、記憶測驗準備階段(即告知被試即將對其進行中文或英文的記憶測驗的提示線索)、實際的記憶測驗實施階段以及獲得積極或消極的學習成績反饋階段的腦活動, 以揭示正性情緒的心理與腦認知特點。盡管在這項研究中我們沒有采用其他組別的被試(如厭學組別)與樂學被試進行對照, 但通過學習中、英文材料相互對比的方式不但能夠在一定意義上揭示英語樂學者的腦認知特點, 而且對于腦功能成像實驗而言, 組內設計可以更好地排除不同個體在腦活動上可能存在的差異的干擾。特別地, 我們擬重點探討與正性樂學情緒和獎賞有關的腦區(如杏仁核以及黑質紋狀體通路和中腦皮層邊緣系統通路等腦內多巴胺通路)在英語的學習過程中的激活情況以研究和探測英語樂學者在學習和記憶英文過程中的心理獎賞特點。
2 研究方法
2.1 被試
19名來自北京各高校的具有較高英語樂學分數的大學生(9男 10女)參加本實驗(該被試群體是從總數為 70人的大學生中根據其英語樂學得分選取的高分被試, 詳情見后), 平均年齡 23歲(SD
=2.79), 排除英語、地理等可能對地名材料比較熟悉的相關專業。所選被試均為右利手, 視力或矯正視力正常, 無精神障礙和神經系統疾病。核磁掃描在清華大學生物醫學影像研究中心進行, 實驗已通過相關倫理委員會的批準, 且實驗之前所有被試均簽署知情同意書。另外, 被試如果在6個頭動參數(包括 3個方向的平動和 3個方向的轉動)的一個方向上超過2 mm或2 degrees即被排除。2.2 實驗材料
本實驗分為受試篩選和正式核磁實驗兩個部分。所采用的實驗材料詳述如下:
2.2.1 受試篩選問卷
自編《英語樂學問卷》。問卷分為英語樂學和英語厭學兩個維度, 其中樂學有 5個條目, 厭學有7個條目, 共12個條目。樂學維度正向計分, 厭學維度反向計分, 兩個維度的分數相加構成樂學問卷總分。題目樣例如下:“我在課余會抽出一定時間學英語” (樂學), “只有為了應付考試我才會學英語”(厭學)。樂學和厭學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系數分別為0.75和0.72。
《大學生學業倦怠問卷》(MBI-GS修訂版) (倪士光, 伍新春, 張步先, 2009)。問卷共 14個題目,包含情緒衰竭(4個題目)、譏誚態度(4個題目)、成就感低(6個題目)三個分量表。采用Likert 7點計分,“1”代表“從來沒有”, “7”代表“每天都有”。總量表的α系數為 0.81, 三個分量表情緒衰竭、譏誚態度、成就感低的α系數分別為0.77, 0.77, 0.81。
《焦慮自評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20個題目, 4級評分。計算標準分后, 標準分小于50分為無焦慮, 50~60分為輕度焦慮, 60~70分為中度焦慮, 70分以上為重度焦慮。
《抑郁自評量表》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含20個題目, 4級評分。計算抑郁嚴重指數(SDS 得分/總分 80), 指數在 0.50以下為無抑郁,0.50~0.59為輕微至輕度抑郁, 0.60~0.69為中至重度抑郁, 0.70以上為重度抑郁。
2.2.2 核磁實驗材料
采用經典的“學習?再認”實驗范式, 材料選用中、英文兩種語言的世界地名, 詞匯內容為使用頻次較低的城市及其對應的國家。例如, Conakry——Guinea、阿塔富——托克勞, 其中左側詞匯為城市,右側詞匯為國家。所有材料均選自《世界地名翻譯大辭典》 (周定國主編, 2008年1月出版), 英文詞長度范圍為4~10個字母, 中文詞長度范圍為2~4個漢字。
正式實驗分為 4個學習階段和 4個再認階段,兩階段交替呈現(見圖1)。每個學習?測驗階段包含12個小單元(trial) (中、英文各6個), 每個trial含有 3個英文或者中文詞對(但不會出現中、英文在一個trial中混搭的情況), 每個學習?測驗階段共呈現 36個詞對(中英各 18個), 4個學習階段共呈現144個詞對, 中英文各72對。再認階段的材料的一部分與學習階段相同, 如詞對中出現的城市與上一學習階段相同, 國家有 50%與學習時完全對應(即正確配對), 另外 50%的國家打亂了順序, 與城市不是對應關系(即錯誤配對)。再認階段的詞匯數量及分布方式與學習階段相同, 但項目的呈現順序被再次隨機化。在學習和再認階段, 中/英文學習材料的trial隨機交叉呈現, 最多連續出現2個相同語種的 trial。此外, 為避免熟悉性對學習效果的影響,中英文各選用不同材料, 即一個特定地名詞對如以中文形式呈現過, 則就不會再出現其英文形式,中、英文材料的選定在不同被試之間進行均衡。
2.3 實驗程序
使用自編《英語樂學問卷》、《大學生學業倦怠問卷》、《焦慮自評量表》(SAS)、《抑郁自評量表》(SDS)篩選被試。篩選標準如下:取英語樂學分數范圍(12~60分)的前 27%, 即樂學總分≥ 47.04, 且學業倦怠總分< 55, 焦慮標準分< 50、抑郁嚴重指數< 0.5的人作為樂學被試。只有所有問卷得分均符合標準才能參與正式核磁實驗。

圖1 核磁掃描流程
在核磁掃描前的準備階段, 首先采集被試的基本信息, 其中包括對中文學習的態度、大學入學成績排名、學期成績排名, 要求被試對這3個項目進行5點評分。之后在主試講完指導語之后針對核磁程序進行練習, 直到被試完全掌握實驗要求和按鍵反應方式為止。核磁掃描流程共 8個 run, 其中學習run 4個, 再認run 4個, 學習和再認run交替呈現。每個學習run呈現8 min, 再認run呈現7 min, 間隔休息1 min, 實驗總時長為68 min (見圖1)。采用拉丁方對實驗順序進行了平衡, 以排除順序效應。
學習和再認階段一個trial的流程如圖2。在學習階段, 屏幕首先會呈現學習線索(呈現時間為5 s),提示接下來將要學習的材料是英文還是中文, 然后,依次呈現3個詞對, 每個詞對的呈現時間為3 s, 隨之以3~5 s的jitter, 在詞對呈現時被試需要盡量記憶。詞對呈現完之后會出現一個情緒評定界面, 需要被試對記憶過程中體驗到的情緒進行4級評分(1厭惡, 2有點厭惡, 3有點喜歡, 4喜歡), 對應分別以左手中指、左手食指、右手食指、右手中指做反應。至此一個trial結束。在再認階段, 也是先呈現再認線索(呈現時間為5 s), 提示接下來測驗的是中文還是英文, 接著在詞對呈現時被試需要對依次呈現的3個詞對進行“是”或“否”的判斷。如果左側詞城市與右側詞國家與學習階段的完全一樣, 則按“3”(是), 否則按“4” (否)。每個詞對呈現時間為 3 s。詞對結束同樣要求被試對再認過程中體驗到的情緒做出4級評分。隨后會出現反饋界面, 共有兩種不同的反饋, 正反饋為:“恭喜!您在本組的成績超過了平均成績, 您將獲得額外獎勵”, 負反饋為:“抱歉!您在本組的成績低于了平均成績, 未獲得額外獎勵”, 兩類反饋隨機呈現, 正、負反饋的出現頻次在中、英文兩種條件下各占 50%。為防止被試對反饋生疑, 每個run 4種反饋類型的數量不完全均等。
核磁掃描結束后, 詢問被試是否質疑反饋的正確性, 如果猜到反饋是假的被試作廢。最后主試支付報酬, 實驗結束。

圖2 實驗流程圖
2.4 圖像采集
利用清華大學生物醫學影像研究中心的Philips Achieva 3.0T TX磁共振成像系統, 采用32通道線圈采集圖像。全腦功能像由T2*加權單次激發梯度回波的EPI序列獲得, 功能像相關參數如下:TR = 2000 ms, TE = 35 ms, FOV = 200 mm × 200 mm,FA = 90°, 64× 64 matrix, 30 層, 層厚 4mm, voxel size = 2.5 mm × 2.5 mm × 4.0 mm。結構像掃描參數:TR = 7.65, TE = 3.72, Flip = 8°, 180 層, 層厚 2 mm,層間距1 mm, FOV=230 mm×230 mm, voxel size=0.96 mm×0.96 mm×1 mm。通過E-prime 2.0軟件制作的程序實現trial的呈現與核磁掃描同步。
2.5 fMRI數據處理及分析
實驗所獲取的圖像數據采用加載于MATLAB2014a平臺上的SPM 8軟件包進行預處理及統計分析。對19名有效被試的fMRI數據分別進行時間校正、頭動校正, 將校正后的圖像空間標準化到標準的MNI (Montreal Neurological Institute)模板, 采用全寬半高值(FWHM)為 8 mm的高斯核函數及128 s的高通濾波進行空間平滑。
對預處理后的數據采用一般線性模型進行參數估計, 包括個體水平分析和組分析。在個體水平分析中, 學習階段定義了6個事件:(1)即將進入英文材料學習 trial的提示(簡稱英文學習提示) (每個英文trial包含1個該類項目/事件, 總項目數的理論值為24); (2)即將進入中文材料學習單元的提示(簡稱中文學習提示) (每個中文trial包含1個該類項目/事件, 總項目數的理論值為 24); (3)實際學習記憶英文地名詞對(簡稱英文學習) (每個英文trial包含3個該類項目/事件, 總項目數的理論值為 72); (4)實際學習記憶中文地名詞對(簡稱中文學習) (每個中文trial包含3個該類項目/事件, 總項目數的理論值為72); (5)學習英文材料之后的情緒評定(每個英文trial包含 1個該類項目/事件, 總項目數的理論值為24); (6)學習中文材料之后的情緒評定(每個中文 trial包含1個該類項目/事件, 總項目數的理論值為24)。
采用 SPM統計軟件中事件相關設計的建模方法, 將各個心理事件的起始時間定義為特定的刺激(如提示和地名詞對)開始呈現的時間。其中納入模型但未作進一步分析的事件為中/英文情緒評定及6個頭動參數。再認階段的各個認知信息加工事件的定義方法與學習階段相類似, 也包括中、英文記憶測驗提示各兩個事件, 中、英文記憶測驗各兩個事件, 情緒評定等, 與學習階段不同的是, 再認階段還包括對于每個trial的記憶成績的反饋, 包括中文正反饋、英文正反饋、中文負反饋、英文負反饋等幾類。納入模型但未作進一步分析的事件包含中/英文再認測驗、中/英文情緒評定及6個頭動數據。
在進行第二水平(second-level)的組分析時, 在個體水平分析獲得的各種關鍵對比(如“英文學習提示>中文學習提示”、“英文學習>中文學習”或“英文正反饋>中文正反饋”)的基礎上建立隨機效應模型。全腦分析的閾限為p
< 0.005 (uncorrected), 激活團簇體積(cluster size)大于或等于30個體素。此外, 使用Rest軟件中的AlphaSim對結果進行了多重比較校正, 閾限設定為p
< 0.05或p
< 0.005。全腦分析結果顯示:一些與心理獎賞、情緒喚起以及心理厭惡相關的腦區如中腦及黑質(substantia nigra, SN)、杏仁核以及腦島等在英文條件下的激活均要顯著大于中文的相應條件。根據全腦分析結果,我們選取中腦、黒質、腦島為感興趣區(regions of interest, ROI), 采用特定腦區(如中腦)的結構模板(WFU Pick Atlas Version 2.4)確定各個ROI, 并利用MarsBar軟件分別提取每一位被試的特定ROI在關鍵心理事件(如即將學習英文的提示)呈現后的24 s之內的時間信號變化值(每隔2 s (即一個 TR)一個數值, 24 s共 12個數值), 取每位被試在特定事件(如英文學習提示)相對于其對照條件(如中文學習提示)在時間信號變化過程中的最大差值與行為反應(如記憶成績和樂學分數)進行相關性計算。
3 結果
3.1 行為結果
對學習和再認兩個階段的情緒評定結果進行相關樣本 t檢驗, 結果如下:同一階段兩種語言之間對比發現, 學習階段英文情緒(M
= 2.87,SD
=0.51)評價要比中文(M
= 3.01,SD
= 0.55)更消極, 達到邊緣顯著,t
(18) = –2.05,p
= 0.055; 再認階段英文情緒評價(M
= 2.73,SD
= 0.58)則顯著低于中文(M
= 2.84,SD
= 0.57),t
(18) = –2.84,p
= 0.011。同一語言兩階段對比發現, 學習階段的英文情緒評價(M
= 2.87,SD
= 0.51)要高于再認階段(M
= 2.73,SD
=0.58),t
(18) = 2.21,p
= 0.04; 學習階段的中文情緒評價(M
= 3.01,SD
= 0.55)也要顯著高于再認階段(M
= 2.84,SD
= 0.57),t
(18) = 2.79,p
= 0.01。對再認階段的記憶成績分析發現, 英文記憶成績(M
=45,SD =
8.12)顯著低于中文(M
= 47.89,SD =
7.75),t
(18) = –2.70,p
= 0.015。將被試對中文學習的態度、大學入學成績排名、學期成績排名與《英語樂學問卷》總分、被試的英、中文記憶成績做相關分析。結果發現, 雖然“語文學科態度”一項平均分為4.12 (在評分體系中,1代表非常厭惡, 2代表比較厭惡, 3代表難以確定,4代表比較喜歡, 5代表非常喜歡), 大學入學成績、學期成績排名平均分分別為 2和 1.53(在評分體系中, 1代表前20%, 2代表20~40%, 3代表40~60%, 4代表60~80%, 5代表后20%)。但英文樂學總分與大學入學排名、學期排名均無顯著相關, 與被試對中文的態度也沒有顯著相關。即, 并非被試的英文樂學程度越高, 其中文樂學程度及總體樂學程度也隨之越高, 兩者沒有必然聯系。
3.2 腦成像結果
3.2.1 學習階段激活腦區

表1 學習階段英文線索與中文線索呈現激活的腦區
學習階段的英文線索相比于中文線索, 更多地激活了包括枕下回、枕中回、腦島、中央前回等在內的腦區。而中文線索相比于英文線索, 更多地激活了舌回等腦區(表1)。相比于中文線索, 學習階段的英文線索更多地激活了雙側的前部腦島, 激活圖見圖3。

圖3 學習階段英文線索>中文線索腦島激活
學習和記憶英文相比于中文, 更多地激活了枕中回、頂下小葉、頂上小葉、海馬、中央前回、楔前葉等腦區。而學習記憶中文比學習記憶英文更多地激活了顳中回、顳上回、舌回、梭狀回、楔前葉、扣帶回、額中回等腦區(表2)。

表2 學習階段英文記憶與中文記憶過程激活的腦區
3.2.2 再認階段激活腦區
再認階段的英文線索與中文線索相比, 更多地激活了舌回、枕中回、中央前回、楔前葉、顳中回、顳下回等腦區。而中文線索則比英文線索更多地激活了舌回、楔葉(表3)。除表3所激活的峰值點外,特別地, 英文回憶線索相對于中文線索的腦激活團簇的范圍還延伸到了黑質及中腦等區域, 因為這些區域與學業情緒關系密切, 因此我們也將這個區域的激活通過ROI的方法加以展示(圖4)。
英文正反饋比中文正反饋激活更強的區域有楔前葉、梭狀回、顳上回、顳中回和枕下回。中腦、黑質和杏仁核雖不是峰值點坐標, 但在該條件下均有激活(圖 5)。中文正反饋比英文正反饋激活更強的腦區有額中回(表4)。對負反饋分析, 英文負反饋比中文負反饋激活更強的腦區包括枕下回、枕中回、舌回、腦島、屏狀核。其中, 腦島的激活見圖6。中文負反饋減英文負反饋無顯著激活腦區(表5)。

表3 再認階段英文線索與中文線索呈現激活的腦區

圖4 再認階段英文線索>中文線索下中腦(左)、黒質(右)激活(p < 0.05, uncorrected)
3.2.3 ROI及相關分析結果
采用以上分析方法, 將所選取的感興趣區與《英文樂學問卷》總分計算皮爾遜相關, 采用Dunn–?idák校正方法調整顯著閾限(調整后的顯著閾限為0.034), 得到的結果如下:學習階段英文線索減中文線索在腦島的激活差異與英文記憶成績呈正相關(r
(17) = 0.50,p
= 0.030), 與問卷總分正相關(r
(17) = 0.50,p
= 0.031) (圖7中的A、B)。英文正反饋減中文正反饋在中腦的激活差異與樂學問卷總分呈邊緣正相關(r
(17) = 0.49,p
= 0.035); 與測驗階段英文提示減中文提示中觀察到的黑質激活水平正相關(r
(17)= 0.50,p
= 0.030), 與中腦的激活水平呈邊緣正相關(r
(17)= 0.49,p
= 0.035) (圖7中的 C、D、E)。英文負反饋減中文負反饋在腦島的激活差異與樂學問卷總分正相關(r
(17)= 0.57,p
=0.012) (圖 7中的 F)。
圖5 再認階段英文正反饋>中文正反饋條件的激活圖

表4 再認階段英文正反饋與中文正反饋激活的腦區

圖6 再認階段英文負反饋>中文負反饋條件下腦島激活
4 討論
本實驗對英語持有積極學業情緒的個體在中英文學習、測驗和反饋階段的情緒和腦活動特點進行了研究。行為結果表明, 無論是在學習還是在測驗階段, 被試在學習英文單元后的情緒評價都低于中文, 且英文的記憶成績也顯著低于中文, 這可能與中英文材料的學習記憶難度有關, 本實驗所使用是較為陌生且語義較不豐富的地名材料, 學習和記憶英文較之中文更加困難, 而這種難度上的差別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被試在學習中的情緒體驗和實際的記憶成績。

表5 再認階段英文負反饋與中文負反饋激活的腦區
在學習階段, 當遇到英文學習線索提示時被試表現出了更強烈的雙側前腦島的激活, 這可能與他們所體驗到的因面臨困難的學習任務而引起的壓力以及對認知努力的積極調動有關。腦島是表征情緒體驗的重要腦區, 它與邊緣系統如杏仁核、內嗅皮層及顳極存在緊密連接(Fudge, Breitbart, Danish,& Pannoni, 2005; H?istad & Barbas, 2008; Mesulam& Mufson, 1985; Stefanacci & Amaral, 2002), 并可在多種情緒誘發任務和線索類型下被激活(Kober et al., 2008; Singer et al., 2004; Wager & Barrett,2004; Wicker et al., 2003)。特別地, 研究表明:腦島與厭惡刺激識別密切相關(Hennenlotter et al.,2004; Jabbi, Swart, & Keysers, 2007; Phillips et al.,1997), 腦島毀傷的病人有可能失去識別厭惡刺激的能力 (Calder, Keane, Manes, Antoun, & Young,2000), 而元分析研究也表明, 厭惡刺激一致地激活了額下回和腦島, 因此腦島是腦內表征厭惡情緒體驗的關鍵腦區之一(Vytal & Hamann, 2010)。Lyons和 Beilock (2012)研究了具有數學焦慮的人在預期將要做數學任務及實際執行任務過程中的腦區激活, 結果發現, 數學任務線索的出現引起了背側后腦島(dorso-posterior insula)的激活, 但在實際做數學任務的過程中該區域并未激活。背側后腦島是反映疼痛感的重要區域(MacDonald & Leary,2005), 在數學任務提示階段激活了后部腦島, 這說明數學焦慮者在期待令其感到焦慮的任務出現時會產生心理厭惡。然而在本研究中, 我們發現即將學習英文的提示線索相對于中文激活了更多前部腦島而非后部腦島, 這一方面意味著由于材料的學習記憶英文材料難度較大的原因, 被試在學習的準備階段體驗到了更多的壓力和負性情緒, 而另一方面也意味著被試可能正在準備和調動更多的認知資源以應付即將出現的艱苦學習。與 Lyons和Beilock (2012)關于數學焦慮的研究發現后部腦島的激活不同, 我們關于樂學被試的研究發現了前部腦島在學習準備階段的激活。盡管腦島是表征軀體感受和情緒體驗的關鍵腦區, 但前部腦島與后部腦島也有著功能上的區分。一般認為, 后部島表征那些更加基本、更加初級的情緒體驗, 而前部腦島則表征經過認知調制之后的次級的情緒體驗(Craig,2009), 它也參與對由環境刺激或心境誘發的情緒狀態的調節(Dolan & Holbrook, 2001; Phillips,Drevets, Rauch, & Lane, 2003)。例如, 后部腦島被動地表征痛苦情緒, 前部腦島的激活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對痛苦情緒的控制和調節(Decety, 2011)。據此可以推測, Lyons和Beilock (2012)所研究的數學焦慮被試在面臨數學任務時所體驗到的純粹被動的痛苦, 因而這種體驗主要通過后部腦島來表征,而本實驗研究的是樂學被試, 盡管他們也在面對枯燥而艱難的學習任務時體驗到了壓力和負面情緒,但這也同時轉化成為了調節動力和其后的學習努力, 這就導致了前部腦島在學習記憶準備階段的激活。與上述假設相一致, 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對于英語樂學被試而言, 英文線索(相對于中文線索)所引發的左側前部腦島的激活不但與樂學問卷的總分呈正相關, 而且也與其后的記憶成績呈正相關,這說明如果一個人的英語樂學傾向越強, 則其在英語學習的準備階段所體驗到的學習壓力就會越大,其調動的認知努力就會越多, 而其后的學習記憶成績也會越好。

圖7 相關散點圖
與學習和記憶階段不同, 在再認階段, 當被試得到關于英文記憶成績的正反饋時相比于得到中文正反饋更多地激活了中腦區域和杏仁核。前人研究表明:中腦的激活與期待令人愉悅的味道(D'Ardenne, McClure, Nystrom, & Cohen, 2008;O'Doherty, Deichmann, Critchley, & Dolan, 2002),獲得金錢(Knutson, Taylor, Kaufman, Peterson, &Glover, 2005)及引發浪漫愛情的視覺刺激(Fisher,Aron, & Brown, 2005)有關; 而杏仁核在獎賞加工中所發揮作用也被許多研究所證實(Baxter &Murray, 2002; Cador, Robbins, & Everitt, 1989;Everitt, Cador, & Robbins, 1989; Everitt et al., 1999;Murray, 2007; Ramirez & Savage, 2007), 例如, 實驗發現潛在獎賞(McClure, Laibson, Loewenstein, &Cohen, 2004)甚至是潛在的毒品獎勵(Zald, 2003)都有可能激活杏仁核。因此, 可以認為被試在獲得英文記憶成績正反饋時中腦和杏仁核的激活反應了一種心理獎賞及相關情緒的產生和喚起。值得強調的一點是, 上述中腦和杏仁核的激活是在嚴格控制了對照條件的情況下獲得的, 亦即:無論是英文條件還是中文條件, 被試都獲得了正反饋而且按照實驗約定他們都將獲得額外的被試費作為獎勵, 但當被試得知自己在英文記憶上獲得好成績時產生的獎賞感及相關的情緒喚起仍然更加強烈, 這說明英語樂學被試對英語學習的成功更加看重。為了檢驗這種獎賞感究竟是否反應了樂學特質, 我們進一步計算了上述中腦激活在激活程度上與樂學分數之間的相關性, 發現二者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 這說明如果一個個體越樂學, 則其在獲得英文學習正反饋時所產生的心理獎賞感就會越強烈。
事實上, 樂學被試的這一特征不僅體現在獲得好的記憶成績反饋的階段, 甚至在當被試看到即將進行英文測驗的提示時, 相對于看到中文提示, 中腦黑質就會表現出更多的激活。前人研究發現, 中腦多巴胺神經元的活動不但與獎賞獲得有關, 而且負責編碼對獎賞的預期(Mirenowicz & Schultz,1996; Montague, Dayan, & Sejnowski, 1996; Schultz,Dayan, & Montague, 1997; Schultz, 2002), 因此, 在被試看到即將進行英文測驗的提示時就有包括黑質在內的中腦激活這一事實提示樂學被試甚至在實際得到有關英文學習的正反饋之前就產生了對于獎賞的預期, 這從某種意義上反映了樂學被試不但具有“樂學”的特點, 而且具有“樂考”的特點, 即他們樂于考試并期待著好成績。相關分析發現, 被試在記憶測驗提示階段英文相對于中文條件的中腦及黑質的激活水平與其在獲得正反饋時英文相對于中文條件的中腦激活呈正相關, 這從一定意義上說明了對獎賞預期的腦活動與實際獲得獎賞的腦活動之間存在關聯, 但我們沒有在記憶測驗提示階段英文相對于中文條件的中腦及黑質的激活水平與被試的樂學分數之間發現明顯的相關, 這意味著這種對獎賞的預期與樂學特質之間的關聯不如實際獲得獎賞與樂學特質之間的關聯那么密切。
那么, 樂學被試在得到英文正反饋時獎賞區和情緒區的激活是否有可能是由中、英文兩種任務在記憶難度上的差別所造成的呢?即:假設有難易不同的兩個任務, 那么, 人們在那個較難的任務上獲得成功之后其獎賞感可能會比較大, 這只是因為成功來之不易的緣故。本研究不能排除這一可能性,但從相關結果看, 英文正反饋減中文正反饋激活了更多獎賞區, 即被試在獲得英文正反饋時感到更加愉悅(且獎賞區的激活與樂學分數、測驗階段英文提示減中文提示中觀察到的黑質、中腦的激活水平正相關); 而且當被試得到關于英文記憶成績的負反饋時相比于得到中文負反饋更多地激活了雙側前腦島(且該腦島的激活水平與樂學特質即英文樂學問卷總分呈正顯著相關), 這表明被試在英文成績上獲得負反饋可能令他們感到不滿意并試圖調動更多的認知努力應對接下來的英文測驗。這些結果同時表明英文正反饋獲得的獎賞感也可能是由于樂學特質所致。此外換角度講, 對于難度更高的英文任務, 英語樂學者仍然愿意接受挑戰去學習,并在獲得正反饋后體驗到更強烈的獎賞感, 這恰好反映了英語樂學者的樂學特征。
作為一項在嚴格控制的實驗室條件下獲得的認知神經科學發現, 本實驗對于教育實踐也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它提示了積極學業情緒可能與人們的態度和價值觀念有關, 對于英語的喜愛和重視可以使同樣的正反饋產生更大的心理獎賞效應, 這說明了正或負反饋并不僅僅是一種客觀事實, 它也同時受到主觀態度和價值取向的調節, 乃是這種客觀成績與主觀價值傾向之間的交互作用形成了在樂學被試特定學習環境下的心理強化體系。而從英語樂學被試在英文記憶測驗提示階段就表現出中腦獎賞區的激活這一事實來看, 我們推測積極學業情緒可能與以往的成功經驗有關, 如果沒有以往大量的成功學習經驗, 樂學被試不可能在英語記憶測驗尚未實際實施之前就表現出對于獎賞的期待。但是,僅就本實驗而言, 我們也發現了一些令人感到隱憂的信息, 即樂學被試并未在實際的英語學習過程中產生更加積極的情緒體驗, 他們的樂學特點似乎只表現在更能對好成績產生積極的心理響應上, 這種重視學習結果而非享受學習過程的心理與腦認知特點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目前應試教育模式下“好學生”的學習動機特點, 但在得出這樣的結論之時, 我們也同樣需要考慮到以下這個事實,即:為了良好地控制實驗條件, 本實驗采用了較為枯燥的地名詞對作為學習材料, 因為這個原因, 樂學被試享受學習過程的認知特點也很有可能在這樣的實驗設置中不能被探測到, 因此, 未來的研究如欲澄清和確認這個問題, 則應將學習材料本身的趣味性和意義性納入探討和系統的研究。此外, 本研究僅對比了英文樂學者在學習英、中文過程中的認知特點和神經機制, 由于未能納入英文厭學組作為對照, 因此本研究所得結果不能推及英文厭學者在學習中、英文過程中的腦認知特點, 也難以回答英文樂、厭學者的在認知特點和神經機制上存在的差異這一問題。未來研究可進一步納入厭學組, 深入探究厭學大學生在學習英、中文過程中的認知特點及神經機制, 并對比樂、厭學群體的情緒特點及神經機制的差異。
5 結論
本研究通過對在英語樂學分數上得分較高的被試在學習陌生的中文或英文材料(外國地名)時的腦激活狀況的比較, 發現對英語的樂學是一種“苦中作樂”。這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首先, 英語樂學被試在學英文時所體驗到的積極情緒均明顯低于學中文, 腦成像的結果進一步顯示:在學習的準備階段, 相對于中文而言, 英文伴隨明顯的島葉的激活, 鑒于以往關于學業焦慮情緒的腦成像研究也發現了這個區域的激活, 我們推測這個區域的激活很可能反映了被試在準備學英文時體驗到了令人不快的壓力感并調動了認知努力。其次, 當英語樂學被試得到正反饋(即得知自己的學習測驗成績高于大多數人)時, 因學英文而得到的正反饋所導致的獎賞腦區明顯大于因學中文而得到的正反饋, 這說明英文學習成功能帶來更高的獎賞感。因此, 對于英語樂學者, 他們雖然在英語學習過程中體驗到了更多的痛苦, 但其成功也帶來了更大的心理獎賞,這種“痛并快樂著”的特征說明了“樂學”具有“理智感”的特征, 它并非一味地尋求和獲得快樂, 而是有苦有樂, 先苦后樂。
Baxter, M. G., & Murray, E. A. (2002). The amygdala and reward.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3
, 563–573.Cador, M., Robbins, T. W., & Everitt, B. J. (1989).Involvement of the amygdala in stimulus-reward associations:Interaction with the ventral striatum.Neuroscience, 30
,77–86.Calder, A. J., Keane, J., Manes, F., Antoun, N., & Young, A.W. (2000). Impaired recognition and experience of disgust following brain injury.Nature Neuroscience, 3
, 1077–1078.Craig, A. D. (2009). How do you feel-now? The anterior insula and human awareness.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10
, 59–70.D'Ardenne, K., McClure, S. M., Nystrom, L. E., & Cohen, J. D.(2008). BOLD responses reflecting dopaminergic signals in the human ventral tegmental area.Science, 319
, 1264–1267.Decety, J. (2011). Dissecting the neural mechanisms mediating empathy.Emotion Review, 3
, 92–108.Dolan, K. A., & Holbrook, T. M. (2001). Knowing versus caring: The role of affect and cognition in political perceptions.Political Psychology, 22
, 27–44.Dong, Y., & Yu, G. L. (2007).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an academic emotions questionnaire.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39
, 852–860.[董妍, 俞國良. (2007). 青少年學業情緒問卷的編制及應用.心理學報, 39
, 852–860.]Everitt, B. J., Cador, M., & Robbins, T. W. (1989).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amygdala and ventral striatum in stimulus-reward associations: Studies using a second-order schedule of sexual reinforcement.Neuroscience, 30
, 63–75.Everitt, B. J., Parkinson, J. A., Olmstead, M. C., Arroyo, M.,Robledo, P., & Robbins, T. W. (1999). Associative processes in addiction and reward the role of amygdalaventral striatal subsystems.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877
, 412–438.Fisher, H., Aron, A., & Brown, L. L. (2005). Romantic love:An fMRI study of a neural mechanism for mate choice.Th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Neurology, 493
, 58–62.Fredrickson, B. L. (2001). The role of positive emotions in positive psychology: The broaden-and-build theory of positive emotions.American Psychologist, 56
, 218–226.Fredrickson, B. L., & Branigan, C. (2001). Positive emotions.In T. J. Mayne & G. A. Bonanno (Eds.),Emotions: Current issu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pp. 123–151). New York:Guilford.Fredrickson, B. L., & Branigan, C. (2005). Positive emotions broaden the scope of attention and thought-action repertoires.Cognition and Emotion, 19
, 313–332.Frenzel, A. C., Pekrun, R., & Goetz, T. (2007). Girls and mathematics-A “hopeless” issue? A control-value approach to gender differences in emotions towards mathematics.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of Education, 22
, 497–514.Fudge, J. L., Breitbart, M. A., Danish, M., & Pannoni, V.(2005). Insular and gustatory inputs to the caudal ventral striatum in primates.Th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Neurology,490
, 101–118.Goetz, T., Pekrun, R., Hall, N., & Haag, L. (2006). Academic emotions from a social-cognitive perspective: Antecedents and domain specificity of students' affect in the context of Latin instruction.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76
, 289–308.Goetz, T., Frenzel, A. C., Hall, N. C., & Pekrun, R. (2008).Antecedents of academic emotions: Testing the internal/external frame of reference model for academic enjoyment.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sychology, 33
, 9–33.Goetz, T., Frenzel, A. C., Pekrun, R., & Hall, N. C. (2006).The domain specificity of academic emotional experiences.Th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Education, 75
, 5–29.Goetz, T., Frenzel, A. C., Pekrun, R., Hall, N. C., & Lüdtke, O.(2007). Between- and within-domain relations of students'academic emotions.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99
,715–733.Goetz, T., Preckel, F., Pekrun, R., & Hall, N. C. (2007).Emotional experiences during test taking: Does cognitive ability make a difference?Learning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7
, 3–16.Hennenlotter, A., Schroeder, U., Erhard, P., Haslinger, B.,Stahl, R., Weindl, A., … Ceballos-Baumann, A. O. (2004).Neural correlates associated with impaired disgust processing in pre-symptomatic huntington’s disease.Brain,127
, 1446–1453.H?istad, M., & Barbas, H. (2008). Sequence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 for emotions through pathways linking temporal and insular cortices with the amygdala.NeuroImage, 40
,1016–1033.Jabbi, M., Swart, M., & Keysers, C. (2007). Empathy for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s in the gustatory cortex.NeuroImage, 34
, 1744–1753.Knutson, B., Taylor, J., Kaufman, M., Peterson, R., & Glover,G. (2005). Distributed neural representation of expected value.The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25
, 4806–4812.Kober, H., Barrett, L. F., Joseph, J., Bliss-Moreau, E.,Lindquist, K., & Wager, T. D. (2008). Functional grouping and cortical-subcortical interactions in emotion: A metaanalysis of neuroimaging studies.NeuroImage, 42
, 998–1031.Lu, J. M. (2009). On adolescent affective quality.Educational Research,
(10), 30–36.[盧家楣. (2009). 論青少年情感素質.教育研究,
(10),30–36.]Lu, J. M., Liu, W., He, W., Wang, J. S., Chen, N. Q., & Xie, D.F. (2017). The status quo of China's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affective diathesi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49
, 1–16.[盧家楣, 劉偉, 賀雯, 王俊山, 陳念劬, 解登峰. (2017). 中國當代大學生情感素質的現狀及其影響因素.心理學報,49
, 1–16.][盧家楣. (1986). 對情感的分類體系的探討.心理科學通訊,9
(4), 60–64, 59.]Lyons, I. M., & Beilock, S. L. (2012). When math hurts: Math anxiety predicts pain network activation in anticipation of doing math.PLoS One, 7
, e48076.Ma, H. X., Nie, S. Y., & Su, S. J. (2010). College students'academic emotions in examination situation.Studies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8
, 201–207, 222.[馬惠霞, 聶勝昀, 蘇世將. (2010). 大學生考試情境下的學業情緒.心理與行為研究, 8
, 201–207, 222.]MacDonald, G., & Leary, M. R. (2005). Why does social exclusion hur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and physical pain.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1
, 202–223.McClure, S. M., Laibson, D. I., Loewenstein, G., & Cohen, J.D. (2004). Separate neural systems value immediate and delayed monetary rewards.Science, 306
, 503–507.Mesulam, M. M., & Mufson, E. J. (1985). The insula of Reil in man and monkey. In A. Peters & E. G. Jones (Eds.),Association and auditory cortices
(pp. 179–226). New York, USA: Springer.Mirenowicz, J., & Schultz, W. (1996). Preferential activation of midbrain dopamine neurons by appetitive rather than aversive stimuli.Nature, 379
, 449–451.Montague, P. R., Dayan, P., & Sejnowski, T. J. (1996). A framework for mesencephalic dopamine systems based on predictive Hebbian learning.The Journal of Neuroscience,16
, 1936–1947.Murray, E. A. (2007). The amygdala, reward and emotion.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1
, 489–497.Ni, S.G., Wu, X.C., Zhang, B.X.(2009).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undergraduates academic burnout scale and its structure.China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17
(7), 827–830.[倪士光, 伍新春, 張步先. (2009). 大學生學業倦怠問卷的信效度驗證及其結構.中國健康心理學雜志, 17
(7),827–830.]O'Doherty, J. P., Deichmann, R., Critchley, H. D., & Dolan, R.J. (2002). Neural responses during anticipation of a primary taste reward.Neuron, 33
, 815–826.Pekrun, R., Elliot, A. J., & Maier, M. A. (2006). Achievement goals and discrete achievement emotions: A theoretical model and prospective test.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98
, 583–597.Pekrun, R., Goetz, T., Titz, W., & Perry, R. P. (2002a).Academic emotions in students’ self-regulated learning and achievement: A program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37
, 91–105.Pekrun, R., Goetz, T., Titz, W., & Perry, R. P. (2002b).Positive emotions in education. In E. Frydenberg (Ed.),Beyond coping: Meeting goals, visions, and Challenges
(pp.149–174). Oxford, UK: Elsevier.Perry, R. P., Hladkyj, S., Pekrun, R. H., & Pelletier, S. T.(2001). Academic control and action control in the achieve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A longitudinal field study.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93
, 776–789.Phillips, M. L., Drevets, W. C., Rauch, S. L., & Lane, R.(2003). Neurobiology of emotion perception II: Implications for major psychiatric disorders.Biological Psychiatry, 54
,515–528.Phillips, M. L., Young, A. W., Senior, C., Brammer, M.,Andrew, C., Calder, A. J., … David, A. S. (1997). A specific neural substrate for perceiving facial expressions of disgust.Nature, 389
, 495–498.Ramirez, D. R., & Savage, L. M. (2007). Differential involvement of the basolateral amygdala, orbitofrontal cortex, and nucleus accumbens core in the acquisition and use of reward expectancies.Behavioral Neuroscience, 121
,896–906.Schultz, W., Dayan, P., & Montague, P. R. (1997). A neural substrate of prediction and reward.Science, 275
, 1593–1599.Schultz, W. (2002). Getting formal with dopamine and reward.Neuron, 36
, 241–263.Singer, T., Seymour, B., O'doherty, J., Kaube, H., Dolan, R. J.,& Frith, C. D. (2004). Empathy for pain involves the affective but not sensory components of pain.Science, 303
,1157–1162.Stefanacci, L., & Amaral, D. G. (2002). Some observations on cortical inputs to the macaque monkey amygdala: An anterograde tracing study.Th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Neurology, 451
, 301–323.Villavicencio, F. T., & Bernardo, A. B. I. (2013). Positive academic emotions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regulation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83
, 329–340.Vytal, K., & Hamann, S. (2010). Neuroimaging support for discrete neural correlates of basic emotions: A voxel-based meta-analysis.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22
,2864–2885.Wager, T. D., & Barrett, L. F. (2004). From affect to control:Functional specialization of the insula in motivation and regulation. Published online at PsycExtra (http://www.apa.org/pubs/databases/psycextra)
Wicker, B., Keysers, C., Plailly, J., Royet, J. P., Gallese, V., &Rizzolatti, G. (2003). Both of us disgusted inmy
insula:The common neural basis of seeing and feeling disgust.Neuron, 40
, 655–664.Yang, X. H., & Xu, S. Y. (2014). A longitudinal study on poor students' academic emotions in English learning.China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22
, 764–766.[楊憲華, 徐淑燕. (2014). 英語學差生學業情緒變化發展的追蹤.中國健康心理學雜志, 22
, 764–766.]Yu, G. L., & Dong, Y. (2006). A research of academic emotions among adolescents with and without learning disabilities.Psychological Science, 29
, 811–814.[俞國良, 董妍. (2006). 學習不良青少年與一般青少年學業情緒特點的比較研究.心理科學, 29
, 811–814.]Yu, G. L., & Dong, Y. (2007). The effect of emotions on selective and sustained attention in adolescents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39
,679–687.[俞國良, 董妍. (2007). 情緒對學習不良青少年選擇性注意和持續性注意的影響.心理學報, 39
, 679–687.]Zald, D. H. (2003). The human amygdala and the emotional evaluation of sensory stimuli.Brain Research Reviews, 41
,88–123.Zhao, S. Y., Cai, T. S., & Chen, Z. J. (2012). A research on achievement emotions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school-work achievement.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0
, 398–400.[趙淑媛, 蔡太生, 陳志堅. (2012). 大學生學業情緒及與學業成績的關系.中國臨床心理學雜志, 20
, 398–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