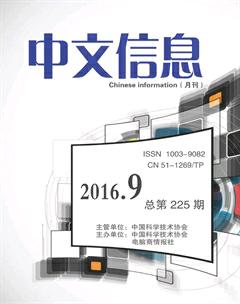“嚴重超速”入刑之商榷
摘 要: “嚴重超速”入刑,存在有違刑法明確性的要求,有違只處罰當罰行為的原則,有違罪責刑相適應原則,有違故意犯罪原則。司法上存在執行成本過大的問題,社會效果上有可能阻礙民生福祉的促進,故對“嚴重超速”入刑持保留態度。
關鍵詞:“嚴重超速”入刑 罪刑法定原則 司法資源配置 行政處罰
中圖分類號:D9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82(2016)09-0348-02
《刑法修正案(九)》將嚴重超速行為入刑以來,引起了社會輿論的廣泛關注,支持與反對皆有之。支持者認為,在“醉駕”入刑以后,有效遏制了酒后駕車肇事行為,但超速行為仍然頻發,本次修正案將嚴重超速行為入刑,對于打擊此類“馬路殺手”將起到很大助益。反對者認為,雖然重大交通安全事故中總是少不了超速的身影,嚴抓嚴管超速行為符合情理,但嚴抓并非僅僅是入刑,現在急于入刑的做法比較草率,隨著醉駕入刑和酒駕現象的明顯減少,這一治理手段又成了應急式立法的典型。動輒入刑的做法,使得有關道路交通安全法規被弱化,被架空。本文對入刑持保留態度,以下詳述之。
一、立法上的商榷之處
首先,刑法的明確性要求,規定犯罪的法律條文必須清楚明確,使人能確切了解犯罪行為的內容,準確地確定犯罪行為與非犯罪行為的范圍,以保障刑法規范沒有明文規定的行為不會成為該規范適用的對象。從刑修案九第八條來看,超速多少算是嚴重超速?規定時速中的“規定”指什么?規定時速是全國性規定還地區性規定,是永久規定還是暫時規定?以上問題,皆無明確規定,有違刑罰法規的明確性原則。不明確的刑法意味著有意或者無意的抹殺民意。并且,由于刑法條文的不明確,導致不具有預測可能性,公民在行為時難以明白其行為的法律性質。更嚴重的是,立法上的不明確,為國家機關恣意侵犯自由找到了形式上的法律根據,最終限制了公民自由。
其次,刑罰法規只能將具有處罰根據或者值得科處刑罰的行為規定為犯罪,從而限制立法權。從法條上看,“嚴重超速”入刑屬于處罰了不當罰的行為。因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法》與《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都出于地區與時間的不同而對機動車車速進行了不同限定,也對超速行為明確規定了罰則。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法》第99條規定:“有下列行為之一的,由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處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罰款,其中第(四)項規定,機動車行駛超過規定時速百分之五十的;”該條并未提及“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也即嚴重超速行為已經被規定為行政違法行為,受行政處罰即可。該規定已經表明了行政法規對嚴重超速或者是特別嚴重超速都有了不同的處罰應對措施。在治理成效上,《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法》實施以來,對于嚴重超速行為并沒有出現失控局面,有效了維護了道路交通安全。同時,一些重大事故中出現的嚴重超速造成嚴重后果的情形,有一部分是由于醉駕、吸毒后駕駛等原因造成的,單純嚴重超速的行為較少見。在行政法對“嚴重超速”規定了行政處罰之后,刑法又規定了刑事處罰,將會出現“一國三公,吾誰適從”的局面。
再次,有違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刑修案九將“在公路上從事客運業務嚴重超過規定時速行駛的”與“追逐競駛,情節惡劣的”、“醉酒駕駛機動車的”并列放入法條中,并共同適用“處拘役、并處罰金”,使人誤認為這三種行為在法益侵害上等同。如果與“追逐競駛,情節嚴重”相較,“在公路上從事客運業務嚴重超過規定時速行駛的”的危害性是遠遠低于前者的。嚴重超速對于不同人有著不同的危險,因為駕駛員的駕齡、反應速度、駕車嫻熟度都是影響車速的因素。而“嚴重超速”入刑顯然是為了保護公路交通安全法益和客車上人員的人身安全法益。如果在車流或人流較少的城市或者車流較少的高速公路上,雖然嚴重超速,但只要緊急制動平穩,基本上是可以保證車上人員安全的。然而,追逐競駛的情況下,駕車人在客觀上體現出了賽車的性質,主觀上表現出激動與激情的非理性狀態,同時用“情節嚴重”做為入刑的條件,那么,在構成危險駕駛罪的情況下,“追逐競駛”的法益侵害性都是高于“在公路上從事客運業務嚴重超速的”。在立法的宏觀層面上,危險駕駛罪所列舉的幾種行為方式,法益侵害性高低各不相同,幾種法益侵害性程度不同的行為,卻處以相同的刑罰,恐怕很能符合罪責刑相一致原則。
第四,危險駕駛罪所列舉行為的主觀要件不同。根據張明楷教授的觀點“故意與過失是確定入罪的要件,故意與過失之間的關系,是回避可能性的高低度關系,是責任的高低度關系,也是刑罰意義上的高低度關系,因而是一種位階關系。”通說認為,危險駕駛罪的主觀方面是故意,所以,過失不是該罪的主觀狀態。醉酒駕駛狀態下,從原因自由行為理論,可以認定為故意犯罪。追逐競駛狀態下,行為人明知“行為會對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重大財產安全以及公共交通安全產生危險或造成侵害結果”,故也是故意。然而,“嚴重超速”可能是過失,例如,超速可能涉及道路交通管理上的原因,某些地方限速設置不合理,交通提示牌不醒目,此時應為“過失”;“嚴重超速”也可能是意外事件,例如,汽車儀表盤出現故障或者損壞,不能正確指示時速,駕駛員主觀上對超速無法認識,但客觀上已經超速,此時是意外事件。將出現“嚴重超速”的結果做為入刑的標準,是將嚴格責任帶入現行刑法,這違背了我國刑法堅持的主客觀相一致原則,沖擊了刑法基本原則的穩定性,進一步限制了公民自由。
二、司法上可行性的商榷
從實施法律的成本來看,將嚴重超速入刑,可能不會起到行政處罰手段產生的抑制此類行為的效果。有效實施法律有賴于多種現實因素,其中司法資源的配置問題是主要因素。行政處罰具有及時性,交警當場發現,可以當場處罰。然而,刑罰具有滯后性,難以及時處罰。并且,較之于行政程序法,刑事訴訟法對證據的收集、保存、證明程度、處理程序的要求極為嚴格。立案之后,刑事案件還要經過偵查、起訴、一審、二審等既耗時又復雜的訴訟程序,這將使得司法成本迅猛增加與效率嚴重降低。同時,嚴重超速入刑后,交通警察必然也要參加到刑事訴訟進程中,那么,交警的執法成本會迅猛增加,執法效率會大大下降,而執法效率的下降又會影響到對嚴重超速的查處概率,查處概率的降低,會增強嚴重超速違法者的逃避法律制裁的僥幸心理,嚴重超速行為反而有可能增多。同時,從國家機關執法的角度來看,在某個時期內,集中主要司法資源來嚴肅處理嚴重超速行為并不罕見,但長期的高強度執法與投入高昂的司法資源來處理嚴重超速行為,必然會左支右絀,心有余而力不足。即使如“嚴打”、“春雷行為”之類也只能維持短暫的時間,主要的司法資源肯定會重新分配到其他嚴重社會問題與重案要案中。例如,醉駕在《刑修案(八)》通過之后的短暫時期內,確實顯著降低。然而當社會對輿論對醉駕的關注度降低,執法機關出現疲態和執法力度下降后,醉駕現象又報復性的反彈。在現有的司法資源大體不變的情況下,行政處罰的可行性要遠遠大于刑罰的可行性,或者說,刑罰處罰“嚴重超速”可能會在實行執法中成為一紙空文,高昂的成本會迫使執法的放棄。同時,從預防效果上來看,行政處罰的及時性具有的明顯的優點,因為,除非潛在罪犯認為自己可能會被逮住,否則,以嚴厲的處罰作為震懾手段是沒有大作用的。處罰或者說預防是否有效,在于及時性,而非嚴厲性。
三、社會效果上的消極影響
“嚴重超速”入刑,也可能導致難以促進民生福祉。如上所述,嚴重超速的入刑,短期內也許會降低此類行為,然而要想長期保持執法力度是不現實的,此類行為反而會有所增加。并且,如果用刑罰來處罰偶然被查處的嚴重超速行為,這種選擇性執法的方式,必然會導致處罰嚴重不公平。一項法律,只能被選擇性的執行,少數被抓的人鳴冤叫曲,多數逃避處罰的人幸災樂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又如何落實呢?
再者,行政處罰較之于刑罰更寬容,為違法者提供了改善改正的可能,與違法的程度相適應,且不會導違法者社會生活的困難。而刑罰會人為制造持續的犯罪者、反社會者,反而不利于社會和諧。其實,眾多從事客運的駕駛員處于社會基層,是依靠駕駛技能自食其力,勉強維持生存的普通勞動者,嚴重超速入刑后,這些人就會成為受到刑事處罰的罪犯,未來重返社會與謀生都將困難重重。良法是善治的前提,如果法律的制定過程本身充滿了隨意性,缺乏科學、民主和詳細的審議,不僅善治無法實現,甚至在某些情況下還陷入了韋伯所說的“理性的牢籠”,無力回應社會的各種問題,反而加劇了問題。
四、抑制超速的有效措施
不可否認,我國汽車超速現象非常多發。超速行為對公共安全的危險性實際上比醉駕與追逐競駛更嚴重。
如所周知,超速行為不僅對路橋會造成嚴重損壞,還會導致重大交通事故。我國每年在支付的養路費中有三百多億元用來修復車輛超速對公路造成的損害,交通事故中超過70%是由于超速引起的,一半以上的重大傷亡交通事故由于超速而導致,超速是道路交通中的首要殺手。盡管很多人想到用類似醉駕入刑的方式來抑制超速行為,然而,法學界中很多人對危險駕駛罪的設立是持反對與質疑的。刑修案(八)實施以來,危險駕駛罪成為危害公共安全罪之一,但關于危險駕駛罪設立必要性的爭議仍然存在。法學界對設置危險駕駛罪的合理性、科學性仍在商榷中。對于嚴重超速入刑,已如上文所言,恐怕并非能夠解決道路交通安全領域的問題,我們應當在刑法以外的思路上考慮如何有效的抑制、減少超速行為,努力保護公民的生命健康以及財產安全。
首先,應當突破僅僅入刑的思路,在思想上破除“刑法萬能主義”的觀點。在大眾中存在著指望通過嚴刑峻法的立法、設置新的罪名、加大原罪名的刑罰來處理或抑制某些嚴重的違法犯罪現象。然而,歷史與現實告訴我們,在立法上入罪或者加重其他法律的處罰強度,對違法犯罪行為的威懾效果實在是有限的,在某些特定的條件下也許起著相反的作用。立法是一項科學活動,自然應該沿循基本的法教義學原理與社會運作的客觀規律。良好的動機未必帶來善良的結果,出于好意在立法上的入罪,可能只是一廂情愿,與初衷背道而馳。
其次,行政執法的力度強,則治理超速的效果好,反之亦然。從治標的角度來看,執法的力度是某種違法犯罪行為下降的首要因素。我國有很多地方政府曾經采取過或者正在采取無縫隙、拉網式的集中治理危害道路交通安全的專項執法行動,通常在集中執法期間,抑制效果會十分顯著。因此,即使依然用行政法規來規制超速行為,只要加大行政執法力度,或者階段性的強化行政執法,增加查處違法行為的概率,同樣能夠達到良好的預防、抑制的法律效果。
第三,在治本的角度看來,只有落實了其他民生政策才能取得治理超速的穩定持續的效果。集中專項治理行為雖然能在短期內取得顯著的抑制效果,但執法資源非常有限,運動式的集中專項執法是難以為繼的。有限的執法資源必然會被每年面臨的不同的突出問題而有所調整與重新分配。運動式執法一旦放松,超速就會反彈。用法律規制超速行為當然不可缺少,但僅僅是治標之策。超速是客運、物流中長期伴隨的現象,只有找到了經濟社會的客觀運行規律,才能從源頭上治理超速。例如,在“河南天價過路費案”中表現出了“只有超速超載才能賺錢,不然就虧本”,這是一個關乎客運人員最基本的生存需求的問題,不解決這樣的問題,超速超載就不可能根治。生存的壓力會完全壓倒法律的威懾。只有當局切實減少收費公路,降低收費額度,遏制違規收費、違規轉讓公路經營權,嚴厲打擊公路建設與公路收費中的腐敗犯罪現象,才能治本,這也同時有利于民生。
綜上,立法者希望通過嚴刑峻法來提高公民的風險意識以達到抑制危險駕駛的目的,這種做法正是重刑主義的思路所致。“嚴重超速”行為確實要嚴厲打擊,但入刑不是唯一手段,只能是最后的手段。正如德國著名刑法學家李斯特所言:"在與犯罪作斗爭中,刑罰既非唯一的,也非最安全的措施",我們理應用好現有的行政法律法規,警惕刑法萬能主義,切實保障公民自由與民生福祉。
參考文獻
[1]齊燕:交通違法行為入刑“擴容”是懲罰更是關愛,《公民導刊》,2015(12)
[2]戴帥:淺談“危險駕駛”入刑,《道路交通管理》,2015(10)
[3]郭小亮:新型危險駕駛罪的理解與適用,《江西警察學院學報》,2016(1)
[4]莉瀟:高危駕駛行為的刑法規制問題,《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0(5)
[5]胡小義:風險社會視閾下危險駕駛罪研究,《江西理工大學學報》,2015(3)
[6]陸婷:危險駕駛罪與刑的適用研究,《沈陽師范大學學報》,2012(5)
[7]樊耀東:危險駕駛罪研究,《北方工業大學學報》,2012(9)
[8]沈玉忠:交通肇事的犯罪化與非犯罪化之思考,《南陽師范學院學報》,2008(7)
作者簡介:蔣捷(1989-),男,漢族,江蘇南京,東南大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