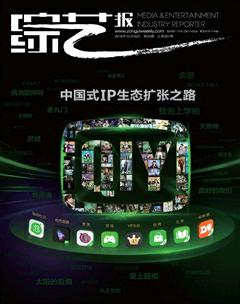淺談電影的文化屬性
趙軍
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協會副會長。
前幾天某座談會上,有專家指斥當下一些影片浮躁,毫無價值,“不能憑這樣的影片完成走出去任務”云云。筆者在現場表態:不必過早宣布某些電影是否有價值,現在是中國翻天覆地的時代,是五千年中華文明未曾有過的變局,過若干年后再看,當下影片很有可能就是這個時代最生動的詮釋,會變成一種記憶,提供很多有價值的歷史記錄。今天爭議越大的影片對明天也許越有價值。
關注一部影片好壞,評判它是否浮躁低俗,都不如去關注其文化屬性。很多人往往不注意文化屬性的作用,評來評去都似隔靴搔癢。一說起中國電影走出去,就認為是外國不理解中國現實,殊不知即使在國內,中國人也未必都了解中國人。文化鴻溝首先是在內部,在中國人自己當中。
解開這一切的謎底就在于文化屬性的整個生成、演變和蛻變中,尤其是在發生激烈碰撞的社會轉型期的今天。電影是社會生活的銀幕折射,就其娛樂本性而言,本不需要過于深刻的分析,偏偏專家們要從中找出最深刻的哲理來。也好,不妨就此剖析當下諸多電影現象,找出它們背后的文化屬性才是硬道理。
前些天,在筆者參加的第十三屆中國院線看片會暨市場研討會上,會議代表們有幸在同一天內遇到三位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有份量的導演。
首先是《地球四季》的編劇、導演,法國紀錄電影導演雅克·貝漢。雅克-貝漢溫文爾雅,為大家講述《地球日季》拍攝初衷,關于人如何珍惜動物、如何意識到地球上諸種生物的和諧共處,以及生物鏈的此消彼長和生命律動。雅克-貝漢身上彰顯著法國文化氛圍、歐洲文化氛圍和世界文化氛圍。
晚上,另一位知名導演登場,他就是“粉絲大亨”郭敬明。他推薦的是新片《爵跡》。郭敬明是當代的一個文化符號,據說他粉絲過億,是80后、90后的代表。這也是一種文化,一種無需深刻但已經一呼百應的文化。只是沒人愿意深究郭敬明身上所散發出的當代文化屬性。這種文化屬性在于以物質時代為背書向傳統世界發出的顛覆叫囂——來勢洶洶并最終直面市場,挾巨大投資而不畏一搏,這就是郭敬明或者愿意為他“沖鋒陷陣”的粉絲們的狂熱文化。筆者以為《爵跡》在制作上算得上美文,只是沒有深度。唯文化屬性不以深淺論英雄,只需區分它屬于哪一類文化即可。
第三位上臺的導演是武漢電視臺紀錄片導演陳為軍。兩分鐘之前他的影片《生門》剛放映完,影片以犀利現實主義風格,表達對于人間痛苦的深刻情懷與無解的現實困惑。很少有陳為軍這樣直面民生的導演,很少聽到一位導演說“這部影片就是人民電影”。其文化屬性為何?是中國真正的知識分子最傳統的悲天憫人情懷。《生門》從日位早產兒產婦在醫院逐一走過生命鬼門關的經歷,拍出現實當中復雜、艱難、憂傷的悲歡離合故事,宛如一部長篇生命交響曲。
一天當中遇見三位文化屬性截然不同的高手,貌似他們才是打開這些電影所蘊藏的精神領地的鑰匙。《生門》是以普通人情懷關切地注視世界,《爵跡》是以“世外超人”眼光看待世界,《地球四季》則是以自然胸襟包容世界。文化屬性無法深藏,編導身上的創作屬性便是文化屬性,誰有怎樣的文化屬性,就能拍出怎樣的電影。
文化屬性是今天這個發生著巨大社會轉型的中國最深刻的沖突戰場。它豐富著人的靈魂,同時對人們潛移默化。也許明天我們還會同時在市場上接受更多文化屬性相反的影片。不管承認與否,文化屬性就在這里,在每一部電影創作、傳播、接受、批評當中,這就是當下之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