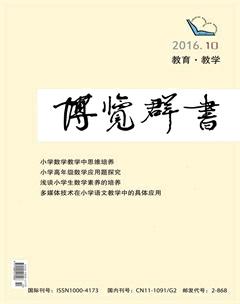《聊齋志異》中的女性形象欣賞
陳群萍
小時候我就喜歡看《聊齋》故事,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美麗的花仙狐妖,她們總是讓我產生神奇的想象。讀大學以后對《聊齋志異》有了更多更全面的了解,但異彩紛呈的女性仍然是我心底的最愛。我想這些女性形象之所以會讓人迷醉是因為蒲松齡善于用他的生花妙筆把讀者引入他所創設的藝術境界。
蒲松齡拋開對人物表面的,浮泛的外表特征的描寫,把主要精力集中在能體現人物性格的行為、語言的細致勾勒上,使得那一個個女性的容音笑貌栩栩如生,宛在目前。如《小謝》中開頭小謝與秋容戲弄陶生的情景:先藏書又送還案上,“生寂然不動,長者翹一足踹生腹,少者掩口匿笑”“女近左以左手捊鬢,右手輕批頤頰作小響!”“以細物穿鼻”、“鶴行鷺伏”、“飄竄”……一個接一個動作的出現,生動地把兩個鬼丫頭那種活潑伶俐、調皮的性格,非常強烈而又深刻地印進了我們的腦海。
《聊齋志異》中的女性的語言非常個性化,這些個性化的語言使她們畢妙畢肖地出現在我們的眼前,讓我們不但能看而且能聽地全方位地感受人物,如《嬰寧》里面嬰寧的語言。嬰寧先是在上元節發現王子服死死盯住自己,“顧婢曰:個兒郎目灼灼似賊!”仿佛不知道他是在看自己,初步表現了她的天真。后來王子服等至其家與她的一段對話更是令人絕倒。王子服與嬰寧在花園中相見,王拿出上元節嬰寧遺落的梅花向她示愛,她卻渾然無知地說:“待郎行時,園中花當喚老奴來,折一捆負送之。”她以為王留花的原因只是象她一樣愛花,當王告訴她“非愛花,愛拈花之人耳”她全然不理解“對花思人”的思戀之情說:“葭莩之情,愛何待言。”當王子服告訴她他想的是“夜共枕席“的夫妻之愛時,仍不明白所指為何“府思良久,曰:‘我不慣與生人睡”,可見她天真純潔得近手癡憨,后來嬰寧甚至還告訴母親說:“大歌欲我共寢”王子服窘得拼命掩飾,因小語責女,告訴她“此背人語。”嬰寧卻說:“背他人,豈得背老母?且寢處亦常事,何諱之?”我想讀到這兒絕大部分的讀者都會在發出會心的微笑的同時發出這樣的感嘆:“世上競有這樣天真的女子!”《聊齋》里的女性的語言是“能使讀者由說看出人來的”(魯迅語)。
蒲松齡筆下的婦女形象是富有層次感,血肉豐滿的非常耐看。如《小翠》中的小翠是一個美麗善良、堅強果敢、心思縝密、多情聰慧的女狐,而她的這種形象并非一開頭就呈現在我們面前的,而是一步步,一層層展現主來的。開頭我們只看到她的美麗,王太常贊她為“仙品“。與元豐成親后”能窺翁姑喜怒博得了公婆的歡心,我們看到了她的聰慧善良;接下來我們有看到了她的天真活波,嫁了一個傻丈夫卻從來沒有表現出一點愁苦,整天帶著丈夫和丫頭們玩耍,把自己的院子變成了一個游樂場。她果敢堅強,踢布球時受到夫人詬罵,她一聲不吭,也沒有絲毫畏懼的樣子。她把元豐扮成天子被公公知道了,她關起門來“任其詬厲”當公公要用斧頭破門而入時,她在房內含笑告訴公分說:“翁無煩怒,有新婦在,刀鋸斧鋮婦自受之,必不令貽害雙親,翁若此,是欲殺人滅口耶?”這些話既是出于她的自信,更表現出她的堅強與聰慧,她不動聲色,鎮定自若地讓一切計劃逐步進行,把陷阱藏在游戲之下,讓公公的仇敵自取滅亡。從她乞求夫人寬宥無豐,及出走后用心良苦地為元豐安排另一樁婚姻,等幾件事來看她又是善良多情的。
蒲松齡善用對此,映襯的手法來刻畫人物。如《張鴻漸》中方氏與狐仙施舜華同為張鴻漸的妻子都美麗,聰明、善良,但作者都能根據她們的不同的身份遭遇從中寫出不同,真可謂兩花爭艷,各具特色。諸同學約張鴻漸一起為同學范生鳴冤時,方氏勸他說:大凡秀才作事,可以共勝,而不可以共敗,勝則人人貪天功,敗則紛然瓦解,不能成聚。今勢力世界,曲直難以理定;君又孤,脫有翻覆,急難者難也!從這段話可以看她在不平的世事面前取明哲保身的態度,但這當中有對秀才的洞徹肺腑的了解,有對世道入木三分的觀察,有對丈夫知冷知熱的關懷,這表明她是一個世情練達、性格深沉、感情內斂、眼光敏銳的人。狐仙施氏在與張成親之時雖表示不介意其有妻、并說“此亦見君誠篤”似乎很明理。但當張鴻漸要求回家探望妻子時,她就不高興了,當張曉之以理時她說:“妾有褊心,于妾愿君之不忘,于人愿君之忘之也。”并幻化出方氏母子,以試驗張對自己的情感,這表明她在多情中又帶著不加掩飾的妒忌和頑皮狡滑。張鴻漸在離家三年后初次返家,把自己的遭遇“具言其詳”時方氏對他有外遇的事未置一詞,方氏是機智寬厚的,正符合當時社會道德對女性的要求,正如作者開篇說的是“美而賢”。文中有張鴻漸回家與真假方氏見面的情景描寫更使兩者區別開來了。與假方氏見面是“近以兩指彈扉,內問為誰,張是道所來,內秉燭啟關,真方氏也。兩相驚喜,握手入帷……方縱體入懷曰:君有佳偶,想不復念孤倉中有零涕人矣”,與真方氏見面是“逾垣叩戶,宛者前狀,方氏驚起,不信夫歸,詰證確實,始挑燈鳴咽而出。既想見,涕不可抑……方氏不解曰:‘妾望君如歲,枕上啼痕固在也,甫能相見,全無悲戀之情,何以為心矣。”一方面假方氏一問知張鴻漸就“秉燭啟關”而真方氏則“驚起,不信夫歸,詰證確實”才挑燈哭著出來“涕不可抑”只有遭受過迫害,折磨、整天擔驚受怕,歷經滄桑的真方氏才會有這樣的警惕性,才會將信將疑,反復盤問;另一方面作為封建社會的婦女因受禮教的束縛,即使在丈夫面前也要保持莊尊自持的樣子,不可能象假方氏那樣“兩相驚喜,握手入帷”主動地“縱體入懷”這種行動只有不受禮教約束的甚至帶點狐媚之氣的假方氏,真狐仙施舜華才會有,方氏更不會有”君有佳偶,想不復念孤衾中有澪涕人“這種富挑逗意味,飽含哀怨又帶點妒忌的語言,張鴻漸第二次見到的才是一個真正的封建社會的“美而賢”的方氏。
總之欣賞《聊齋志異》讓我看到了封建社會中一群熱烈追求愛情,勇敢反抗壓迫和不讓須眉的光輝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