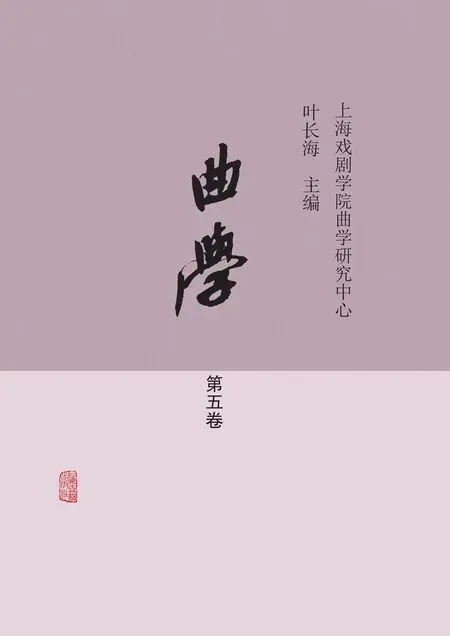論“湯沈之爭(zhēng)”
——昆曲貴族性與市民性的交織
顧聆森
400年前,湯顯祖的不朽劇作《牡丹亭》問(wèn)世,就戲劇文學(xué)而言,湯顯祖直承了由昆山梁辰魚《浣紗記》所開創(chuàng)的典雅風(fēng)格,且又自成一派: 講究文采而不拘音律,被后人命名為“臨川派”(或曰“文采派”)。據(jù)考,《牡丹亭》原著是為江西宜黃腔所創(chuàng)作的傳奇,不久流傳到昆曲的發(fā)源地吳中,經(jīng)“吳江派”沈璟等曲家改編后搬演于昆曲舞臺(tái),由于沈璟他們篡改了原著的音律和文句,便遭到了湯顯祖的猛烈抨擊。湯顯祖以“意、趣、神、色”為傳奇劇本的創(chuàng)作理念,認(rèn)為“四者到時(shí),或有麗詞俊音可用”就不必顧及九宮四聲,從而為“犯律”提供了前鑒。湯氏又認(rèn)為,文采是創(chuàng)造文學(xué)意境和“言情”的手段。真正的藝術(shù)意境就像畫家王摩詰的“冬景芭蕉”,全在筆墨之外,“吳江派”為了“便俗唱”而改寫他的文句,就仿佛“割蕉加梅”。湯顯祖因此譏道:“彼惡知曲意哉!”*(明) 呂天成《曲品》,《中國(guó)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六集,中國(guó)戲劇出版社,1959年,第213頁(yè)。但沈璟堅(jiān)持自己的“音律”和“本色”主張,“吳江派”曲家也都以“本色”與“守律”為然,認(rèn)為高雅文字并非戲曲之道,聲稱戲曲語(yǔ)言如“使聞?wù)卟唤鉃楹握Z(yǔ),何異于對(duì)驢彈琴”*(明) 徐復(fù)祚《曲論》,《中國(guó)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四集,中國(guó)戲劇出版社,1959年,第238頁(yè)。!而失律之句,不僅“屈曲聱牙”,同時(shí)也將丟失昆曲韻味。
“湯沈之爭(zhēng)”是中國(guó)劇壇發(fā)生的一場(chǎng)曠日持久的學(xué)術(shù)爭(zhēng)鳴,明清二代曲家?guī)缀醵茧y以回避抉擇。1998年我在《論中國(guó)古代戲曲的理論批評(píng)》*原載《戲曲藝術(shù)》1998年第3期,《戲劇·戲曲研究》1998年第10期轉(zhuǎn)載。一文中曾把“湯沈之爭(zhēng)”歸結(jié)到戲劇“文學(xué)性”和戲劇“舞臺(tái)性”之爭(zhēng)。昆曲問(wèn)世之前,戲劇“文學(xué)性”未能被強(qiáng)調(diào),始終安居于次要或從屬地位。昆曲興起以后,高雅的音樂(lè)敦促其劇本文學(xué)趨之于雅化,從而激活了中國(guó)戲曲“雅”與“俗”的對(duì)立,從而也凸顯了戲劇“文學(xué)性”和戲劇“舞臺(tái)性”之間固有的矛盾。然而,“湯沈之爭(zhēng)”表面上看是戲劇“文學(xué)性”和戲劇“舞臺(tái)性”孰主孰次的爭(zhēng)論,如往新的層次開掘,它其實(shí)有著更為深邃的社會(huì)內(nèi)涵。
本文有意把“湯沈之爭(zhēng)”放在明代蘇州社會(huì)經(jīng)濟(jì)中進(jìn)行考察。時(shí)至明代,蘇州的絲綢手工業(yè)已經(jīng)進(jìn)入興盛期,據(jù)《吳邑志》載,明嘉靖時(shí)期(即昆曲問(wèn)世之時(shí))蘇州已是“比屋皆織,貿(mào)轉(zhuǎn)四方”、“綾錦纻絲紗羅綢絹,皆出郡城機(jī)房”,周邊農(nóng)民紛紛進(jìn)城打工尋雇。也有打工者一旦自精其業(yè),或有了原始積累,便自購(gòu)織機(jī)生產(chǎn)。就像吳江盛澤這樣的小村落,由于“盡逐綾綢之利”就漸發(fā)展成為吳江名鎮(zhèn),嘉靖年間,已是絲綢產(chǎn)銷基地。城鎮(zhèn)的絲綢手工業(yè)又拉動(dòng)了輕工等其他手工業(yè)。總之,在昆曲興起之際,蘇州已是全國(guó)最大的金融業(yè)中心和商貿(mào)市場(chǎng)之一。隨著城市經(jīng)濟(jì)的起飛,新興的市民階層迅速壯大,成為一支重要的社會(huì)力量。湯沈所生活的萬(wàn)歷年間,蘇州絲織工人葛成曾領(lǐng)導(dǎo)了一次震驚朝野的反苛捐雜稅的市民暴動(dòng),明末清初的劇作家李玉還把這場(chǎng)群眾斗爭(zhēng)寫成傳奇《萬(wàn)民安》搬演于昆曲舞臺(tái)。表明了蘇州市民階層作為一支重要社會(huì)力量已經(jīng)成熟。
成熟的市民階層也把文化的消費(fèi)對(duì)象鎖定于昆曲。然而昆曲本質(zhì)上屬于貴族藝術(shù),魏良輔是依照了士大夫、貴族知識(shí)分子的審美意愿和審美情趣創(chuàng)立了昆曲水磨腔,昆曲第一個(gè)創(chuàng)作流派“昆山派”,其典雅的戲劇文學(xué)風(fēng)格正是為昆曲典雅的音樂(lè)特質(zhì)所決定。昆曲與市民階層一開始就似乎有著一種天然的審美距離。市民觀眾熱切希望按照他們的審美愿望把昆曲引進(jìn)市民舞臺(tái)。而沈璟的“本色”理論,其核心恰恰是要將昆曲的舞臺(tái)語(yǔ)言返歸生活。“吳江派”的骨干成員王驥德這樣解釋沈氏的“本色”理論: 他說(shuō)“世有可解之詩(shī)而不可令有不可解之曲”,曲奏之場(chǎng)上,應(yīng)該做到“不論士人閨婦以及村童野老無(wú)不通曉”。*(明) 王驥德《曲律》,《中國(guó)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四集,第154頁(yè)。他甚至提出,制曲者應(yīng)在脫稿以后去念給“老嫗”們聽聽,她們聽得明白了,才可在場(chǎng)上采用。其實(shí),沈璟的“本色”主張,客觀上已成為了市民昆曲審美的代言。
也就在明萬(wàn)歷年間,經(jīng)“吳江派”曲家的推波助瀾,造就了轟轟烈烈的戲劇“本色運(yùn)動(dòng)”,導(dǎo)致昆曲從貴族的廳堂紅氍毹向外溢出,直接推動(dòng)了民間昆曲職業(yè)戲班的繁榮。昆曲也借了職業(yè)戲班開始占領(lǐng)民間的酒肆茶樓乃至廣場(chǎng)草臺(tái)。仗著昆曲戲班的流播,昆曲觀眾結(jié)構(gòu)發(fā)生了重大變化,市民很快成為昆曲的受眾主體,成為她最大消費(fèi)者。
毋庸諱言,中國(guó)戲曲是中國(guó)農(nóng)業(yè)社會(huì)的產(chǎn)物和寵兒,昆曲問(wèn)世之前無(wú)論南戲還是雜劇,它們的消費(fèi)對(duì)象主要就是市民和農(nóng)民。戲曲雖然同時(shí)為貴族欣賞、所利用,但市民性一直是中國(guó)戲曲社會(huì)屬性的主要方面。昆曲興起之初,只流行于上層社會(huì),流行于士大夫、貴族知識(shí)分子的廳堂紅氍毹上,從而較成功地排斥了中國(guó)戲曲所固有的市民屬性,而成為貴族的寵物。然而昆曲畢竟是從傳統(tǒng)的中國(guó)戲曲中脫胎,她的市民屬性的胎痕根深而蒂固,而當(dāng)市民社會(huì)一旦成熟,昆曲本身也極愿意借勢(shì)而向更為廣闊的空間發(fā)展壯大。它之所以能很快從貴族廳堂紅氍毹中突圍,彌散于市井草臺(tái),原因恰恰在于沈璟的戲曲“本色”理論激活了她一直深潛在內(nèi)的昆曲的市民屬性。
昆曲之所以能為貴族和市民共同欣賞與愛(ài)戴,正是昆曲的社會(huì)屬性——貴族性和市民性的和諧相處和相輔相成。沈璟和以沈璟為盟主的“吳江派”陣營(yíng)的重要骨干如王驥德、呂天成、沈自晉、馮夢(mèng)龍、葉憲祖、范文若、袁于令、徐復(fù)祚、顧大典等幾乎都是那個(gè)時(shí)代的士大夫、貴族知識(shí)分子,而竭力主張昆曲本色化、平民化的又恰恰就是這一批貴族曲家,他們不僅從理論上,而且在實(shí)踐中不遺余力地張揚(yáng)著昆曲的市民性。尤其沈璟的后期劇作,讓諸多市井小人物充塞舞臺(tái),舞臺(tái)語(yǔ)言也明白如話、毫無(wú)修飾,從而深為市民觀眾所喜愛(ài)。沈璟和“吳江派”劇作家們用自己的作品證明了市民階層作為昆曲觀眾的主體,他們的觀賞思潮已經(jīng)非常有效地倒逼昆曲的審美方式從貴族群向市民傾斜。于是昆曲迎來(lái)了自己發(fā)展史上的一個(gè)重要節(jié)點(diǎn): 即從自?shī)首詷?lè)的貴族家班的廳堂唱演蛻變成以贏利為目標(biāo)的昆曲職業(yè)戲班的草臺(tái)演出。正是仗著市民觀眾的推擁,昆曲職業(yè)戲班在流動(dòng)演出中,才得以迅速把昆曲藝術(shù)遍傳大江南北。
湯顯祖同樣屬于士大夫、貴族階層的一員。他的“意、趣、神、色”的創(chuàng)作理念和使事用典、崇尚文采的實(shí)踐方法,客觀上是在全力維護(hù)戲劇文學(xué)免受“俗唱”的過(guò)分?jǐn)D壓。但湯顯祖并非昆曲藝術(shù)本體中“貴族性”的純粹代表,湯顯祖作品中所流露出來(lái)的反封建禮教的思想與代表著先進(jìn)生產(chǎn)力的市民階層的意識(shí)形態(tài)有著高度的重合面。便似《牡丹亭》這樣的作品所表達(dá)的夢(mèng)中的戀愛(ài)形態(tài)和市民對(duì)婚姻自由的渴望與追求,也并無(wú)二致。《牡丹亭》在高雅詞曲的包裝下也煥發(fā)著一種沉甸甸的市民精神。湯顯祖竭力主張,形式格律必須為內(nèi)容即文學(xué)意境服務(wù)。他那種格律形式一旦束縛或妨礙了內(nèi)容的體現(xiàn)就可以破律的思想,某種程度上也鼓勵(lì)了市民職業(yè)戲班的“便俗唱”。
作為貴族階層的劇作家精英,無(wú)論“臨川派”還是“吳江派”,在創(chuàng)作傳奇時(shí),都無(wú)法規(guī)避那個(gè)時(shí)代的市民精神的感染,也因此,昆曲“典雅派”和“本色派”才有可能在一個(gè)藝術(shù)本體中包融,之所以能在一個(gè)藝術(shù)本體中包融,又僅僅是因?yàn)橹袊?guó)戲曲的社會(huì)屬性——“貴族性”和“市民性”,與它的藝術(shù)屬性——“文學(xué)性”、“舞臺(tái)性”一樣,總是交織在一起,而且密不可分——盡管它們都具有一定的排他性。昆曲作為中國(guó)戲曲的形態(tài)之一,絕不例外。
然而,沈璟雖然成為市民昆曲審美的代言人,卻也絕非是昆曲藝術(shù)本體中“市民性”的純粹代表,這一點(diǎn),他與湯顯祖有著同工異曲之妙。當(dāng)職業(yè)戲班“便俗唱”到了一定時(shí)段,大概沒(méi)有一個(gè)傳奇文本不被戲班增刪篡改的,也包括聲腔唱演,水磨腔“依字行腔”的嚴(yán)格曲律同樣受到了所謂“隨心令”(引徐渭《南詞敘錄》)的嚴(yán)重沖擊。沈璟于是及時(shí)制定了《南九宮十三調(diào)譜》(即《南曲譜》),對(duì)填曲、唱曲的格律規(guī)則重新進(jìn)行了嚴(yán)格的規(guī)范,糾正了案頭和場(chǎng)上的“出宮犯律”,捍衛(wèi)了原真的魏良輔昆曲韻味,從而成功實(shí)現(xiàn)了在昆曲音樂(lè)、昆曲文學(xué)領(lǐng)域中的一次衛(wèi)道,又從而保證了昆曲典雅質(zhì)的傳承和發(fā)揚(yáng)。“吳江派”曲家?guī)缀鯚o(wú)不既是音律理論家,又是本色劇作家,沈璟的格律理論和本色主張?bào)w現(xiàn)了昆曲“貴族”與“市民”的雙性要求。正是昆曲的“貴族性”和“市民性”的交織,造就了那個(gè)時(shí)代的曲家群體,包括湯顯祖在內(nèi)。
昆曲藝術(shù)本體中的貴族性和市民性的交織,也同時(shí)為湯顯祖和沈璟各自主張的戲劇理論提供了契合點(diǎn)。“吳江派”曲家呂天成提出:“守詞隱先生(沈璟)之矩矱而運(yùn)以清遠(yuǎn)道人(湯顯祖)之才情。”*(明) 呂天成《曲品》,《中國(guó)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六集,第213頁(yè)。自此劇壇有了“雙美”一說(shuō),即要求于傳奇創(chuàng)作既堅(jiān)守格律原則,又發(fā)揚(yáng)文采才情,從而從兩個(gè)方面確保昆曲的典雅本真。呂天成有意借湯、沈兩家的理論精髓,以期能徹底護(hù)衛(wèi)住昆曲的貴族性;“吳江派”的另一位曲家王驥德則倡導(dǎo):“詞與法兩擅其極。”*(明) 王驥德《曲律》,《中國(guó)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四集,第172頁(yè)。王驥德之所謂“法”,當(dāng)是指沈璟所修訂的昆曲格律;所謂“詞”,指的是舞臺(tái)語(yǔ)言和文字。王驥德歷來(lái)主張昆曲舞臺(tái)語(yǔ)言以本色當(dāng)先,甚至要讓“老嫗”們聽得懂。然王驥德并沒(méi)有交代此“老嫗”是城里人還是鄉(xiāng)下人,是文盲還是文化人,其要義自然只是讓人明白聽懂而已。王驥德對(duì)“詞”的真見解,是“本色不廢文采”。“典雅派”創(chuàng)作傳奇好使事用典,王驥德指出:“曲之佳處,不在用事,亦不在不用事。好用事失之堆積,無(wú)事可用失之枯寂。”*同上,第127頁(yè)。又說(shuō):“大抵純用本色,易覺(jué)寂寥,純用文調(diào),復(fù)傷雕鏤。”*同上,第122頁(yè)。顯然王驥德的“本色論”對(duì)沈璟的一味遷就于通俗有了某種修正,也為曲壇所普遍認(rèn)可與接受,致使“詞與法兩擅其極”成為了劇壇新的“雙美”標(biāo)準(zhǔn)。王驥德的“本色不廢文采”論,意為“典雅”與“本色”的爭(zhēng)論提供一條中和之道。然而,如前所述,昆曲雖然包融了“貴族性”和“市民性”,但它們相互之間卻存在有較大的排他性。在創(chuàng)作具體的方式上,湯顯祖的不肯就俗和沈璟的難以媚雅,決定了這一時(shí)代的傳奇創(chuàng)作不可能生產(chǎn)出真正“雙美”的作品來(lái)。
時(shí)至明末清初,傳奇創(chuàng)作才仗著傳奇的“雙美”理念進(jìn)入了一個(gè)嶄新的境界,致使昆曲進(jìn)入了一個(gè)“家家收拾起,戶戶不提防”的極盛時(shí)期。昆曲的鼎盛有賴于曲壇涌現(xiàn)了一個(gè)實(shí)踐“雙美”的新的創(chuàng)作流派,這就是昆曲“蘇州派”。
“蘇州派”是這樣一個(gè)劇作家群落,與“吳江派”不同,他們是清一色的市民曲家。我曾在專著《李玉與昆曲蘇州派》(廣陵書社2011年出版)中詳細(xì)分析評(píng)論了他們70余個(gè)傳世的全本傳奇,他們作品最大的趨同特征,一是塑造市民的脊梁,二是頌揚(yáng)貴族精神。令人驚奇的是,市民脊梁的塑造竟筑基于貴族精神。他們作品中栩栩如生的市民脊梁的代表人物的那種見義勇為、除暴安良乃至家國(guó)精神,足可以和真正具有“貴族精神”的士大夫的那種忠貞廉潔、剛正不阿品質(zhì)相比美。也許“蘇州派”劇作家們經(jīng)歷了改朝換代的社會(huì)大動(dòng)亂,從而痛定思痛,一方面竭力鞭撻貴族社會(huì)的售奸賣國(guó)、貪贓枉法,同時(shí)也無(wú)情揭露市民社會(huì)爾虞吾詐、見利忘義等種種丑行。但他們把主要筆墨更放在熱烈宣揚(yáng)忠孝節(jié)義、誠(chéng)信廉恥等貴族精神的核心——儒家道德。通過(guò)一種泛貴族精神的表達(dá),以求對(duì)明亡沉痛教訓(xùn)的總結(jié)反思和對(duì)社會(huì)安定的強(qiáng)烈訴求。對(duì)于“蘇州派”曲家而言,必欲使源出于儒家思想的貴族精神為貴族、市民乃至整個(gè)社會(huì)所追求、遵循、敬仰。因而昆曲所包融的貴族和市民的雙性屬性更貼近他們的創(chuàng)作理念與訴求。故他們的作品絕少卿卿我我、才子佳人那種純貴族式的生活內(nèi)容,寧可把人物引導(dǎo)到抗擊異族侵略的戰(zhàn)場(chǎng),借此也開創(chuàng)為貴族和市民觀眾所共同喜聞樂(lè)見的武戲系統(tǒng)。
須知昆曲“蘇州派”是在“湯沈之爭(zhēng)”的余波中興起。這時(shí)的劇壇“湯沈之爭(zhēng)”已給傳奇創(chuàng)作理論的提升提供了捷徑,而創(chuàng)作理論的提升又同時(shí)為創(chuàng)作實(shí)踐準(zhǔn)備了條件。可以這樣說(shuō),“湯沈之爭(zhēng)”的最大受益者恰恰就是明末清初以李玉為首的昆曲“蘇州派”。和“蘇州派”的創(chuàng)作思想和創(chuàng)作理念相適應(yīng),他們的作品重音律又不拘泥于音律,重本色而又不廢文采,可讀又可演。他們所注重的形式可以最大限度地體現(xiàn)他們所秉持的創(chuàng)作理念。故他們的作品能深受士大夫貴族階層和市民階層的共同的青睞。如江左名士吳偉業(yè)稱道“蘇州派”領(lǐng)袖李玉的傳奇“有美斯彰,無(wú)微不著”*(明) 吳偉業(yè)《北詞廣正譜序》,北京大學(xué)影印本,1922年版。,錢謙益也贊譽(yù)李玉“如達(dá)夫、昌齡聲高當(dāng)代”*(明) 馮夢(mèng)龍《墨憨齋重訂永團(tuán)圓傳奇敘》。。時(shí)至清初,“蘇州派”的作品已經(jīng)達(dá)到了“詞與法兩擅其極”的境界,即格律與文采的兩相統(tǒng)一,雅與俗相望相守,貴族廳堂和市井草臺(tái)都不峻拒,從而開創(chuàng)了吳門昆曲“雅俗共賞”的新局面,達(dá)到了所謂“家家收拾起,戶戶不提防”,這里的“家家”、“戶戶”,同時(shí)包括了貴族和市民乃至販夫走卒等所有的社會(huì)階層,昆曲從此進(jìn)入了一個(gè)“全民文藝”的新紀(j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