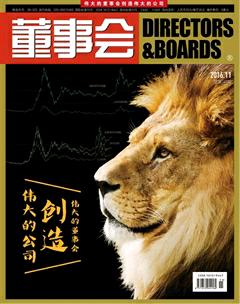“強人”無法永遠控制企業
徐強
無論是過去的四川長虹倪潤峰、娃哈哈的宗慶后、海爾的張瑞敏,還是現在的阿里巴巴的馬云、蘇寧的張近東、京東的劉強東,甚至是華為的任正非,都沒有看到有什么分權的內部治理機制或者效果出現,所以,我們必然擔心這些企業的后勁。
職業經理人制度是上世紀20年代開始在美國企業推行的傳承制度,從此企業選擇管理者有了范圍,這對企業的持續發展影響深遠。分權管理是上世紀50年代通用電氣實行的內部管理的做法,企業的決策權出現分散,不再因為某個人的離開而發生改變,這在當時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企業戰略管理是上世紀60年代之后出現的新的企業革命,包括CEO、CFO在內一批新的決策職位的出現,使得企業的內部治理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企業不再由一兩個人決定命運,戰略管理刺激了企業的規模化生產和轉型。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互聯網革命引領企業新的轉型,企業的規模經濟現象被打破,合伙人制度“死灰復燃”成為具有新的生命力的制度形式……
從以上這些過去百年來西方企業管理發展在傳承方面的重要節點可以看出,我國企業和西方發達國家企業在傳承理論和實踐方面的差距非常大。當前我國民營企業所面對的傳承問題不僅僅是一個企業的問題,而是企業發展過程中必定面臨的普遍問題,從消除權力集中(集權)角度看,問題的解決需要根據經濟社會環境的變化而有所改變。
首先,建立有效的職業經理制度,為企業傳承提供人才基礎。企業有效傳承的第一前提是有企業管理的“能人”,過去這種能人主要從家族或者企業內部產生,這是因為第一代家族創業者不愿意將權力旁落,自然就產生太多的局限和不確定性。其實民營企業的創業者們應該明白,對權力的控制,并不能帶來企業的持續經營,如果不能用市場的方法提供給企業能夠傳承的能人,創業者們想放權也不能促進企業的發展,所以,建立有效的職業經理制度迫在眉睫!應該說,美的集團的“職業經理人制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職業經理制度,因為職業經理制度不僅僅是企業的事情,還包括職業經理的教育制度、職業經理的培訓制度、職業經理的選拔機制等在內的整個社會經濟系統的事情。譬如國外的MBA是專門培養職業經理的教育搖籃,但中國引入到現在都僅僅是一個學歷教育,這或許不僅是教育的問題,還包括企業的選拔機制的問題。與企業內部的職業經理人崗位制度相匹配的,一定是放權。民營企業的決策者們應該明白,只有永遠的資本增值,沒有永遠的企業控制!
其二,改變企業股權權利結構,為企業傳承提供權利保障。要改變企業的權力機制,首先需要改變股權權利結構。你不能指望你絕對控股企業,然后讓中小股東、債券人和職業經理為你賣命,不愿意放股權的企業就不能做大,小農經濟永遠不能成就大氣候。美國企業規模經濟下有利于企業傳承的職位和制度(譬如董事會的獨立董事、職工董事、CEO和CFO、職業經理制度等),都是隨著美國家族企業的股權分散,企業股權決策權力下降,同時企業的內部決策制衡機制建立起來而出現的。進入新的世紀,實際上,美國企業現在再一次地面臨股權權力變化的變革:股權社會化向股權集中化的變化,無論成功與否,這是美國經濟變革的需要。我國的民營企業發展歷史較短,現在正處于第一代企業家(資本家)因為生理原因,需要逐步交權的時候,如果能夠借此將股權權力進行必要的變革,或許是這些企業未來繼續充滿生命力的關鍵要素之一。
第三,變革企業內部治理結構,為企業傳承提供制度安排。中國的民營企業在科學管理決策方面的欠缺是有目共睹的,這是緣于企業的內部治理結構不合理。大多數企業,無論什么背景,決策的集權現象非常明顯,集權決策就基于一個“強人”的存在,但人的壽命是有限的,如果沒有好的傳承,企業基本就是“富不過三代”。在企業集權的分權這點上,無論是過去的四川長虹倪潤峰、娃哈哈的宗慶后(2016年已71歲)、海爾的張瑞敏,還是現在的阿里巴巴的馬云、蘇寧的張近東、京東的劉強東,甚至是華為的任正非,都沒有看到有什么分權的內部治理機制或者效果出現,所以,我們必然擔心這些企業的后勁。企業的內部治理結構應該是怎么樣的,沒有統的模式,衡量的標準應該是企業決策有利于資本的增值,而非企業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