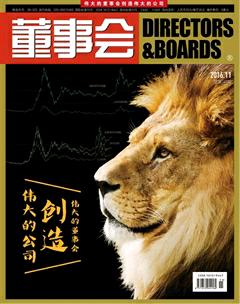國企改革深層次問題出在哪兒
安林 陳慶
我們從當(dāng)前出臺的眾多文件中,并沒有看到諸如“國資委組織體制改革試點”、“國資委監(jiān)管體制改革試點”等文件的出臺。“下面繩子都在解開,上面‘結(jié)還不動!”這恐怕是國企改革不見效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國有企業(yè)領(lǐng)導(dǎo)人的訪談中,最常聽到的一句話是“誰管我的烏紗帽,我就聽誰的!”這或許最能說明,此種政企關(guān)系“簡單化”對國資國企改革所產(chǎn)生的不利影響及嚴(yán)重程度——國企改革是企業(yè)內(nèi)部管理體制與管理企業(yè)的體制結(jié)合起來的改革,國企改革與國資體制變革是“一幣的兩面”,診斷當(dāng)前深化國企改革的深層次問題需要同時從兩方面來進(jìn)行。
“七化”問題避之不開
至2016年,我國國資體制運行在取得階段性輝煌成就的同時,也存在一些“繞之不過,避之不開”的問題,表現(xiàn)在國資運營系統(tǒng)中、國資系統(tǒng)改革行為中。國資運行系統(tǒng)中的問題可歸為“七化”。
干部管理“直接化”。深化國資國企改革,黨管干部是一條原則。問題是,管到哪一層以及怎么管。幾乎各地各級黨組織機(jī)構(gòu)者附巴“原則性的管”變成了“直接的任命或推薦”。
政企關(guān)系“簡單化”。由于干部管理的“直接化”,致使政企分開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應(yīng)有的意義,國企領(lǐng)導(dǎo)人“誰管我的烏紗帽,我就聽誰的!”或許最能說明這種簡單化的不利影響及嚴(yán)重程度。
股東職權(quán)“濫用化”。國資出資人監(jiān)管的邊界模糊,也未能建立清晰的監(jiān)管權(quán)力清單和責(zé)任清單,實現(xiàn)以管企業(yè)為主向以管資本為主的轉(zhuǎn)變。管事方面,董事會、經(jīng)理層的事,國資委還在管,而且主要靠發(fā)紅頭文件來管!就近幾年運行狀況看,國資委的監(jiān)管行為某種程度上仍處于管企業(yè)狀態(tài)。
議決機(jī)制“風(fēng)險化”。國資委依舊沿襲政府行政會議制度——主任辦公會形式的議決制,來作股東決議,這樣的決策機(jī)制風(fēng)險極大。從國資委工作制度上看,主任辦公會的表決機(jī)制和問責(zé)制度有待改進(jìn)。如對于股東決議事項,有些需開主任辦公會,有些只要分管主任審批即可,有些情形要三分之二會議成員通過,有些二分之—通過即可等,缺乏制度性安排。
授權(quán)體制“模糊化”。國資委集國資監(jiān)管權(quán)力與出資人權(quán)利于一身,由此國資委發(fā)出的行為,常常弄不清是行政上的監(jiān)管還是治理上的行權(quán),是權(quán)力還是權(quán)利。
董事會履職“程序化”。除中央企業(yè)董事會試點工作顯示明顯成效外,許多地方國企法人治理結(jié)構(gòu)基本還停留于“法律型”框架階段。黨政聯(lián)席會議、班子會議,實際上仍然是各地國企的決策權(quán)力機(jī)構(gòu)。
終極維權(quán)“虛置化”。“國家統(tǒng)一所有,中央與地方政府分級代表”的國有資產(chǎn)管理體制,與原有的“分級管理”體制相比,無疑更進(jìn)了一步,但在實際運行過程中,“分級代表”得到了更多的強(qiáng)調(diào),而“國家統(tǒng)一所有”這個根本前提卻被人們“虛置”,國務(wù)院國資委注重的是中央企業(yè)的利益,地方政府國資委注重的是地方企業(yè)的利益,那么誰在注重“國家”的利益呢?
“試點”依賴幾時休?
國資系統(tǒng)行為中,則顯現(xiàn)出“六大癥狀”。
有“試”無終癥。2005年首批推出7戶中央企業(yè)進(jìn)入董事會試點,到現(xiàn)在總共106戶中央企業(yè)試到了85戶,雖然2010年后改名“規(guī)范董事會建設(shè)”,但始終沒有改變“董事會試點”之實。地方國資委的情形同樣如此。
“試點”依賴癥。十八屆三中全會前一直有董事會試點;十八屆三中全會后,還有包括董事會建設(shè)的“四項改革試點”,2016年又推出仍包括董事會建設(shè)的“國企十項改革試點”。如此林林總總的“試點”,很難不讓人形成“把試點當(dāng)改革”或過度依賴“試點”的印象。國資系統(tǒng)這種通過試行辦法等更多依賴行政手段規(guī)范企業(yè)生產(chǎn)經(jīng)營活動的行為,也亟待有效清理和規(guī)范。
濫用“試點”癥。目前所開展的無論是“四項改革試點”,或“國企十項改革試點”中的許多工作,明明為《公司法》《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和《中共中央、國務(wù)院關(guān)于深化國有企業(yè)改革的指導(dǎo)意見》所規(guī)定,只需貫徹執(zhí)行就行了,而沒有必要試點來試點去。
有“點”不“試”癥。董事會選聘經(jīng)理應(yīng)成為董事會試點的必選項,但啟動多年未把這個“點”拿出來“試”。《公司法》明確規(guī)定的“國有資產(chǎn)監(jiān)督管理機(jī)構(gòu)可以授權(quán)董事會行使股東會的部分職權(quán)”,國資系統(tǒng)也不曾積極主動加以試點。
只改不動癥。就現(xiàn)時期而言,更主要的是國資體制的改革,其中國資委自身組織與職能的改革應(yīng)首當(dāng)其>中。當(dāng)下,伴隨著大量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的設(shè)立,和國家“開展政府直接授權(quán)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履行出資人職責(zé)的試點”,國資委的地位和作用、職能和定位、行權(quán)和履職,都必將面臨轉(zhuǎn)型和巨變。但我們從當(dāng)前出臺的眾多文件中,并沒有看到諸如“國資委組織體制改革試點”、“國資委監(jiān)管體制改革試點”等文件的出臺。“下面繩子者陸解開,上面‘結(jié)還不動!”這恐怕是國企改革不見效的重要原因之一!
“指導(dǎo)”過多癥。國資委對國資國企的改革指導(dǎo),過于倚重紅頭文件。自身改革動力緣何不強(qiáng)
深化國企改革,根本上離不開國企自身的改革動力。當(dāng)前,普遍上看,各國企意欲改革的動力不強(qiáng)。原因有六個方面。
董事會核心職權(quán)缺失。“董事會擁有經(jīng)理的聘任、考核和分配決定權(quán)”是任何一個現(xiàn)代企業(yè)董事會的核心職權(quán)。缺乏這一職權(quán),董事會的權(quán)威和權(quán)力將受到嚴(yán)重削弱,董事會的地位和作用將難以正常體現(xiàn)。縱觀國企改革這么多年,仍然沒有一家企業(yè)董事會擁有這項權(quán)力。即便新興際華作為唯一一家中央企業(yè)試行了董事會選聘經(jīng)理的實踐,但離《公司法》賦予的董事會職權(quán),還有一定距離。
經(jīng)營自主決定權(quán)不足。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一直致力于擴(kuò)大企業(yè)經(jīng)營自主權(quán)的探索。《公司法》做出了“國有資產(chǎn)監(jiān)督管理機(jī)構(gòu)可以授權(quán)公司董事會行使股東會的部分職權(quán),決定公司的重大事項”的特殊規(guī)定。但長期以來,國有企業(yè)董事會應(yīng)有的職權(quán)都被剝奪或被限制,更談不上還能獲得額外的股東會授權(quán)。
高管薪酬激勵功能乏力。國企要持續(xù)實現(xiàn)國資資本保值增值,同樣需要在社會或市場上創(chuàng)造價值。而要實現(xiàn)這一目標(biāo),尤其需要企業(yè)發(fā)揮高管的聰明才智和主觀能動性,需要給予應(yīng)有的合理的薪酬激勵。但近年來,各地政府基于社會“公平”等因素考量而頒布的國企高管限薪令,雖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積極效果,但不能不說也給國企界的高管們帶來了工作積極性和能動性的嚴(yán)重打擊。
員工持股激勵好看難用。引入員工持股和股權(quán)激勵,讓員工與企業(yè)同擔(dān)共享,能進(jìn)一步有效建立激勵約束長效機(jī)制,激發(fā)國企的內(nèi)在動力。但基于操作中的復(fù)雜性和防范國資流失的顧慮,各級各地國企基本上都沒有開展此項工作。2016年8月《關(guān)于國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業(yè)開展員工持股試點的意見》的出臺,可謂國企改革中的爆炸性新聞。但,在“試點企業(yè)營收要求、試點企業(yè)層級要求、入股員工崗位要求、員工現(xiàn)金出資要求、員工持股總量占比”等方面改革的謹(jǐn)小慎微,使得這項改革有可能“好看不中用”。
內(nèi)部改革提升空間受限。國企改革的本質(zhì)是激發(fā)企業(yè)內(nèi)在動力和活力。過去,國有企業(yè)改革一直徘徊于“集權(quán)”與“放權(quán)”之間。如何“集而不死”“放而不亂”,企業(yè)的內(nèi)部改革與管理提升極其重要。事實上,2003年國資委成立以來,一直在抓企業(yè)內(nèi)部改革與管理提升,但無論是董事會建設(shè)試點、還是全面管理提升或企業(yè)提質(zhì)增效活動,最終都碰到了“天花板”,觸到了管理企業(yè)的國資體制的改革問題,進(jìn)而企業(yè)內(nèi)部改革遇到了“不可控”的阻力和限制。
董事會決策權(quán)踐行不易。董事會是現(xiàn)代企業(yè)制度下的決策機(jī)構(gòu)。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結(jié)構(gòu),完善董事會建設(shè),就是要通過做實董事會,來確保董事會發(fā)揮決策機(jī)構(gòu)作用。但現(xiàn)今多重政策文件和法律法規(guī)的疊加,使得企業(yè)董事會決策權(quán)踐行起來極為不易,甚至無所適從。最好的例子是,基于黨組織在企業(yè)中發(fā)揮政治核心作用背景下的董事會如何行使決策權(quán)問題。2004年《中央組織部、國務(wù)院國資委黨委關(guān)于加強(qiáng)和改進(jìn)中央企業(yè)黨建工作的意見》強(qiáng)調(diào),企業(yè)黨組織參與決策,是對需要參與決策的重大問題提出意見和建議,而不是代替董事會和經(jīng)理層決策重大問題。2010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wù)院辦公廳印發(fā)的《關(guān)于進(jìn)一步推進(jìn)國有企業(yè)貫徹落實“三重一大”決策制度的意見》指出,董事會、未設(shè)董事會的經(jīng)理班子研究“三重一大”事項時,應(yīng)事先與黨委(黨組)溝通,聽取黨委(黨組)的意見。不久前,國務(wù)院國資委黨委發(fā)表“在全面深化國有企業(yè)改革中加強(qiáng)黨的建設(shè)工作”一文則進(jìn)一步提出,“全面深化國有企業(yè)改革,國企重大決策須由黨委討論后董事會決定。”據(jù)筆者調(diào)研情況,后者正在制造企業(yè)黨委與董事會決策權(quán)新的混亂,也自覺不自覺地挫傷了董事會的工作能動性,致使企業(yè)內(nèi)部改革意愿、作為意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