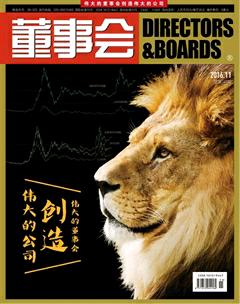做大做強做優的排序
馮立果

青年經濟學者。中國企業聯合會副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博士后,目前重點研究大企業和體制改革
如果真正有自信的話,“做大”這種結果就可以不要,德國人以中小企業、微型冠軍著稱于世,同樣受人尊敬。中國的國有企業如果能在“做強”“做優”上取得進步,能夠在市場競爭中取得較強的市場地位,那么“做大”就是一種水到渠成的結果,不求自來了。
這好像不是個問題,因為在整個國有企業改革的大工程里,“做大做強做優”的排序表述實在是個小問題。可是您還別看它小,它還是學者們討論比較多、爭論比較大的焦點問題。
現在政府部門、國有企業等使用的普遍是“做強做優做大”的排序。這來自于習近平總書記在今年7月4日對全國國有企業改革座談會的批示內容:必須理直氣壯做強做優做大。我們學習習總書記講話精神,當然主要是學習其講話精神,不只是背誦一下語言句子。事實上,這三個“做”的排序并不是一成不變的,是經過幾次變化而來。
三個“做”最早的排序方法是“做大做強做優”。如果百度搜索的話,能夠發現在2000年之前,“做大做強做優”這個詞組還沒有出現。這恐怕和當時我國的總體經濟發展水平不高有關。進入本世紀后,使用“做大做強做優”的情況逐漸增多,但通常用在城市建設上,比如石家莊、長沙市2003年都提出要把城市做大做強做優;也有地方提出要把支柱產業、某一項產業或者把民營企業做大做強做優的口號。在2005年之前,除了個別企業提出要實現三個“做”,學術界、官方很少把國有企業和三個“做”聯系在一起。
2005年10月28日,《中共廣東省委、廣東省人民政府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決定》發布,時任廣東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鐘陽勝接受《南方日報》記者的獨家專訪時表示:“我省國有企業改革必須做出更大膽的戰略決策并付諸實施,才能使之進—步做大做強做優”。這應該是官方比較早的將國有企業做大做強做優連在一起表述的情況。
2007年之后,三個“做”的排序出現了變化,變成了“儲雖做優做大”,而且,越來越多的政府官員將之作為國有企業改革的目標。在2007年中國大企業高峰會上,國資委副主任李偉重點探討了“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問題,針對一些大型國有企業經營困難的現象,他提出“大而不強,好景不長;大而不優,必有遠憂”的觀點,振聾發聵。這之后,“做強做優做大”被政府作為國有企業改革目標的主要表述方式。十八大后,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國有企業改革工作,更是提出“必須理直氣壯做強做優做大”“搞好國有企業、發展壯大國有經濟”的指示。
從“做大做強做優”到“做強做優做大”,三個“做”的排序發生了微妙變化,“做大”從最前面放在了最后面。“做大”不好嗎?我們在很長的時間內追求能有幾家中國企業進入世界500強。隨著2003年前后中國工業化進程進入重化工業化階段,國民經濟進入新一輪高速增長階段,國有企業迎來歷史上最好的發展機遇,無論資產規模還是營業收入規模都實現了歷史上最快的增長,同時在國資部門主導下國有企業進行了大規模合并重組,一時間進入世界500強的國有企業達到數十家之多。然而社會公眾對于國有企業取得的成績并不完全認可,國有企業被廣為詬病的主要問題是:占據壟斷地位“與民爭利”:高度依賴政府政策和行政資源,患有“巨嬰綜合征”;國際化水平低,主要賺自己人的錢;即使這樣不少企業仍然嚴重虧損甚至資不抵債。綜合起來,就是“大而不強”。在這種情況下,“做強做優做大”的排列順序被確立了下來。
實際上,對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來說,規模大小只是一種市場競爭的結果,只有市場競爭能力強才可能擁有較高的市場地位,才有可能“做大”,才能形成高度集中的產業組織結構。我們在制定企業政策時機械地以為將幾家企業捏合在一起就能形成大企業,市場集中度就提高了,競爭力就具有了。這已經被事實證明失敗了。嚴格意義上,如果真正有自信的話,“做大”這種結果就可以不要,德國人以中小企業、微型冠軍著稱于世,同樣受人尊敬。中國的國有企業如果能在“做強”“做優”上取得進步,能夠在市場競爭中取得較強的市場地位,那么“做大”就是一種水到渠成的結果,不求自來了。當然,“做強”“做優”二者并不是不可顛倒。如果把“做優”“做強”“做大”作為一種遞進關系,通過做優來做強,通過做強來做大,這樣的邏輯關系是不是更順一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