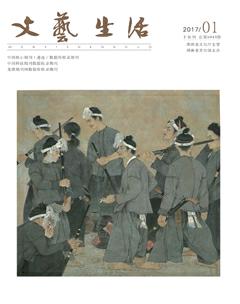悲與美:《穆斯林的葬禮》的文化自信力
王嘉熙
摘 要:《穆斯林的葬禮》講述了“玉器梁”家三代人的悲劇命運,但所有人面對不幸的命運都沒有一味地表現出失望和頹廢,而是鼓起勇氣接受事實并且更加積極、更加坦然地面對命運的安排,堅持以堅韌頑強的意志突圍,在不幸中追求生命的真諦與美好,彰顯著一個民族的文化自信。
關鍵詞:悲劇;美好;文化自信
《穆斯林的葬禮》描寫了民國初期,一個穆斯林家族的興衰沉浮,講述了三代人的悲劇命運,其中有家破人亡、顛沛流離的社會悲劇,也有交錯扭結的愛情悲劇。可是,悲劇并未將人打倒,絕望之中往往會孕育新的希望,這些悲劇更是展現了一個民族自信漸強的不屈歷史,書寫了一首中華民族在不幸中奮然前行的莊嚴詩篇。
一、《穆斯林的葬禮》之“悲”
作品開篇就講述了古都京華老字號玉器行“奇珍齋”的梁亦清,是一位技藝高超的回族琢玉藝人,正當梁亦清和徒弟韓子奇二人為一件訂貨而勞作時,梁亦清卻突然暈倒在轉動著的玉坨上,吐血身亡。即將在中秋佳節完成的一件寶船也被毀壞,這件寶船是匯遠齋為洋人定做的“鄭和航海船”。梁家為了抵債,只能將奇珍齋轉手給落井下石的匯遠齋老板。韓子奇為了報仇,潛伏到匯遠齋做學徒,三年之后,學成歸來的韓子奇為了報恩,娶了梁亦清的長女梁君璧,開始重振家業,此時又喜得一子。似乎命運已經從此改變,卻正巧遇上農村里被日本侵略者帶走,中途逃走的中年婦女,韓家便認這婦女為大姐,讓孩子叫她姑媽。果然,后來日軍侵華戰爭爆發,韓子奇因為擔心玉器珍品被毀,就留下家人,帶著玉器珍品隨英國商人亨特來到倫敦,一家人只能忍受顛沛流離之苦。戰后韓子奇帶著妹妹梁冰玉一同回國,梁君璧卻容不下梁冰玉母女倆,于是冰玉決定帶女兒遠走他鄉,雖然在韓子奇的苦求下留下了女兒,一家人卻只能再次分離。而女兒新月長大成人,上學后與楚雁潮發生愛情,因回族不與漢族通婚,他們的愛情為梁家反對,卻在萬般阻撓中愈加熾熱。而長子韓天星也因母親的操縱,沒能和自己喜歡的同事結婚,當發現時,一切都來不及了。
漸漸地,新月和楚燕潮的愛情在重重阻力下不斷向前發展,而命運卻再一次沒有眷顧他們,新月紅顏薄命,因嚴重的心臟病不幸逝世,楚雁潮及新月一家悲痛欲絕,多年以后,韓冰玉回到闊別已久的博雅宅,但一切已經物是人非。
二、“悲”中彰顯的文化自信
《穆斯林的葬禮》寫的是“玉器梁”一家的悲劇命運。一是社會悲劇:奇珍齋的主人空有一腔傳播、宏揚中國玉器文化事業的壯志豪情,卻因社會環境的摧殘而不斷遭受挫敗;二是愛情悲劇:如韓子奇和梁冰玉的愛情悲劇;三是命運悲劇:梁亦清、韓子奇、梁冰玉、韓新月以及作為悲劇制造者的虔誠穆斯林,梁君璧和不是回族卻愛上回族女孩的楚雁潮——他們的命運在宗教文化與現實生活的突出矛盾之中顯得尤為悲慘。但是,這些悲劇并沒有將 “玉器梁”一家打敗,他們堅持以堅韌頑強的意志突圍,彰顯著中華民族在不幸中堅持奮勇向前的民族文化。
(一)動蕩不安的社會摧不毀玉石匠振興民族文化的志向
民國時期外國資本家大肆的競爭與剝削、帝國主義侵略戰爭和后來“文化大革命”的摧殘都摧不毀奇珍齋兩位玉石匠捍衛民族文化、振興玉器事業的宏偉志向。一輩子安分守己地在玉石坊打磨溫潤奇珍美玉的梁亦清,卻愿以死為回回民族爭口氣,他的生命在最后一刻發出了璀璨的光亮。愛玉如命的韓子奇在侵華戰爭爆發后,毅然決定跟隨英商友人去英國避難,為的是不讓玉器在戰爭中被摧毀。他也曾經為了女兒新月上大學和兒子天星而賣出藏品,而當他后來鑒定出自己忍痛賣掉的玉,因為受不了刺激而跌下臺階。韓子奇不是拿玉器當財寶,在他的心里玉器藏品的意義甚至超過家人和自己的生命,他是為了讓這種承載了中華民族文化的載體能夠通過自己的手傳承下去。
(二)民族宗教的禁錮擋不住有情人向往美好愛情的憧憬
從梁冰玉和韓子奇,到韓新月和楚燕潮,他們的愛情都突顯了回族人民在文化融合中敢于打破民族宗教禁錮,勇于追求真情的堅定信念。梁冰玉經歷了刻骨銘心的愛恨糾葛,終于領悟到“人可以失落一切,唯獨不應該失落的是自己”,在苦苦尋求愛的歸宿中終于找到自我,最后更是毅然出走,并且沖破倫理桎梏,與姐夫生出愛的情愫。韓新月和楚燕潮不顧家人反對,以最純潔、最真摯的愛情給冰冷的世界增添了一絲溫暖。這種對愛情的向往、對民族宗教信仰的挑戰證明了源遠流長的中華民族文化具有包容性和多樣性,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文化都能夠在中華大地上生根發芽,并且能夠與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相互交融,即使這種交融需要一個較為漫長的過程。
(三)生離死別的命運抹不滅人世間追求生命真諦的足跡
書中太多的生離死別顯得命運是那么的悲慘和不幸,但是所有人面對不幸的命運卻沒有一味地表現出失望和頹廢,而是鼓起勇氣接受事實并且更加積極、更加坦然地面對命運的安排,永不停息追求生命真諦的步伐。
哥哥韓天星在得知母親故意操縱自己的婚姻之后,并沒有一氣之下丟下這個家而不管不顧,而是選擇不再讓現在的妻子受到傷害。韓新月面對死亡,在愛和溫情中堅定了生的信念,雖然最后帶著純真美好和希望離去,但她既沒有爺爺的遺憾也沒有爸爸的恐懼。也許正如作者在本書后記中所言:“我覺得人生在世應該做那樣的人,即使一生中全是悲劇,也是幸運的,因為她畢竟經歷了并非人人都經歷的高潔、純凈的意境。人應該是這樣大寫的‘人。”在悲劇中看到美好,在不幸中追求生命的真諦,這正是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