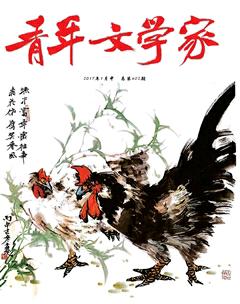李白詩中“水”意象功能淺析
陳振偉
摘 要: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山水對于文人的精神世界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特別是那種變化萬千、姿態迥異的水更是滋養了藝術的精華。本文淺析了李白詩中“水”意象的功能,詩因水的存在而增靈魂,水因詩的參與而生靈氣。
關鍵詞:李白詩歌;水;意象
[中圖分類號]:H31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7)-02--01
詩仙李白以其雄渾瑰麗的詩歌展現出了璀璨的浪漫主義光輝,在他的詩歌中同樣包含了富有浪漫主義色彩的水的意象,有石上清流,有汪洋江河,呈現出潺潺之態,也表現出波瀾壯闊的雄奇,可以說是風情萬種,儀態萬方。其實在李白的詩歌當中,用功能的角度去劃分,可以歸結為以下幾種。
一、以大水壯氣勢,以清水寫意境
李白詩歌氣勢豪放、樂觀灑脫,但是甚少對具體客觀物象的描繪,這與他的浪漫主義色彩一脈相承,但是詩人往往通過對水的表述來傳達那種豪情和氣勢,可以說水在李白詩歌當中對氣勢和意境的營造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李白在《公無渡河》中這樣寫:“黃河西來決昆侖,咆哮萬里觸龍門。波滔天,堯咨嗟。”黃河以昆侖都不可阻擋之勢,咆哮萬里直沖龍門,其滔天萬里氣勢撲面而來。再如他在《望廬山瀑布》寫到“日照香爐生紫煙,遙看瀑布掛前川。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想象奇特、夸張貼切。在這些詩句中詩人就這樣通過神來之筆,把浩浩大水的氣勢給勾勒出來了,從而形成了個人詩歌的豪邁風格。
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別有風味。李白詩歌中的水不單純是壯闊的大水,還有寧靜的富有靜美的水,在詩歌中也營造了別樣的優美意境。在他的詩歌中這類水一般是清澈的、或碧綠的,他用這樣的水來展現那種樸素、寧靜、天真、自然、雅致的情趣,形成一個個美麗的畫卷。借用他自己的詩句說,那就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例如“青山橫北郭,白水繞東城。”(《送友人》)巍巍青山,明凈的河流描繪出的清幽寧靜的境界;還有作者在《清溪行》中“清溪清我心,水色異諸水。借問新安江,見底何如此?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里。”莫不如是。
二、借流水以寄情,用流水來托理
在李白的詩歌中,水是有生命的,有感情的,自己的情感和水的流動意趣形成了共鳴,因此水的流動的姿態依然成為了情感表達和傾訴的最佳載體。所以李白往往通過用那綿長的流水來表達自己的思念之情,用那千轉百回的流水來表達依依不舍的情感。“金陵勞勞送客堂,蔓草離離生道傍。古情不盡東流水,此地悲風愁白楊。”(《勞勞亭歌》)離別最是傷心事,歷來文人最關情,作者借助勞勞亭這個送別的標志名詞,用東流之水來傳達永恒的情感。就如詩人說是:送別是萬古不變的悲情,就像江水流不盡。“流水無情去,征帆逐吹開。相看不忍別,更進手中杯。”(《送殷淑》)更是借流水來傾訴離別的痛楚。“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送孟浩然之廣陵》)詩人借流向天邊的滔滔江水來傳達對惜別的無限難舍深情。再如“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贈汪倫》)通過潭水之深類比情感之深。還有他的《江夏行》、《金陵酒肆留別》、《金陵酒肆留別》等詩歌都是通過流水或是表述對友人的不舍之情,或是表達對友人的思念之情,可謂山高水長,情感悠揚,在這里水也富有了人的情思,水就成了最佳的情感載體。
情理情理,情和理往往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情人看水有情,哲人看水有理,在李白的筆下亦是如此。因了水的流動變化來比喻人事的變動,用水的特性來比喻一些特定的理念,這在李白詩歌中亦很常見。如李白在《將進酒》中:“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通過流水的流逝比喻時光的流逝,這種時間的概念和感覺就是情理的闡發與結合。在《古風》中“榮華東流水,萬事皆波瀾。白日掩徂輝,浮云無定端。”通過變幻不定的流水表達了世事無常;在《宣州謝脁樓餞別校書叔云》中“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用極為形象的語言表達了愁緒無法決斷的痛楚。
三、見微以知著,托物以言志
言為心聲。在李白的詩歌當中,許多關于對水的描寫,往往從中透露出作者的思想狀態或人生感慨,也就是所謂的托物言志。這樣他通過水來構造自己的精神天地,通過水來釋放自己的憤懣情懷。如“鳳凰臺上鳳凰游,鳳去臺空江自流。”(《登金陵鳳凰臺》)寫出了繁華不再物是人非的歷史感慨;“桃花流水窅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山中問答》)化用了典故,表達了自我安慰之外的郁悶;“我來圯橋上,懷古欽英風。唯見碧流水,曾無黃石公。”(《經下邳圯橋懷張子房》)寫出了懷才不遇的苦悶;“牛渚西江月,青天無片云。登高望秋月,空憶謝將軍。”(《夜泊牛渚懷古》)寫出了無人賞識的惆悵。
袁行霈先生說:“詩的意象帶有強烈的個性特點,最能見出詩人的風格。詩人有沒有獨立的風格,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是否建立了他個人的意象群。”李白在詩歌當中對水意象的經營極其鮮明地反映了他的精神特質和內在感情,突出地顯示了他的個性特征。在這些包容性極大的“水”意象里頭,不僅融入了詩人的生命感悟,而且強烈地體現了詩人的生命精神,也反映了他所生活的那個時代的特征。可見“水”意象在李白詩中頻繁出現絕非一種偶然而簡單的文化現象,值得我們加以重視和深入研究。
參考文獻:
[1]袁行霈,《中國文學史》(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袁行霈,《中國詩歌藝術研究》(修訂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