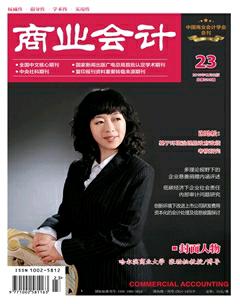多理論視野下的企業(yè)慈善捐贈內(nèi)涵評述
沈弋 徐光華
摘要:企業(yè)慈善捐贈已經(jīng)成為人們?nèi)找骊P(guān)注的熱點(diǎn)話題,文章從企業(yè)慈善捐贈的理念出發(fā),系統(tǒng)地回顧了企業(yè)慈善捐贈的概念,以及其在多種理論視野下的不同內(nèi)涵,最后對后續(xù)研究進(jìn)行了展望和評論。研究對理解企業(yè)慈善捐贈的內(nèi)涵以及相關(guān)文獻(xiàn)脈絡(luò)有一定的梳理和啟發(fā)作用。
關(guān)鍵詞:慈善捐贈 企業(yè)社會責(zé)任 評述
一、背景
2015年6月12日,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及社會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共同發(fā)布了《慈善藍(lán)皮書:中國慈善發(fā)展報告(2015)》。報告顯示,“我國目前符合環(huán)保公益訴訟主體資格的社會組織數(shù)量約為300家。截至2014年年底,全國共有正式登記的社會組織60萬個,比2013年度增長9.7%,且全國直接登記的社會組織超過3萬個。社會團(tuán)體30.7萬個,民辦非企業(yè)單位28.9萬個,基金會4 044個,分別比2013年增長了6.2%、13.3%和13.9%。”更為引人注目的是,2016年3月16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了《慈善法》,這標(biāo)志著我國的慈善事業(yè)進(jìn)入了一個新的時期,而慈善捐贈也已經(jīng)成為企業(yè)家無法回避的話題。
二、企業(yè)慈善捐贈的概念
大部分關(guān)于慈善捐贈的研究都沒有提到慈善捐贈的概念,Gautier和Pach(2015)在回顧了過去將近30年162篇學(xué)術(shù)論文后發(fā)現(xiàn),只有17%的論文闡述了他們對慈善捐贈的定義的理解,而事實(shí)上,學(xué)術(shù)界對于慈善捐贈的定義并不一致。按照Gautier和Pache的歸納,慈善捐贈的概念從“利他”到“利己”可以分為三類:首先,慈善捐贈被認(rèn)為是一種對公共的無私承諾,是一種公共商品(Common Good),這是最為純粹的“利他”型慈善捐贈概念,是一種超越經(jīng)濟(jì)利益的給予,是企業(yè)社會責(zé)任的最高表現(xiàn)形式(Carroll,1991)。其次,慈善捐贈被認(rèn)為是對其所處環(huán)境的投資(Community Investment),持這一派觀點(diǎn)的學(xué)者認(rèn)為,慈善捐贈雖然在短期內(nèi)對企業(yè)的經(jīng)濟(jì)利益有負(fù)向的影響,但是從長期看,依然能夠?yàn)槠髽I(yè)帶來豐厚的經(jīng)濟(jì)收益(Davis,1973)。最后,慈善捐贈也被認(rèn)為是一種市場手段(Marketing),例如,Murray等(Murray and Montanari,1986)就認(rèn)為,慈善捐贈可以成為公司產(chǎn)品的一個組成部分或者本身就是一種產(chǎn)品,這種產(chǎn)品幫助企業(yè)滿足某些特定的公共需求,因而慈善本身就是一種市場手段。
雖然從文獻(xiàn)的角度,可以將慈善捐贈的定義分為以上三類,但并不是說慈善捐贈只可以被分為這幾類,以上的三個定義更多地是從三個不同的側(cè)面反映了慈善捐贈的內(nèi)涵,同一個捐贈事項(xiàng),可能是一個企業(yè)市場運(yùn)作的一部分,但畢竟慈善不是企業(yè)進(jìn)行市場運(yùn)作的唯一選擇,因此一個企業(yè)選擇慈善作為市場運(yùn)作的途徑,反映了企業(yè)管理者“利他”的偏好和慈善之心。
三、利益相關(guān)者理論視野下的企業(yè)慈善捐贈內(nèi)涵
根據(jù)沈洪濤(2005) 的考據(jù),利益相關(guān)者這一概念最早出現(xiàn)在1963年斯坦福研究所(The 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現(xiàn)在的斯坦福研究所國際公司SRI International, Inc.,簡稱 SRI)的一份內(nèi)部文件稱,利益相關(guān)者是指 “那些如果沒有他們的支持企業(yè)組織將不復(fù)存在的群體”。在此之后,F(xiàn)reeman(2010) 曾提出過一個關(guān)于利益相關(guān)者的經(jīng)典定義,他認(rèn)為“一個組織里的相關(guān)利益者是可以影響到組織目標(biāo)的實(shí)現(xiàn)或受其實(shí)現(xiàn)影響的群體或個人”。顯然這是一個對于利益相關(guān)者較為寬泛的定義,這樣的定義雖然可以廣泛地涵蓋利益相關(guān)者可能存在的各種形態(tài),但是也模糊了概念應(yīng)有的聚焦作用。一個企業(yè)的運(yùn)營,必然導(dǎo)致其周圍的各種人群都受到其影響,那么按照Freeman的定義,這些人都是利益相關(guān)者,但反過來看,哪些又不是利益相關(guān)者呢?顯然,過于寬泛的定義無法將利益相關(guān)者真正有效地從總?cè)巳褐袇^(qū)分出來。
與寬泛定義相對應(yīng)的,是Carroll(2014) 提出的相對狹義的關(guān)于利益相關(guān)者的定義,他認(rèn)為利益相關(guān)者是“指那些企業(yè)與之互動并在企業(yè)里具有利益或權(quán)利的個人或群體”,這一定義里強(qiáng)調(diào)了利益相關(guān)者應(yīng)具有對標(biāo)的企業(yè)潛在的“利益”訴求,以及對“權(quán)利”的要求。
慈善捐贈作為企業(yè)社會責(zé)任的一個組成部分,被認(rèn)為是滿足利益相關(guān)者的重要手段,并且,能為企業(yè)帶來長期的利益。基于企業(yè)IPO(Initial Public Offering)數(shù)據(jù),Jia和Zhang(2014) 的研究發(fā)現(xiàn),在IPO不同的階段、面對不同的利益相關(guān)者,慈善捐贈帶來的效應(yīng)有所差異。
利益相關(guān)者理論為學(xué)者理解慈善捐贈的后續(xù)效應(yīng)提供了一個寬泛的基礎(chǔ)性視角,慈善捐贈作為企業(yè)的“非主營業(yè)務(wù)”,其存在與企業(yè)理性經(jīng)濟(jì)人假設(shè)相悖,必然是受到了某些利益團(tuán)體的驅(qū)動,而其結(jié)果也必然反映了相應(yīng)利益團(tuán)體的訴求和反饋。因此從利益相關(guān)者角度出發(fā),能夠有效地將企業(yè)的利益聚焦在固定的利益群體上,進(jìn)而能夠合理地判斷相應(yīng)利益團(tuán)體可能產(chǎn)生的反饋。綜上,在利益相關(guān)者視角下,企業(yè)慈善捐贈不僅僅是利他之心的一種反映,同時也被賦予了企業(yè)平衡多個利益相關(guān)者的戰(zhàn)略內(nèi)涵。
四、制度理論視野下的企業(yè)慈善捐贈內(nèi)涵
雖然學(xué)界很早就意識到企業(yè)的經(jīng)營和發(fā)展必然受到其所在地制度環(huán)境的影響,但具體到制度環(huán)境如何影響企業(yè)社會責(zé)任的履行,相關(guān)的理論研究卻并不多。Jones(1999) 較早地建立了一個制度環(huán)境對于企業(yè)社會責(zé)任影響的理論框架,該研究認(rèn)為,社會文化、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以及公司盈利狀況等都會影響企業(yè)社會責(zé)任的履行水平。Campbell( 2007) 構(gòu)建了一個較為完整的理論分析框架,在該框架中,包含了國家法律、行業(yè)自律、獨(dú)立的第三方監(jiān)督、社會道德水平、工會組織以及交流通暢程度這六個方面,并認(rèn)為國家之間的制度差異會影響企業(yè)在不同國家的慈善決策。在一個強(qiáng)勢且運(yùn)行良好的管制范圍內(nèi),政府將會釆取積極的鼓勵措施,如免稅政策等,引導(dǎo)企業(yè)積極地參與慈善活動。存在健全而有效的行業(yè)監(jiān)管,特別是當(dāng)政府支持行業(yè)自我治理的條件下,企業(yè)更可能采取具有社會責(zé)任性質(zhì)的社會公益活動。非營利組織、媒體、學(xué)校、工會等組織對企業(yè)承擔(dān)社會責(zé)任具有普遍預(yù)期和關(guān)注情境下,企業(yè)的社會責(zé)任水平更高。
基于上述Campbell提出的制度理論分析框架,分析我國的制度環(huán)境對于企業(yè)慈善捐贈的影響可以看到,國家法律、行業(yè)自律和獨(dú)立第三方監(jiān)督在我國都相對缺位,只有政府是比較明顯地推動企業(yè)履行社會責(zé)任的力量。之前就有學(xué)者指出,在正處于經(jīng)濟(jì)轉(zhuǎn)型期的中國,政府由于財(cái)力所限,提供的公共產(chǎn)品不一定能滿足公共需求,因而政府更傾向于要求其轄區(qū)內(nèi)的企業(yè)履行捐贈等企業(yè)社會責(zé)任(Dickson,2003)。例如,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政府就曾公開發(fā)出要求,希望企業(yè)進(jìn)行捐贈以緩解在重大突發(fā)事件中公共產(chǎn)品供給的短缺情況,并且,在地震10天之后,上海證券交易所要求所有上市公司向市場披露其捐贈的情況(Zhang et al,2010; Jia and Zhang 2011)。由此可見,在制度安排下,我國政府成為推動企業(yè)慈善捐贈最重要的力量,而慈善捐贈也被賦予了政企利益紐帶的經(jīng)濟(jì)內(nèi)涵。
五、研究展望
雖然現(xiàn)有文獻(xiàn)對慈善捐贈的“前因后果”都進(jìn)行了系統(tǒng)的研究,但是依然還有很多方面有待進(jìn)一步的探索和驗(yàn)證。
首先,企業(yè)社會責(zé)任已經(jīng)成為企業(yè)戰(zhàn)略的一個組成部分,慈善捐贈作為企業(yè)社會責(zé)任中最為外界所關(guān)注的一項(xiàng),也應(yīng)該成為公司戰(zhàn)略的一環(huán)。現(xiàn)有研究大都將慈善捐贈作為一個單獨(dú)的戰(zhàn)略來考慮,例如,將慈善捐贈看作是公共關(guān)系管理戰(zhàn)略的一個組成部分,用于構(gòu)建更好的政企關(guān)系,但是,從更宏觀的背景看,公共關(guān)系也是公司整體戰(zhàn)略的一個組成部分,與公司其他經(jīng)營戰(zhàn)略需要形成相互的支撐,才能為公司整體提供價值,那么,慈善捐贈與其他戰(zhàn)略之間是否/如何形成戰(zhàn)略間的支撐?慈善捐贈又是否會影響別的戰(zhàn)略的執(zhí)行?這些因素都有待進(jìn)一步的研究。
其次,慈善捐贈屬于企業(yè)社會責(zé)任的一種,本文研究了同屬于企業(yè)社會責(zé)任的慈善捐贈與稅收貢獻(xiàn)之間的關(guān)系,而主流文獻(xiàn)一般認(rèn)為,企業(yè)社會責(zé)任還包含了勞動保護(hù)、環(huán)境保護(hù)等方面,后續(xù)研究可以進(jìn)一步研究企業(yè)社會責(zé)任的不同模塊之間的關(guān)系,以期拓展對企業(yè)社會責(zé)任行為的理解。
第三,現(xiàn)有對慈善捐贈的研究大都以企業(yè)視角為基礎(chǔ),事實(shí)上各類慈善基金會以及NGO組織也日益增多,那么,各類慈善組織的興起是否會對企業(yè)層面的慈善捐贈產(chǎn)生影響?專業(yè)的慈善組織在“慈善的競爭”中是將企業(yè)擠出,還是提供更專業(yè)的慈善捐贈服務(wù),導(dǎo)致企業(yè)更愿意捐贈?這些問題也有待后續(xù)的研究和探討。
最后, 2016年3月我國第一部慈善法正式出臺,這一法律的頒布和執(zhí)行,會對我國企業(yè)和個人的慈善捐贈有怎樣的制度性影響,也是后續(xù)亟待跟蹤研究的課題。
綜上,企業(yè)慈善捐贈不單內(nèi)嵌在公司戰(zhàn)略和經(jīng)營中,也與社會制度、文化相互融合、相互影響,這些都有待學(xué)者進(jìn)行深入的研究和討論。Z
參考文獻(xiàn):
[1] Campbell J L.Why would corporations behave in socially responsible ways?An institutional theory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7,32 (3): 946-967.
[2]Carroll A B.The pyramid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Toward the moral management of organizational stakeholders[J].Business horizons,1991,34 (4):39-48.
[3] Carroll A B, Buchholtz A K. Business and society:Ethics,sustainability,and stakeholder management[M].Nelson Education, 2014.
[4]Davis K.The case for and against business assumption of social responsibilities[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73,16 (2):312-322.
[5] Dickson B J. 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The party,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6] Freeman R E. Strategic management: A stakeholder approach[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7] Gautier A, Pache A.Research on corporate philanthropy:A review and assessment[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5,126 (3):343-369.
[8]Jia M, Zhang Z.Agency costs and corporate philanthropic disaster response:the moderating role of women on two-tier boards–evidence from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2011,22 (9):2011-2031.
[9] Jia M,Zhang Z.Donating money to get money:The role of corporate philanthropy in stakeholder reactions to IPOs[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2014,51 (7):1118-1152.
[10]Jones M T.The institutional determinants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1999,20 (2):163-179.
[11] Murray K B,Montanari J B.Strategic management of the socially responsible firm: Integrating management and marketing theory[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6,11 (4):815-827.
[12]Zhang R,Rezaee Z,Zhu J.Corporate philanthropic disaster response and ownership type: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sresponse to the Sichuan earthquake[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0,91 (1):51-63.
[13]沈洪濤.公司社會責(zé)任與公司財(cái)務(wù)業(yè)績關(guān)系研究——基于相關(guān)利益者理論的分析[D].博士學(xué)位論文,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