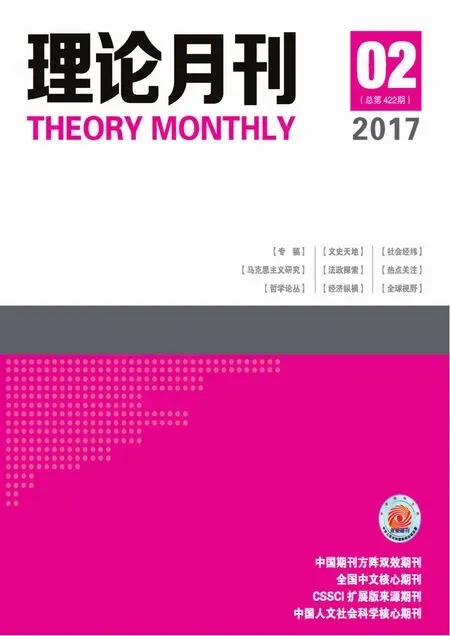從《共產黨宣言》的創(chuàng)作看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一致性
□許文星
(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北京 100871)
從《共產黨宣言》的創(chuàng)作看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一致性
□許文星
(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北京 100871)
《共產黨宣言》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中影響最為廣泛的作品。雖然《共產黨宣言》是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署名的,但學界對其主要作者一直存在爭論,甚至認為二者的思想不一致。在《共產黨宣言》完成之前,恩格斯曾寫過兩份草稿。比較兩份草稿和《共產黨宣言》的結構、用詞和內容,能夠更加清晰地確定他們兩人的理論貢獻是旗鼓相當的,他們的思想根本上是一致的,正如他們的合作構成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形成和發(fā)展的整個過程。
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草稿
《共產黨宣言》(以下簡稱《宣言》)在1872年首次重印后,成為世界社會民主運動中最重要的文件之一。這篇全文不到15 000字的綱領性文件,宣示了一種新世界觀的問世。恩格斯則在1890年序言中指出,《宣言》是全部社會主義文獻中傳播最廣和最具國際性的著作。斯大林甚至認為,馬恩《宣言》的問世創(chuàng)造了一個新的時代。但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是否一致,誰的貢獻大,仍是一個爭論不休的話題。比如麥克萊倫認為《宣言》是馬克思的觀點,而熊彼特則認為是恩格斯的觀點。本文要通過對《宣言》的寫作過程的論述和兩份草稿內容的比較分析,說明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宣言》的完成各有其貢獻,他們對共產主義運動和發(fā)展的觀點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1 從《共產黨宣言》的寫作過程看馬恩的一致性
《宣言》的寫作緣起于共產主義者同盟在新綱領上的需要。共產主義者同盟是由流放到巴黎的德國手工業(yè)者于1836年創(chuàng)立的一個秘密社團組織,原名“正義者同盟”。正義者同盟于1846年由巴黎搬到倫敦后,1月20日,倫敦通訊委員會決定派莫爾去布魯塞爾請求馬克思的幫助,并邀請他參加同盟。3月,馬克思恩格斯所創(chuàng)立的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被并入正義者同盟。在1847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正義者同盟后,同盟召開大會決定接受馬克思的提議,改名為“共產主義者同盟”,以下簡稱“同盟”[1]164-169。在此之前,同盟內部曾受到魏特林,社會主義的右傾機會主義(以克利蓋為代表),卡爾·格律恩鼓吹的蒲魯東主義,以及傅里葉主義的影響,亟需一個統一的、有約束力的綱領來確定同盟的思想核心。在11月29日,同盟召開第二次大會,馬克思和恩格斯提交了一個黨綱草案,經過至少八個晚上的辯論之后,全體成員都支持他們所申訴的原則和第一次大會上已提出的章程草案。會議結束后,受同盟的委托,馬克思和恩格斯接受了寫一份綱領的任務。馬克思當時正在寫的《哲學的批判》,其主要內容基本涵蓋了《宣言》的第一章[2]65。
在寫《宣言》之前,共產主義者同盟曾于1847年6月2日至9日在倫敦召開第一次大會,但馬克思沒有參加,恩格斯則代表巴黎成員參加了大會。由代表大會所決定的綱領草案《共產主義信條草案》(以下簡稱《草案》),實際出自恩格斯之手。在馬克思動筆寫《宣言》之前,恩格斯還于1847年10月底至11月寫了另一份草稿,即《共產主義原理》(以下簡稱《原理》),用25個問題的問答闡述了共產主義的基本原理和無產階級革命實現的途徑等問題。學界曾有人認為同盟在11月和12月發(fā)出的兩份通告也算是草稿的“草稿”,但鑒于通告的簡略性和通告的作用,大部分學者并不認同。1847年12月下半個月,恩格斯和馬克思在布魯塞爾撰寫《宣言》,這時他們已從同盟中央那里得到了成文的討論意見。12月底,恩格斯有事前往巴黎,馬克思仍留在布魯塞爾寫《宣言》,于1848年1月完成了初稿并最后定稿。《宣言》未經任何更改就馬上在倫敦付印,并被同盟中央熱烈地通過,很快發(fā)到同盟成員手中,引起巨大的反響[3]92。恩格斯在其1888年英文版和1890年德文版上曾加了十二個注釋。《宣言》最初沒有署名。1850年,英國憲政派領袖喬治·朱利安·哈尼在為發(fā)表在《紅色共和黨人》周刊上的《宣言》英文節(jié)縮本寫的序言中才指明作者是馬克思和恩格斯。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則是在1872年的德文版上才露出作者的身份[4]。這也給學者猜測《宣言》的真正作者留下了空間。
《宣言》共分為四個部分,分別論述了資產者與無產者,無產者與共產黨人,對各種社會主義派別的批判,以及共產黨人對各種反對派的態(tài)度。通過簡單地敘述資產階級產生的歷史和兩大階級的對立狀態(tài),在明確資產階級的功績的前提下,指出資本主義社會將必然滅亡。由于革命的需要,共產黨人在理論和實踐中都起著重要的作用,而共產主義的目標則是消滅資產階級的所有制,其根本的目的是要打破人剝削人的制度,建立一個“以各個人自由發(fā)展為一切人自由發(fā)展的條件的聯合體”[5]491。在解釋了共產黨人對不同反對派有不同態(tài)度之后,再次明確共產黨人的追求是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消滅資產階級的私有制。對于這些思想的來源者,學者們有不同的看法。對于馬恩在《宣言》中的不同理論貢獻及其思想是否一致,學界主要有以下三種觀點。
第一種認為《宣言》的思想主要來自馬克思。《宣言》比兩份草稿更加成熟,包含了全新的唯物史觀,而馬克思發(fā)現了唯物史觀[6]。其次,《宣言》的寫作過程就是馬克思幫助恩格斯進一步克服“真正的社會主義”殘余影響的過程。因為《草案》把共產主義看作是一種“理想制度”,《原理》把共產主義看作是一種“理論原則”,《宣言》則視之為一種“現實運動”[7]14-21。麥克萊倫甚至認為,《宣言》實際上的寫作完全是馬克思一個人完成的。因為,正如恩格斯后來曾說:“基本思想完全是屬于馬克思一個人的”,馬克思雖然極為廣泛地吸收了其中(恩格斯草稿)的思想,但馬克思根據法國工人階級的經驗,更多地強調政治[1]177。
第二種觀點認為,《宣言》是馬恩新世界觀的第一次系統闡述,包含了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根本批判,這主要是恩格斯的思想。而馬克思后來在《資本論》中闡述的對資本主義經濟的觀點,在《宣言》中已經形成了。熊彼特就認為,直到1843年并且包括1843年在內,馬克思對經濟學還沒有產生任何特殊的興趣。在巴黎,部分是由于受恩格斯的誘導,馬克思才取得了比較重要的進展。只是在19世紀50年代期間,他才成為當時最有學問的經濟學家之一[8]。
第三種觀點認為馬恩對《宣言》作出了同等貢獻,二者思想根本一致。梅林認為,根據文章風格的判斷,馬克思大概在最后的修改中起了主要的作用。不過從恩格斯的草案也可以看出,恩格斯在理解方面并不低于馬克思,因此他理應被認為是《共產黨宣言》的同等權利的作者[9]191。J.D.亨利和巴加圖利亞也認同這種觀點[10]54-60。
從上述學者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從不同的理論視角和側重點來分析馬恩思想,可能得出不同的結論。麥克萊倫更為強調《宣言》中政治思想的突破,熊彼特更看重經濟思想上的成就,而梅林則綜合考慮了寫作風格、過程以及思想內容。從《宣言》醞釀以及寫作的整個過程來看,恩格斯比馬克思更早參與到《宣言》的寫作準備階段,他完成的兩份草稿收到了同盟內部的討論意見,是《宣言》寫作的基礎。從1847年12月下半月正式寫作開始到12月底,恩格斯和馬克思共同進行了約半個月的討論和起草,1月份馬克思動筆完成了《宣言》的寫作,應該說其中體現的是兩人已經達成一致的思想。但由于表述者的不同,難免與恩格斯的文風有別。
從內容上看,筆者認為,在一般意義上,馬克思主義包含了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三個組成部分,這三者統一于《宣言》中。只強調某一方面并不能說明《宣言》的思想主要來源于誰。因此,應當詳細地比較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思想的差異。而恩格斯在《宣言》寫作前完成的兩份草稿,提供了恩格斯思想的真實寫照;馬克思執(zhí)筆完成《宣言》,也使透過《宣言》研究馬克思的思想成為可能。盡管恩格斯在草稿完成后思想可能有些變化,但通過比較兩份草稿和《宣言》,仍然可以得出馬克思和恩格斯之間異同。
2 《宣言》與《共產主義信條草案》、《共產主義原理》的關系看二者的一致
正如前文提到的,《共產主義信條草案》是恩格斯所寫的第一份草稿,完成于1847年6月;《共產主義原理》則是第二份草稿,完成于1847年10月至11月。以下從兩份草稿與《宣言》的寫作形式、對主要的定義和內容上的差異三點進行比較。
首先,恩格斯的兩份草稿均采用了問答的形式。馬丁·洪特認為,在這一草案中,人們還能清楚地看出仍有參考空想共產主義者拉波納雷的《教義問答》之處。綱領草案仍然沿用教義問答的形式并自稱為“信條”[10]83。而《宣言》則采用了歷史敘述的論證方式,證明共產主義的必然性。值得注意的是,正是恩格斯提出要改變草稿中的問答形式,這種改變是由內容決定的。他在致馬克思的一封信中寫道:“我想,我們最好是拋棄那種教義問答形式,把這個東西叫做《共產黨宣言》。因為其中必須或多或少地敘述歷史,所以現有的形式是完全不合適的。”[11]123。從中也可以看出,二者對《宣言》的大體內容已經達成了共識。另外,巴加圖利亞曾經制作了一份表格來說明兩份草稿和《宣言》在結構上的異同。他認為,所有三個文獻在結構方面是彼此相符的。《草案》的1-6條在《原理》中作了修改,在《宣言》中刪掉了。其7-12條、13-22條分別對應《原理》中的1-13條、14-23條和《宣言》的第一、二章。《原理》增加了第24、25條,分別對應《宣言》第三、四章。顯然,共同的東西已經包含在《宣言》之中,《宣言》第一章第一部分,現在是作為歷史發(fā)展的經過來評述的;接著研究社會將進行的變革和作為這種變革的最終結果的共產主義(第二章)。《宣言》的內容是從《草案》和《原理》中發(fā)展而來的[12]214-215。

《草案》(條)《原理》(條)《宣言》(條)1-6作了修改——7-12 1-13一13-22 14-23二——24三——25四
其次,比較對同一概念或同一問題在不同文本中的定義。其一,對“共產主義”的定義基本相同。《草案》定義為:“使社會的每一個成員都能夠完全自由地發(fā)展和發(fā)揮其全部才能和力量,但并不因此而損害這個社會的基本條件”,這與《宣言》中“每一個人的自由發(fā)展是所有人自由發(fā)展的條件”雖然表達不同,但含義基本相同,差別在于后者將個人發(fā)展對其他人發(fā)展的作用更直接地表達出來了,而前者僅限于消極的不損害。其二,“無產階級”的內涵相同,特征為出賣勞動而不是靠資本維持生活,但在《草案》和《原理》中是通過區(qū)分“無產者”和“奴隸”、“農奴”、“手工業(yè)”者來明確其特征的,而這些人都屬于勞動階級。《宣言》中最初并沒有對“無產階級”或“無產者”加以定義,而是恩格斯在1888年以注釋的形式定義的。不同的是,對于無產階級的禍福、存亡,在《草案》和《原理》中認為取決于生意的好壞或競爭的波動,而在《宣言》中則指出“無產階級是現代社會的最下層,它如果不摧毀壓在自己頭上的、由那些組成官方社會的階層所構成的全部上層建筑,就不能抬起頭來,挺起腰來。”[5]477其三,對“無產階級是如何產生的”這一問題的解答,在《草案》和《原理》中,恩格斯都指明是由于產業(yè)革命帶來的生產力發(fā)展,使得工人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勞動來維持生存。由于生產不斷擴大,資產者的勢力不斷擴大,手工業(yè)者和小資產階級的破產使得無產者越來越多,進而形成一個階級。工人的民族性和宗教最終將隨階級的消失而消失。但《宣言》則使用了“生產關系”這一概念加以論證。這是馬克思在剛剛完成的《哲學的貧困》中首次提出并使用的。其四,《原理》中對生產發(fā)展導致市場世界化的論述,在《宣言》中也得到了進一步的發(fā)展。《宣言》提出了“文化的全球化”趨勢:“各個民族的精神活動的成果已經成為共同享受的東西。民族的片面性和狹隘性已日益不可能存在,于是由許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個世界的文學。”[5]470其五,《原理》第十三個問題在解釋周期性經濟危機的結果時,提出兩個結論,即:“現今的一切貧困災難,完全是由已不適合于時間條件的社會制度造成的;用建立新社會制度的辦法來徹底鏟除這一切貧困的手段已經具備。”[5]364《宣言》中的“兩個必然”是其更加精準的概括。其六,對于實現無產階級統治、消滅私有制的措施,在《草案》中,列舉了三類措施,分別為限制或轉變私有財產為共有、企業(yè)國營化和教育公共化;在《原理》中,則有順序地列舉了12個更為具體的措施。《宣言》則取消了順序的要求,列舉了10個措施。比較《原理》和《宣言》中的措施發(fā)現,所有的措施都是《原理》中已經提及或明確提出的,但《宣言》中的語言更為簡練、明確。另外,在兩份草稿和《宣言》中都論述了生產的發(fā)展將導致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分化和矛盾、共產主義運動的世界性。最后,兩份草稿和《宣言》都論及了共產主義將導致家庭依賴關系和私有制的消失。
另外,對比《宣言》,有些內容是前兩個草稿中完全沒有的。
其一,《宣言》中通過對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辯證發(fā)展來描述人類歷史,清晰的表達了唯物史觀的主要內容,簡明概括而又不失清晰地說明了資產階級是如何產生,又將如何滅亡的。《原理》則沒有使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原理。恩格斯在1888年版序言中也曾經指出,《宣言》中唯物史觀的思想主要是來自馬克思的。
其二,《宣言》提出了無產階級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條件下孕育產生的,正是資產階級本身在進行階級斗爭的過程中,培育了與自己進行未來的階級斗爭的敵人——工人階級。《宣言》中寫道:“在這一切斗爭中,資產階級都不免要向無產階級呼吁,不免要向無產階級求援,因而不免要把無產階級卷進政治運動里。于是,資產階級自己就把自己的一部分知識授予了無產階級,也就是把反對自身的武器授予了無產階級。”雖然在《原理》中也論及無產階級的壯大和不滿情緒的增長會導致無產階級革命,但這種論證還不能準確地說明無產階級為何能戰(zhàn)勝資產階級。
其三,一個較大的差異在于,《草案》和《原理》中,恩格斯對革命所抱持的態(tài)度與《宣言》不一樣。《草案》中,在論述了對“密謀”的反對和“革命到來”本身的客觀規(guī)律性后,恩格斯寫道:“但我們也看到,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的無產階級的發(fā)展都受到有產階級的暴力鎮(zhèn)壓,因而是共產主義者的敵人以暴力促成革命。如果被壓迫的無產階級最終被推向革命,那時,我們將用行動來捍衛(wèi)無產階級的事業(yè),正像現在用言語來捍衛(wèi)它一樣”。對恩格斯來說,采取暴力促成革命有一種無奈,是迫不得已的選擇。在《原理》第十八問“這個革命的進程將是怎樣”的解答中,恩格斯指出:“首先無產階級革命將建立民主制度,從而直接或間接地建立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假如無產階級不能立即利用民主來實行直接侵犯私有制和保證無產階級生存的各種措施,那么,這種民主對于無產階級就會毫無用處。”[5]367而在《宣言》中,則明確提出“無產階級首先必須取得政治統治,上升為民族的階級”,“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無產階級變成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要做到這一點,當然首先必須對所有權和資產階級生產關系實行暴力的干涉”[5]489。可以說,在《宣言》中,已經明確了使無產階級取得政治統治、成為統治階級的手段,是暴力革命。這就摒棄了兩份草稿中的猶豫。這大概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最大的不同。恩格斯曾在1895年3月6日寫的《法蘭西階級斗爭·導言》中,論述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無產階級進行選舉斗爭的必要性和適宜性,指出這種新的斗爭方式是符合《共產黨宣言》的原則的,因為“《共產黨宣言》早已宣布,爭取選舉權,爭取民主,是戰(zhàn)斗的無產階級的首要任務之一。”雖然恩格斯1846年10月23日《致布魯塞爾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的信中提到共產主義的宗旨之一是:“除了進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認有實現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11]75。從時間上來看,《草案》寫于這封信之前,而《原理》則成于這封信之后,這說明雖然恩格斯在寫這封信時認定要進行暴力的民主革命,但他仍未作出最終確定的選擇。
而最大的不同在于,《宣言》中明確了共產黨與其他黨派的區(qū)別,批判了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空想社會主義和“真正的社會主義”等各種錯誤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確立了黨的宗旨、目標和特征。這是兩份草稿中完全沒有涉及到的。《原理》最后雖然論及了如何對待其他政黨,自然涉及共產黨與其他政黨的區(qū)別,但相比《宣言》則用詞模糊,更沒有明確黨的任務,即推翻當前的政治制度、尤其是所有制和爭取所有民主主義政黨的團結協作。
綜上,《宣言》的署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是有道理的。《宣言》與兩份草稿的結構基本一致,而恩格斯兩份草稿中的大部分經濟學內容在《宣言》中都有所體現并進行了擴充。馬克思對《宣言》的重要作用則體現在對唯物史觀的集中論述,以及對無產階級專政和暴力革命手段的確定上。馬克思的語言更為明確,對政治革命有更強烈的追求,使得《宣言》原本的內容極富感染力和宣傳性,他確定了革命的方式、過程和共產黨的性質,體現了《宣言》作為第一個共產黨綱領的作用。而恩格斯對經濟學的研究和對資本主義經濟的認識則構成了革命正當性的來源。所以,《宣言》的內容應該說是兩個人各有不同的貢獻。
3 結論
從上文對《共產黨宣言》的比較分析中可以看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合作并不是一時興起的選擇,而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重要因素。馬克思的深厚哲學功底和政治追求,恩格斯的豐富社會經驗和經濟思想,都在《共產黨宣言》以及其他合作著作中相得益彰,并對他們各自的研究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馬克思主義理論正是在他們的合作中形成并不斷成長,最終成為指導無產階級及整個人類解放事業(yè)的偉大理論。
窺一斑而知全豹。在《宣言》這一重要理論成果中,對馬克思和恩格斯二人作用的評價,與“如何看待馬克思和恩格斯對馬克思主義的貢獻”和“馬恩思想是否有差異”這些問題直接相關。在國際上,從19世紀末開始,歷史上曾有三次反恩格斯的浪潮,國際上逐漸形成了“馬恩對立論”(以諾曼·萊文和卡佛為代表)和“馬恩一致論”,到20世紀90年代以后,“馬恩差異論”開始逐漸興起。國內學者多堅持“馬恩一致論”,比如,張奎良和趙家祥認為,馬恩在理論上的不同特色構成了他們一生合作的基礎,他們在本質上是一致的。也有少數學者堅持“馬恩差異論”,比如,俞吾金認為,馬恩的合作并不能說明他們之間不存在差異,他們在哲學的研究出發(fā)點和發(fā)展趨勢、自由和自然的基本觀點上是不同的;何中華也認為,承認馬恩的差異,有助于還原二者的本來面目。本文通過比較《宣言》與兩份草稿之間在結構、術語和內容上的異同,意在說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融合于馬克思主義理論中,他們各自的優(yōu)勢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形成構成了互補式的推動,他們之間的差異恰恰促成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偉大發(fā)展,使馬克思主義理論成為包含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的一部指導社會現實的“百科全書”。
[1]戴維·麥克萊倫.馬克思傳[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
[2]馬丁·洪特.《共產黨宣言》是怎樣產生的[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
[3]倪力亞.恩格斯與《共產黨宣言》[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87(6).
[4]曼弗雷德·克利姆.馬克思文獻傳記[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6]李銳.簡析《共產黨宣言》創(chuàng)作史中的“創(chuàng)作者問題”[J].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43(3).
[7]姚順良,夏凡.馬克思是《共產黨宣言》思想的主創(chuàng)者—兼與巴加圖利亞、卡弗等學者商榷[J].學術月刊,2008,40(8月號):14-21.
[8]J·A熊彼特.《共產黨宣言》在社會學和經濟學中的地位[J].馬克思主義與現實,1997(3).
[9]弗·梅林.馬克思傳[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191.
[10]魯克儉.國外馬克思學研究的熱點問題[M].北京:中央編譯局,2006:54-60.
[1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23.
[12]聶錦芳.清理與超越:重讀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礎與方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責任編輯劉宏蘭
10.14180/j.cnki.1004-0544.2017.02.002
A811
A
1004-0544(2017)02-0010-05
許文星(1986-),女,山東臨沂人,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