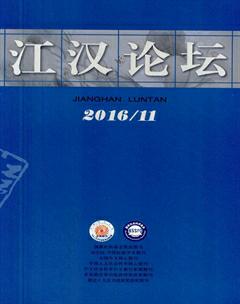“和”的本質在于“生”
朱貽庭
摘要:史伯提出的“和實生物”是地道的中國哲學話語。萬物由“和”而生,“和”是事物生存的最佳狀態和生命之源。“和”的本質在于“生”。儒家提出“中和”,由“中”而“和”,回答了“和”何以可能,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補充并發展了“和實生物”。 “和”體現在社會倫理上,就是“義分則和”,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社會由此得以和諧、統一、強大和發展;體現在人類認識發展上,就是務“和同”而拒“專同”。人類認識和文化的發展同樣遵循著“和實生物”的法則。“和生”較之“和合”更能概括中國傳統“和”文化的特征;作為中國傳統“和”文化的標識,是“和生”而不是“和合”。
關鍵詞:和生;和合;和同;專同
中圖分類號:B2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54X(2016)11-0043-07
當人們幾乎都一致認同“和合”為中國傳統“和”文化標識之時,錢耕森教授經多年的潛心研究和學術積累,將早于孔子提出“和而不同”前200多年西周末史伯的“和實生物”與老子的“道生萬物”歷史地聯系起來,并打通二者,結合時代精神,進行了轉化和創新,提出了“大道和生學”這一理論框架,對傳統“和”文化做了一種新的哲學概括和發展。史伯的“和實生物”即“和生”概念,視“和”為事物存在的最佳狀態和生命之源,揭示了“和”的本質。“和”的本質是“生”。“大道和生學”的提出,將為進一步深入發掘和展示傳統“和”文化的哲學精義開辟新的思想路徑,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受之啟發,本文擬從本體論、倫理學、認識論等三個理論層面,就“和”與“生”、“和生”與“和合”、“和同”與“專同”等三對概念,論述“和實生物”的哲學精義,表明“和生”較之“和合”能更確當地概括中國傳統“和”文化的特征,因而能更好地成為中國傳統“和”文化的標識。
一、“和”與“生”
將“和實生物”——“和生”概括為宇宙之“大道”,是錢耕森教授對古典中國哲學“和”思想的新概括。
“和生”作為宇宙之大道,首先體現為萬物生生之道。孔子提出“和而不同”(《論語·子路》),但是如果單講“和而不同”而不及“和實生物”(《國語·鄭語》),論“和”就有可能就和說和,為和而和,“和”就會成為目的本身而閹割了“和”的本質。史伯的“和實生物”之所以更為精深,在于它揭示了“和”的辯證法實質是“生”。就是說,“和”的目的不是“和”本身,而是“生”,是萬物的生命和發展。據此,我在多年前就明確表示贊同錢耕森教授的觀點:古典中國哲學關于“和”的思想,與其說是“和合”哲學,不如說是“和生”哲學。
在古典中國哲學中,“和”與“同”相對而定義,從而形成了古典中國哲學的一個重要論題,即所謂“和同之辨”。西周末史伯首先提出“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對“和同之辯”作出了極具辯證法智慧的回答。他論述說:“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生)之……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謂“和實生物”。“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同一種東西相加就不會有新事物的產生;“聲一無聽,色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是謂“同則不繼”,這是從本體論的高度揭示出事物生成和發展的辯證法。以此為據,史伯認為周“殆于必弊者也”。因為周幽王“去和而取同”,拋棄與己不同卻是明智有德之人,而寵愛投己所好的奸邪昏庸之人;厭惡與己不同卻是賢明之人。而親近與己相投的頑固愚昧鄙陋之人。這是棄“和同”而“與剸(專)同”。如此,“欲無弊,得乎?”(以上所引史伯語均見《國語·鄭語》)史伯認為,君臣之間應務“和同”而拒“專同”,展現了“和實生物”辯證法思想對現實的穿透力。春秋后期齊國大夫晏嬰重申了史伯的思想,也認為“和”與“同”異,主張“和”而反對“同”。他說:“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火單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左傳·昭公二十年》)
《易經·乾·彖》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這是對“和實生物”的另一種表述。“乾道”即天道。天道的自然變化使萬物各得其屬性之正。而萬物各正性命。方能達致“太和”(“大和”即太和)。高亨注:“太和非謂四時皆春,乃謂春暖、夏熱、秋涼、冬寒,四時之氣皆極調諧,不越自然規律……天能保合太和之景象,乃能普利萬物,乃謂天之正道。”由太和而始生萬物,于是才有萬國之安寧。我們無從確考《乾·彖》與史伯“和實生物”出現之先后,但可肯定的是,無論是“和實生物”,還是“保合太和,乃利貞”都是從本體論的高度,將“和”認定是萬物生生不息的本源。道明了“生”作為“和”的本質。《易傳·系辭下》所謂“天地姻缊,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說的也是“和”與“生”的本質關系;反之,“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易經·革·彖》),說明同性同居,就不能化生新生命體,也就是“同則不繼”。顯然,史伯提出“和實生物”和《易經》表述的“保合太和,乃利貞”,奠定了古典中國哲學“和生”哲學的基礎:它明確地揭示了中國“和”文化的本質特征——“生”。《易傳·系辭下》所謂“天地之大德日生”,正表述了古典中國哲學“和”文化的本質。總之,“和乃生,不和不生”(《管子·內業》)。
史伯的“和實生物”和《易經》的“保合太和。乃利貞”,作為一種萬物生成法則的哲學理念,對以后的諸子哲學產生了重要影響。他們用陰陽這對更為普遍性的哲學范疇提升了“和實生物”的本體論思想。《老子》所謂:“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也即“和實生物”。《淮南子·汜論訓》所謂:“天地之氣,莫大于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即為其解。荀子也說:“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荀子·禮論》),又說“萬物各得其和以生”(《荀子·天論》)。《淮南子·天文訓》表述為:“陰陽合和而萬物生”,而《中庸》所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顯然都是吸收了“和實生物”的思想。
與“和實生物”相一致,孔子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我們認為。“和而不同”雖與“和實生物”相一致,但又有其思想特點。孔子講“和”,同時又提出“允執厥中”(《論語·堯日》),即“中庸”這個概念,《中庸》作者將二者合為一詞——“中和”,突出了“中”對“和”的哲學意義。于是,正如提出“和合”學的張立文教授所說:“啟動了‘和同之辨向‘中和之辨的轉機”。這一轉機的關節點,就是由“和”而“生”,轉為由“中”而“和”。前者回答的是“和”為了什么?后者回答的是“和”何以可能?我們認為,唯有這二者即“中和”與“和生”的融合,才是中國傳統“和”哲學的全貌。只講“中和”而不講“和生”,“和”只是指一種事物存在狀態,或是指一種處事方法,那就有可能趨向保守。唯有將“中和”與“和生”融合一起,才是我們所應繼承和發展的傳統“和”的哲學。
《中庸》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按照理學家的解釋,“中”即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恰到好處,是天道之本原狀態;“和”是“中”之用,即“中庸”,實際是用“中”;《說文》:“庸,用也。”朱熹《論語集注》:“庸,常也。”所謂“中庸”,即“用中以為常道也”。“中”與“和”是“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以“中”為體而達致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恰到好處,也就達到了“和”。南宋理學家陳淳說:“那恰好處,無過不及,便是中。此中即所謂和也。”(《北溪字義·中和》)《中庸》提出“中和”,給“和”以本體論的根據,在哲學上回答了什么才是“和”以及何以致“和”的問題。這是對孔子講“和”的發展,也可以認為是對“和實生物”的“和”的補充和展開。就是說,唯有達到了“中和”,事物才得以“生”。由此達成了“和實生物”的儒學形態。“和實生物”及其轉機為“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或曰“中和生物”,實現了“中和”與“和生”的融合,即由“中”而“和”,由“和”而“生”,充實并達成了“和實生物”作為宇宙萬物生生之道的理論構成。
這一概括萬物生生之道的思維模式后由王夫之做了總結性的發揮。王夫之在《張子正蒙注,卷一》解“一物兩體”、“兩故化”時說:“自太和一氣而推之,陰陽之化自此而分,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原本于太極之一,非陰陽判離,各自孳生其類。故獨陰不生,孤陽不成,既生既成,而陰陽又各殊體。其在于人,剛柔相濟,義利相裁,道器相需,以成酬酢萬變之理,而皆協于一。”“太極之一”即“太和一氣”,內涵陰陽,因兩(陰陽)故化,化而有陰陽之分,但分而不離,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如此才能化生萬物。王夫之特別指出,“獨陰不生,孤陽不成”,體現了“和實生物”的哲理。總之,“和”就是“生”,就是生命。“和生”思想是中國哲學的一大傳統,體現了中國哲學的基本精神,揭示了中國傳統“和”文化的本質特征。
“和實生物”表明“和”是宇宙萬物生存發展的常態。萬物由“和”而生,由“和”而存,由“和”而生生不息。如果不同事物之間或構成事物的內部各要素之間,不能“以他平他”,而是相互對抗不可兩存,各自以消滅對方為目的,以求得“專同”,那么事物生命體也就喪失了存在和發展的生機。在這種情況下,生命體就會破裂,事物的發展就會終止,即所謂“同則不繼”。無數正反兩方面的事實和經驗都已表明,“和”是事物生存發展的常態,“和實生物”是宇宙生生不息的常道。它在肯定事物“不同”(矛盾)的基礎上凸現了矛盾的“統一”;矛盾斗爭不是為了“專同”,而是為了“和生”。“和生”,是中國人用自己的哲學話語對“矛盾對立統一”這一宇宙發展之根本規律的表述,體現了中國哲學辯證法的特點。這就是我們贊同“大道和生學”的緣由。
張立文教授講“和合”雖也包括了“和生”,把“和生”作為“和合”的一種形態。但這顯然降低了“和生”在其“和合學”中的地位和價值。我們認為,與其說“和合”包含了“和生”,不如說“和生”包含了“和合”。和與合,實際上是同義詞,王夫之就說:“和也者合也”(《尚書引義,禹貢》)。或曰,和而合;合,聚合、合作,都體現不出“和”的本質。因而作為一個概括宇宙之大道的哲學范疇,“和合”一詞顯然不及“和生”更能確切地概括宇宙生生之道。《淮南子·天文訓》說:“陰陽合和而萬物生”,“和合學”所表述的“和合”,僅就概念的用詞而言,只取“陰陽合和”而未及“萬物生”,至少可以說是用詞欠當,而“和生”一詞就避免了用詞缺陷。“和”的本質在于“生”,在于“生生不已”。“和”是為了發展、為了更好的發展。僅僅用“和合”一詞,不能體現“和”的本質。
看來,要真正把握中國傳統的“和”文化,必須回到“和實生物”。只提“和”或“和合”,顯然(至少在用詞上)沒有能展現“和”在于“生”這一中國哲學的基本精神和“和”文化的本質。
二、“和生”與“和合”
“和生”也是社會和諧——發展之道。
儒家倡“和”,代表了中國傳統“和”文化的主流。然而,儒家“和”思想的根本所指,是內涵“和”倫理價值的社會制度結構,即“禮”制。或者說,是指“禮”結構的制度倫理。在儒家看來,所謂和諧社會,首先是指體現了“和”倫理的社會制度。唯有建構起“和”的社會制度,這個社會才能生機勃勃、和諧發展。這里正體現了“和實生物”。
由“和實生物”可知,“和”是一個關乎事物結構即事物及其內部諸要素之間“以他平他”結構的哲學概括。在社會,“和”是對社會諸要素“以他平他”結構的倫理定位;而社會結構體現為某種制度,所以作為社會結構倫理定位的“和”也就是一種制度倫理。我們認為,儒家倡“和”,其特點是將“和”引入價值領域,從而指向“禮”的制度倫理。孔子的弟子有子說:“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論語,學而》)這是學界論述儒家關于社會和諧思想的重要依據。但所論往往執著于“和為貴”一詞,將“和”與“禮”分離開來,僅僅理解為和氣、和睦、和善、友善等美德,這顯然不符合有子這段話的本義,
其實,“和為貴”是對“禮之用”即禮之功能和作用的價值陳述。據所云“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可知,“禮”的作用在于節制各等級身份及其行為,使其行為符合禮的規定,既不“過”,也不“不及”,即“中節”,體現了孔子的“中庸”思想。劉寶楠《論語正義》明確指出:“有子此章之旨,所以發明夫子中庸之義也。”蔡尚思先生也認為:“‘禮之用,和為貴,是他(指孔子)治國之道的中庸。”楊伯峻《論語譯注》也以《中庸》注“和”,并引楊樹達《論語疏證》:“事之中節者皆謂之和……。《說文》云:‘和,調也。‘盉,調味也。樂調謂之和,味調謂之盉,事之調適者謂之和,其義一也。和今言適合,言恰當,言恰到好處。”“中節”,也就是合乎“禮”。這一解釋,與“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相契合。如是,“禮之用,和為貴”,其意謂:禮的作用,最珍貴的就是“和”,也就是使各等級身份及其行為既不過也無不及,達到恰到好處。如果僅有“和”的認識。而其行為不能中節于“禮”的制度,“和”也是不可實現的。可見,“和為貴”之“和”。按其本義是相對于“禮”——宗法等級制度而言的。在孔子看來,君臣父子,各有嚴格的等級身份,若能各安其位,各得其宜,使尊卑上下恰到好處,如樂之“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就是“和”。這里的“和”,即是指內在于“禮”制的結構性的“和”。所以朱熹說:“如天之生物,物物有個分別。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至君得其所以為君,臣得其所以為臣,父得其所以為父,子得其所以為子,各得其利。便是和”。又說:“君尊于上,臣恭于下,尊卑大小,截然不可犯,似若不和之甚。然能使之各得其宜,則其和也孰大于是!”顯然,“禮”之“和”,是指各等級“無相奪倫”,互不侵犯,也就是各安其位,諧而不亂。借用孔子自己的話說,就叫做“和而不同”。這是“禮”作為宗法等級制度應有之義,就是說,“和是禮中所有”,是“禮”之能“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內在的結構性功能和價值屬性。這正是孔子之所以贊美“周禮”的緣由所在,體現了孔子獨到的“禮”倫理觀。顯然,“禮之用,和為貴”的“和”,講的是一種制度倫理,而不是指一般的道德規范和美德。它表明了這樣一種社會倫理模式——既等級有序又和諧統一,這也就是孔子所理想的“道”。孔子認為“周禮”正符合這樣一種“和”的制度倫理的社會結構和社會制度。
孔子關于“和”是“禮”內在的制度倫理的這一思想,荀子做了發展,提出了“義分則和”的命題。他說:“(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義。故義(以)分則和。”(《荀子·王制》)荀子認為對社會資源作適當或合宜的“分”,就能達致各等級之間和諧(“能群”)。其實質就是要構建一個以“禮”為制度安排的和諧社會,以達到社會的“有序和諧”。“義”,宜也,適當之謂。“分”既是動詞——分配。也是名詞——名分,是一種制度安排,意謂上下貴賤的等級分得適當,即所謂“制禮義以分之”,使“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荀子·富國》)。“有稱”,合宜也;《荀子·君子》篇的說法是:“貴賤有等,則令行而不流;親疏有分,則施行而不悖;長幼有序,則事業捷成而有所休。故……義者,分此者也。”這是對“義分”內容的明確表述。“義”又具體體現為各等級的行為規范。用來調節君臣上下的關系,即所謂“內節于人而外節于萬物者也,上安于主而下調于民者也。內外上下節者,義之情也”(《荀子·強國》)。這樣,社會各等級既分得合宜,又各有適宜于自己等級身份的行為規范,即所謂“義、分相須”。“義分”,實際上就是“禮”的制度安排。由此就能使各等級各安其分、各得其宜,就能使各等級身份及其行為“無相奪倫”、互不侵犯而恰到好處,于是社會在整體上達致和諧,這就是所謂“群居和一之道”。就是說,只要使社會資源在社會群體中分得合理,“和”即在其中了。所謂“義分則和”,實際上就是內涵于“禮”的“和”這一制度倫理的價值實現。
荀子用“分”與“和”來表述“禮”與“和”的關系,這不是簡單的語詞轉換,而是理論的升華,也是對其“禮論”思想的哲學概括,從制度倫理的理論層面上回答了社會怎樣才能和諧,“禮”何以具有“和”的功能。由荀子思想的語境看,“分”已具有社會資源分配(包括分配原則和分配制度)的概念實質。或者說,荀子已在理論上確立了社會資源分配的思想。荀子提到的所要分的社會資源,除了財貨,還有政治權力、勢位和文化教育資源。可見,荀子“分”的概念,非僅僅是指經濟學意義上的分配。他的“禮論”就是這一“分”概念的具體運用。
關于“分”的思想,很可能先由法家提出。商鞅變法,主張“作為土地貨財男女之分”(《商君書·開塞》)。慎到也曾明確提出“分”的概念:“一兔走街,百人追之,貪人具存,人莫之非者,以兔為未定分也。積兔滿市,過而不顧,非不欲兔也,分定之后,雖鄙不爭。”顯然,荀子的“分”受到早期法家的影響。不過,早期法家言“分”旨在為法制立論,即所謂“法以定分”,而荀子講“分”則為禮制立論,即所謂“分以定倫”。確實,荀子講“義分則和”,深涵著這樣一種思想智慧:要構建和諧社會(“和”),就必須構建合理的分配制度,對稀缺的社會資源作合宜的分配(“義分”),即達致分配“公正”。
從本文對“禮之用,和為貴”的解讀可知,儒家的“和”,既指人與人之間“和敬”、“和親”、“和順”的道德情感,也指“和睦”、“和諧”、“和平”的價值理念,但主要的、更深層次的是指通過制度安排使人際倫理關系處于恰到好處的狀態。這種狀態(“和”)本身就是制度安排應有之義,是“禮”作為一種制度所具有的結構性功能。因而,構建一種合理、公正的社會資源分配制度體系,對于構建和諧社會有著基礎性的至關重要的意義。這里內涵著相當深邃的制度倫理智慧,即社會要達到和諧,在基礎性的意義上,就應從制度安排上保障社會成員能各安其位、各盡其職和各得其所,使德有所福,能有所祿,勞有所得。這樣,就會如朱熹所說:“各得其利,便是和”;“各得其宜,則其和也孰大于是”!也就是說,只要社會資源分配的制度安排得當,那么“和”也就在其中了。
而怎樣才是“義分”——合宜的分配原則和分配制度?就結果而言——在宗法等級制的社會結構中——當然是要達到“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但在荀子看來,要實現“義分”,其關鍵在于“分”之“義”的確定。他反對“以世舉賢”,而主張“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這是對傳統的權位分配原則和制度即等級世襲制的變革,認為“分”之“義”必須適應于變革了的經濟關系和社會結構,也就是宜于時代的變革趨勢。這里,荀子實際上提出了社會資源再分配的主張,其中包涵著一種普適性的“古今通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要實現社會和諧,構建和諧社會,必須站在時代的高度,適應變革的現實,確立合乎新的經濟關系和社會結構的再分配的原則和制度,實現新的“義分”,構建新的和諧。這是荀子提出“義分則和”的精義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荀子提出“義分則和”,不僅對孔子關于“和”(“禮之用,和為貴”)的制度倫理思想作了理論論證,而且進一步指明了制度的“和”所能發揮的作用和力量。如果說孔子指出了“禮”的社會價值(貴)在于“和”,那么荀子則進一步指出了“和”的功能和價值在于“一”、“強”,在于“勝物”。他說:“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故宮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時,載萬物,兼利天下,無它故焉,得之分義也。”(《荀子·王制》)這就是說,唯有“分”得合宜(“義”),從而實現社會和諧,社會才能統一、強大和發展,才能上下一致、齊心協力,戰勝各種困難,達致“序四時,載萬物,兼利天下”。由此道明了構建社會和諧的目的不在于“和”本身,而在于社會的統一和發展——“生”。這體現了儒家社會倫理思想中的“和實生物”。
三、“和同”與“專同”
“和實生物”還是人類認知發展之道,指明了如何在多元和多維認識矛盾中推進人類認識發展的基本路徑。
史伯根據“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的辯證法,在認識論的層面上還提出了務“和同”而拒“專同”的思想。史伯認為周幽王只相信身邊那些阿諛奉承、應聲附和的佞臣,就是搞“專同”。相反,周“先王聘后于異性,求財于有方,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國語·鄭語》)。這里所說的“和同”的“同”顯然與“專同”的“同”有別。“專同”也就是晏嬰所說的“專一”;“和同”的“同”是“講以多物”即不同事物的對立統一。可見,史伯講“和”并沒有排斥“同”;他既講“和生”又講“和同”,“和同”正是“和生”應有之義。因而不能說史伯講“和”而“忽視了‘同”。他只是反對“專同”。史伯提出的“和同”,雖言涉君臣關系,具有政治含義,但又包含著深刻的認識論意義。
“和同”體現在認識論上,就是指不同的認識由“和”(“以他平他”)而取得共識。晏嬰在論述“和同之異”中的一席話道明了這層含義。他認為君臣之間的“和”應該是:“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左傳·昭公二十年》)所謂“以成其可”、“以去其否”,指的就是通過臣對君的不同意見(諫言)而使君臣認識達成一致,即通過不同意見的切磋、爭辯(諫與納諫),在“可”或“否”上達成共識;或使君進一步完善原有的正確決定,或使君認識到自己的錯誤而拋棄原來的決定,使認識得到正確的提升和發展。如此達到的“同”可稱之為“和同”。而隨聲附和或憑借自己的淫威使別人服從自己的意見而達到的“同”,就是“專同”。“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史記·商君列傳》)在歷史上,趙高藉淫威所搞的“指鹿為馬”鬧劇,造成秦二世身邊無一諤諤之士,結果如殷紂王一樣“墨墨而亡”。這就是搞“專同”的典型。而丞相魏征與唐太宗李世明之間的諫與納諫的關系,則是另一番情境。唐太宗十分尊重并聽取魏征的諤諤之言,推行正確的政策而“諤諤以昌”,成就了“貞觀之治”。這就是君臣達成“和同”的典范。在文化史上,搞“經學”獨斷論是“專同”,而儒、佛、道三教由鼎立而走向合流是“和同”。儒佛道合流不僅產生了禪宗這一完全中國化的佛教,而且促成了融合佛道的新儒學即宋明理學的形成,使儒學得以繼續成為中國古代文化的主干和主導的意識形態,這是“和實生物”辯證法在文化發展上的生動體現。在現代的語境下,搞“專同”就是不允許有不同的意見,甚至剝奪別人有發表不同意見的權利,也就是排斥不同的觀點,扼殺文化和學術的發展生機(“同則不繼”)。所以要推動學術的發展,就應務“和同”,倡導百家爭鳴,反對文化專制,拒“專同”。其實,世界上沒有什么“絕對真理”,一種學說或一個人的認識即使是相對真理,也總會有一定的缺陷和局限性,明智的人通過鑒別,會虛心地聽取并吸收與己不同的正確意見和觀點,以糾正和突破自己認識的缺陷和局限,達到與不同觀點的“和同”,從而發展已有的學說和認識。顯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基礎上實現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和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和實生物”的辯證法在文化發展上的偉大勝利。
應該指出,從人類認識發展的總過程來看,達到了“和同”也非一勞永逸,不是認識的終止。也就是說,達致“和同”并不意味再也不存在、再也不會產生不同的觀點和意見了。事實上,人的認識是隨著實踐的推進而不斷發展著的,這種不斷變化和發展的認識成為原有“和同”的否定性力量,因而人類認識過程中的“和同”是動態的、發展的,永無止境的。這一認識發展過程的辯證法規律,用《周易·系辭下》的話來概括就是:“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著名哲學家、哲學史學家馮契教授對之曾做了精辟的闡述,他說:“‘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表述了一個認識的規律。人類的認識只有通過不同意見(包括不同觀點)的爭論。經過邏輯論證和實踐檢驗,才能明辨是非,達到一致結論。而隨著社會實踐的發展,一致又化為百慮,百慮再化為一致,表現為一個螺旋式上升的無限前進的運動。”因此,“從辯證法的觀點看,百慮不應忘記一致,一致亦不應排斥百慮。求一致而能兼綜百慮,便具有兼容并包精神”。明清之際思想家王夫之在發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時就質疑“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之說,認為這種主張就是所謂的“萬法歸一”。他認為“萬法歸一”就終止了認識的發展。因為,若使殊途百慮之“歸一”,就會“橫立此疆彼界于大同之中”。或用行政強力或以“獨斷論”的思想專制來限制百慮,使人們“思其無所思,慮其無所慮”,從而取消“百慮”,于是就會窒息人類認識的發展。這就是說,“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是封閉的,而“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是開放的。王夫之認為,認識達到“一致”(即史伯所說的“和同”)還會繼續有“百慮”的存在和產生,從而持續不斷地推進認識的發展。這正是“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的辯證法之精義所在。在王夫之看來,“殊途而同歸”,追求“萬法歸一”,就會導致“舉一而廢百”,這是“霸者之術”。這里所說的“霸者之術”,也就是史伯所反對的“與剸(專)同”。“專同”在認識論上就是獨斷論。可見,“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是“和同”,是務“和同”而拒“專同”的深一層的意思,也是“和實生物”的辯證法思想在認識論上的展開。
“務和同”就要求“兼綜百慮”,即務不同認識之間的對話方式而拒兩元對立的思維方式。晏嬰說的“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實際上就是一種不同認識之間的對話方式。君臣之際尚且可以進行這樣一種民主式的對話方式,更何況相互平等的個人與個人、學者與學者之間呢!對話(不是對抗),是不同觀點、不同意見之間理性的切磋、爭論,并對對方的思想觀點作“同情的理解”,作出合理的評價,達到相互補充、吸收,從而提高自己原有的認識,推進學術的發展,實現“和而不同”、“和實生物”。按照古典中國哲學的“中和”思想。對話的各方都應堅持無過不及的“中道”,不可把自己的觀點和別人的觀點推向極端;把自己的觀點視為絕對正確,而將別人的觀點視為絕對錯誤。這種認識上的極端就是兩元對立的思維方式。持這樣的思維方式去與他人進行爭辯,必然要搞“專同”。是不可能達到“和同”的,當然也不可能實現認識的提高和學術的發展。貫徹“百家爭鳴”,最忌諱的就是持兩元對立的思維方式。
用兩元對立的思維方式進行辯論,論者的做派必然是唯我獨尊、唯我獨“美”,似乎“真理”全在我手中,容不得別人有不同的觀點和意見,搞徹底批判,堅決打倒,直至置他人于死地而后快。在這種情況下,怎么可能達到不同意見、不同觀點之間的“和同”?又怎么可能實現學術的“和生”呢!凡是反映某種實踐經驗并經過深思熟慮的觀點和理論,無論是歷史的還是現實的,都有自己的存在的理由,都應該得到尊重。而認識又總是有著一定的歷史的和現實的局限,這是人們認識發展過程的必然現象。因此,人們對于不同的觀點和理論應該相互尊重、相互寬容。我可以批評別人的意見,但又必須尊重別人有發表與己不同觀點的權利;既要允許別人犯錯誤,又應歡迎別人修正自己的錯誤。
在認識論上堅持“和實生物”的辯證法,實現多元或多樣學術觀點的“和同”、“和生”。一個關鍵因素就是要確立和提升學者的學術主體性或曰自覺性。學術對話當然是學者主體間的對話,然而,學者的“主體”如果只是作為一種學術承載的實體,那就不是也不等于學術“主體性”。學者的“主體”和學術“主體性”不是同一個概念。學術主體性是主體對自身學術的自覺,包括主體的意志自由和獨立人格,以及對自身學術的反思精神。從而具有創新和發展自身學術的自信心和提升自身學術水準的追求,以及確立“務和同”的理念。“主體”既可以是真正具有主體性的,也可能是對自身學術帶有很大的盲目性的。盲目性往往表現為自利(某種功利目的)、自負(唯我獨美)、自欺(自以為是)、自傲(以勢壓人、盛氣凌人)或自卑(如“一切都不如別人”)。而具有學術主體性的主體,則表現為自重、自信,自強、自歉、求真、大氣。同時又尊重對方,有寬容精神。因而,學術主體性也就是學者的德性。唯有達到了學術主體性境界,主體間才能進行真正的學術對話,做到如荀子說的“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辨”,使辯論“貴公正而鄙賤爭”(《荀子·正名》),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這樣才能“美美與共”,達致多元或多樣學術觀點的“和同”,實現學術的發展。因此,能否進行學術對話,考驗著主體的文化素養:不同學術觀點間能否進行對話,是對不同學術主體是否確立了學術主體性的檢驗。那種唯我獨美,唯我獨尊,處于學術盲目性的主體是不可能進行真正的學術對話的。唯有不斷提升主體性,才能實現不同學術的“和同”,實現“和實生物”,推動學術的發展,
以上論述尚未窮盡“大道和生學”的內涵。事實上,“和實生物”的辯證法還體現在人自身的心理世界和德性修養、人與自然的生態領域等各個方面。“和實生物”是地道的中國哲學話語。概括了世界上一切事物生存、發展的普遍法則。我們這里所述只是想表明:“生”是“和”的本質和靈魂,講“和”而不講“生”,就“和”論“和”,就會丟失中國傳統“和”文化的靈魂。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贊同錢耕森教授的觀點:應該將中國傳統的“和”文化表述為“和生”學。
(責任編輯 胡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