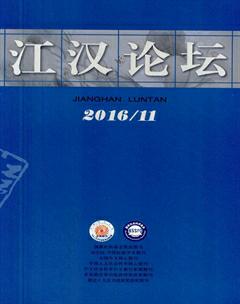唐高宗刺顱出血與中外醫學交流新論
王顏 杜文玉
摘要:永淳二年,侍醫秦鳴為唐高宗刺頭出血治療頭風,這一歷史事件引起了中外學者的高度關注,涌現出一批研究成果,或認為秦鳴鶴為大秦人,或認為其醫術來自大秦,或認為來自印度,遂使這一事件成為學界爭議不斷的話題。筆者收集了大量資料,進行了認真地研究。針對以上觀點,層層剖析,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新觀點,還原了歷史真相。
關鍵詞:針刺出血;開腦出蟲;眼科;中醫
中圖分類號:K2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54X(2016)11-0111-09
唐永淳二年(683),秦鳴鶴為高宗刺頭出血,成功緩解了高宗“目不能視”的癥狀。秦鳴鶴,這個生卒年月不詳,來去不明的微小人物,連同他神奇的醫術一起被載入史冊,成為后人一直津津樂道的話題。新中國建立后,隨著學術界對唐代中外文明交流認識的不斷深入,秦鳴鶴及其醫術再次成為熱門問題,人們為此爭議不斷。
長期以來,學術界圍繞秦鳴鶴其人及其為高宗治病所使用的醫術,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其一,秦鳴鶴為大秦人。早在1926年,日本學者桑原騭藏在《隋唐時代來往中國之西域人》一書中,根據秦鳴鶴之醫術近乎外國“穿頭術”而推測其可能為大秦人。這個論斷得到了國內大部分學者的支持。由于唐代景教源自大秦,一些學者如方豪等人則進而推測其為景教徒。雖然國際知名醫史學者馬伯英先生對這一觀點有疑問,但因無法用中醫解釋“刺百會”治眼,所以只好將信將疑的將秦氏采用之法歸結為大秦醫術,進而認為秦鳴鶴可能是從大秦來的醫生。其二,秦鳴鶴之醫術與印度醫學有緊密關系。其三,與前面兩種觀點不同的是,近年來有學者指出,秦鳴鶴的醫術屬于中醫針灸范圍,非域外放血療法,與景教醫術無關。
綜合以上幾種觀點,筆者想就永淳二年秦鳴鶴為高宗診療一事談談自己的幾點不成熟看法,為中古時期中外文化交流中的這一問題提供新的思路。
一、引言
唐高宗在唐代歷史中往往是以贏弱的形象出現的,這種贏弱不僅反映在政治上,還反映在他的身體上。從現有史料記載來看,高宗李治還是皇太子時,在太宗皇帝駕崩時便“哀毀染疾”。從顯慶五年(660)以后的20多年間,他一直被風疾困擾,“風眩頭重,目不能視”,雖經多方診治,然終究效果不佳。
在為高宗治療風疾的眾多醫人中,秦鳴鶴及其醫術尤為引人注目,引起了中外學者的諸多爭議。永淳二年(683),高宗突然頭風發作,御醫秦鳴鶴為其診治。“帝頭眩不能視,侍醫張文仲、秦鳴鶴曰:‘風上逆,砭頭血可愈。后內幸帝殆,得自專,怒曰:‘是可斬,帝體寧刺血處邪?醫頓首請命。帝曰:‘醫議疾,烏可罪?且吾眩不可堪,聽為之!醫一再刺,帝曰:‘吾目明矣!言未畢,后簾中再拜謝,曰:‘天賜我師!身負繒寶以賜。”類似的記載在《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鑒》及《大唐新語》中都有,雖然各書的記載在文字上略有出人,但基本意思是一致的。
二、刺顱出血還是開腦出蟲
從上引史料來看,秦鳴鶴為高宗實施的治療方法應是針刺出血法,這是一種中國傳統的醫學技術。但現代學者中卻有人將此技術與域外醫學聯系起來,得出其為域外醫術的結論。
現代學者認為秦鳴鶴之方法近似西方開顱法的,多是因為受到桑原氏的影響,桑原氏認為秦氏所采用之醫術近乎外國“穿頭術”,雖然桑原氏并沒有完全肯定外國之穿顱術與秦鳴鶴之法相同,但由于他將兩者聯系起來,因此使得一大批學者將秦鳴鶴之醫術乃至其人進一步與域外聯系了起來,得出了秦鳴鶴乃異國奇醫的結論。
“開腦出蟲”疑即鉆顱術,或稱環鉆術,主要是為了減輕因頭骨骨折發生腦水腫或腦溢血癥狀產生的顱內壓力。許多施行過穿顱術的頭骨在其施術部位或其鄰近部位,存在骨折現象。此法在新石器時代已流行于美索不達米亞、古埃及等地,世界各地幾乎都有考古發現。近來年,隨著中國考古活動的深入,帶有病理治療色彩的開顱術案例在中國也有不少發現,特別是2001年在山東廣饒傅家村大汶口文化遺址392號墓發現的一個顱骨將我國開顱手術歷史上推到5000年前,該顱骨右側頂骨有31×25mm的橢圓形缺損,“根據體質人類學和醫學X光片、CT檢查結果,392號墓墓主顱骨的近圓形缺損系開顱手術所致。此缺損邊緣的斷面呈光滑均勻的圓弧狀,應是手術后墓主長期存活、骨組織修復的結果。這是中國目前所見最早的開顱手術成功的實例。”
古希臘的希波克拉底和蓋倫精通鉆顱術,在《希波克拉底文集》中有這樣的記載:“這幾種形式的骨折和挫傷,不管能否看見及有無骨裂傷,都需要進行環鉆術探查。若多刃器還留在骨頭上,無論有無骨折或挫傷,同樣需要環鉆治療。但是凹陷性骨折只有范圍不大時才用環鉆術。若單純多刃器損傷而無骨折及挫傷,可不必實行環鉆術。骨裂傷嚴重時,亦不用環鉆術。”這種開顱術在唐代的醫書中并無明確記載,也不清楚其是否真實使用過。
中國學者將唐代秦鳴鶴之療法與域外醫術聯系起來的主要文獻依據是,曾在大食等國呆過十多年的杜環在《經行紀》中提到:“大秦善醫目及痢,或未病先見,或開腦出蟲。”在《新唐書·拂蒜傳》中也有相似記載:“有善醫能開腦出蟲以愈目眚。”據此可見,唐人對域外之開顱術已有所了解,但這里的開顱主要指開腦出蟲,似與因頭骨骨折而實施鉆顱術仍有不同。
“腦中有蟲”之觀念在中國傳統的道教文獻中早有記載。道教中有三尸諸蟲說,“蟲有三名,伐人三命,亦號三尸。一名青姑,號上尸,伐人眼,空人泥丸。眼暗面皺,口臭齒落,鼻塞耳聾,發禿眉薄。皆青姑之作也。”上尸蟲在人頭中,使人頭部器官發病。針對人身中潛藏的尸蟲,中國古代著名醫學家華佗已有相應治療方法,他曾傳授弟子漆葉青黏散,此藥“久服去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隋唐時期,巢元方在《諸病源候論》中更指出大風病因就是由體內尸蟲造成的,“凡人身中,有八萬尸蟲,共成人身。若無八萬尸蟲,人身不成不立。復有諸惡橫病,諸風生害于人身,所謂五種風生五種蟲,能害于人。”
這種人身體中有蟲的觀念在印度的佛經中亦有記載,如《佛說·木加奈女耆域因緣經》中記載了印度神醫耆域具有的神奇醫術,其曾為一名因長年頭痛而垂死的女子治愈了頭痛。“耆域便進以藥王照視頭中,見有刺蟲,大小相生乃數百枚,鉆食其腦,腦盡故死,便以金刀披破其頭,悉出諸蟲,封著罌中,以三種神膏涂瘡。……七日晨明,女便吐氣而寐,如從臥覺。”耆域用金刀為患者破頭出蟲,從而使患者起生回死,并解除了她長期以來難以治愈的頭痛,這與開腦出蟲法極其相似。
雖然人身體中有蟲這一觀念在古代中國和印度都有,但從治療方法來看,兩者并不一樣,中國在唐代以前對于三尸諸蟲往往采用服藥、符咒或針刺等方法,沒有開腦之說。到了唐代后期,類似祗域的“開腦出蟲”療法才在文獻記載中有了一例:高駢出鎮維揚時,廣招名士,有一術士因家里著火,被牽連焚燒者數千家,高駢欲按律將其處以死刑,術士說自己“善醫大風”,請求將這門特殊技藝傳授與人,以解救后人。高駢要求術士驗證,術士遂從福田院中選了一位病情最重的進行試驗。具體操作方法如下:“乃置患者于密室中,飲以乳香酒數升,則懵然無知。以利刀開其腦縫,挑出蟲可盈掬,長僅二寸。然以膏藥封其瘡,別與藥服之,而更節其飲食動息之候。旬余,瘡盡愈,才一月,眉發已生,肌肉光凈,如不患者。駢禮術士為上客。”
上述“大風”即麻風,麻風病是麻風桿菌侵犯人體皮膚、神經等引起的如眉毛脫落、塌鼻、獅面相等具有傳染性的疾病。隋代巢元方在《諸病源候論》卷2“惡風候”中曾提到:“凡風病,有四百四種,總而言之,不出五種,即是五風所攝。一日黃風,二日青風,三日赤風,四日白風,五日黑風。凡人身中,有八萬尸蟲。共成人身,若無八萬尸蟲,人身不成不立,復有諸惡橫病,諸風生害于人身,所謂五種風,生五種蟲,能害于人。”但實際上據現代醫學研究,麻風病病源并不在腦部,也不會真的挑出蟲子,所以此病名可能只是一個假借。但“以利刀開其腦縫,挑出蟲可盈掬”確與“開腦出蟲”之術相合。
考察上述兩則事例,發現祗域與維揚術士為人開腦醫病之方法驚人的相似。一是兩者都是在患者失去知覺的情況下施行手術。雖然祗域施治時,其患者已因頭痛而死,但不排除是因頭痛過甚而暫時昏厥,而維揚術士則采用了藥酒麻醉法,令患者暫時失去知覺。二是兩者都曾開腦出蟲。三是開腦后都使用藥膏涂抹創口,以促進創口早日愈合。四是治療結束后需靜養。五是治療效果相當好,兩位患者都迅速痊愈,且沒有留下后遺癥。據此可見,雖然中國自古也有身體有蟲之觀念,但開腦出蟲可能是域外傳人中國之醫術。
不過值得關注的是,雖然這是兩個非常成功的醫療案例,但從其施治情況來看,這種醫術不論在印度,還是在唐朝,應該都是為人所不熟悉,并很難接受的。其所以最終成功實施,是有特殊原因的。從施治對象來看,祗域所治女子長年頭痛,想必各種治療方法都曾試過,但結果是女子終因劇烈頭疼而死亡,病人家屬才讓祗域施治。而維揚術士的施治對象是福田院中的病重者,福田院是唐代寺院創辦的慈善組織,用以收養貧窮孤獨患病之人,這些人生命卑微,沒人會在意他們的死活。福田院雖然能給他們提供簡單的生活和生存條件,但很難為其進行完備的治療。所以術士所選擇的那位病情最為危重者,當已承受了無盡的病痛之苦,因此甘愿一試。而術士此舉,不過是為保命,此后雖高駢待其為座上客,但并未見到其再治愈其他病人的例子。所以開腦出蟲也許并非十拿九穩。
開腦所出之“蟲”到底為何物呢,迄今為止沒有人給出準確答案。季羨林先生認為“出蟲”,可能是幻想,甚至連“開腦”這件事,他也以為可能是針刺的夸大,不可盡信。
“出蟲”到底是否幻想呢?筆者聯系另一則迄今為止在民間都頗有影響的治療方法,試大膽推測一下。譬如齲齒,又稱蟲牙,過去一直認為是因為牙齒被蟲子啃咬而損壞了牙齒,進而導致牙疼。《諸病源候論》中記載:“齒蟲是蟲食于齒,齒根有孔,蟲在其間,亦令齒疼痛。食一齒盡,又度食余齒。”即牙齒疼是因為有牙蟲在牙齒根部吃牙,當一個牙吃光后,又會去吃其他牙齒。《驗方新編》中說,當有蟲牙時,“五倍子,煎濃汁,含漱數次,其蟲立死,其患永除。”除此之外,民間還流傳了一種用韭菜籽或大蔥籽加熱后通過耳朵或直接薰烤病牙的方法,據說此法可以薰出數量不等的小小牙蟲,并能成功治愈牙疼。
但現代醫學已經證實齲齒的產生并不是因為牙蟲蛀壞了牙齒,而是牙齒被細菌及酸性物質腐蝕所致。齲齒發病開始在牙冠,如不及時治療,病變繼續發展,就會形成齲洞,最終導致牙齒完全喪失。牙疼則是因為牙齒被腐蝕,引發牙髓病變,導致牙神經劇痛。而那些堅持采用古老的煙薰法并信誓旦旦地認為真的有蟲子被薰出的人,他們所看到的那些長二三毫米,形似蟲子的不明物體,不過是被加熱的韭菜籽或大蔥籽膨脹后炸裂而形成的新芽。既然牙蟲是根本沒有的,那這種治療方法是無法解決根本問題的。
此處的牙齒之蟲雖然不存在,但確實是會出現一些類似物體,才造成了人們的錯誤判斷,所以這種現象或許可以用來推測開腦出蟲的情況。上文中提到的西方之開顱術,開顱后會取出骨折的顱骨,以及在《希波克拉底文集》第九卷所記載的治療眼睛失明的一種方法:“當眼睛毫無顯著病癥并失明時,可以在頭頂部切開,把柔軟的幾部分分開,穿過頭骨,使液體全部流出。這是一種療法,用此法病人便能治愈。”這種方法也可稱為開顱術,只不過是開顱引流。這兩種開顱方法在實施后。均有物體被取出或流出,雖然所取所流之物并非蟲子。推想在古代醫學不發達的情況下,開顱乃是大手術,旁觀者一定不多,且開顱之術,頭破血流,即使近旁有人相助,也實難直視,所以很有可能不加細究,而是通過外形來粗略判斷取出之物,再加上古代印度和中國深入人心的腦中有蟲之觀念。將取出之物視為蟲子就不難理解了。可謂心中有蟲,則眼中有蟲。
另外,明確記載西方開顱術的《希波克拉底文集》是被西方尊稱為“醫學之父”的古希臘著名醫生希波克拉底親自編寫的,他醫術精湛,醫學理論先進,其著作中的一些古老治療技術與心得都來自他的實踐經驗,作為專業人士,他更清楚開顱之后所出之物到底是什么,所以他的記載是相對真實可靠的。而不論古印度還是唐朝,關于開顱術的記載卻都來自非專業人士,這些人可能是佛教徒,也可能是文人,他們可能并沒有親自到醫療現場,只是靠道聽途說,再加上心中固有的一些醫療觀念,才形成了開腦出蟲之說,可謂以訛傳訛。
雖然季羨林先生認為“‘開腦這件事,可能是針刺的夸大,不盡可信”,但實際上根據文獻的記載,印度古典醫學中,外科已經較為發達,其外科主要治療外部器官,特別是頸部以上鼻、耳、目等首部諸病。其外科鼻祖蘇斯拉他,能切除腫瘤,還能穿刺囊腫及腹水等,并擅長白內障術、鼻成形術和整復骨折術、開腹術、剖腹產等。
佛教自秦漢時期傳入中國以來,印度醫學亦隨之傳人中國,對中國產生了巨大影響。佛經中有大量關于外科醫術的記載,如上引《佛說·木奈女耆域因緣經》中記載的神醫耆域,就具有神奇的醫術,他除了能用金刀披破人頭,取出腦中之蟲,使人迅速痊愈外。還能用利刃破腸,為人治病。
由上可知。古代印度和西方可能都實行過開顱術,并且可能曾在唐代傳人中國,才有了維揚術士的開腦出蟲之例。這是中外醫學在唐朝交匯的一個很好例證。但通過以上分析,可以斷定秦鳴鶴為高宗治療所用之術卻絕非開顱術。理由如下:
首先,開顱術施行前必須要麻醉,否則劇烈的疼痛使病人無法保持安靜,影響醫生的準確下刀。從上述“開腦出蟲”的事例中已看到,術士為病人開顱前,先讓其飲乳香酒數升,達到麻醉的效果。據馬伯英研究,乳香酒有阿拉伯、波斯特點,可能是中國醫生運用外來藥物后改良的麻醉藥。
其次,像開顱這種造成大面積創傷的外科手術。術后必須有縫合或采用其他方式來彌合創口,否則不容易痊愈。所以上述兩則事例中都有開顱后以膏藥彌封病人創口,再加上服藥、靜養,使病人創口很快結疤,最終達到痊愈。
縱觀所有記載秦鳴鶴為高宗診療事件的文獻,都沒有發現有以上術前準備和術后收尾工作。如果說是文獻記載對這些細節有所忽略的話,那在秦鳴鶴結束治療后,高宗能很快回答“吾目明矣!”顯然說明此次治療沒有實施麻醉,否則高宗無法立刻清醒的說出治療效果。且秦鳴鶴的治療工具明確記載為針,并非使用利刀。且刺入部位為百會、腦戶兩處穴位,而非腦縫。
此外,開顱必然會大量出血,而文獻中多次提到秦鳴鶴為高宗刺頭只是“微出血”或“出少血”;最后,開顱之后,都會從腦中取出一些物質,不論是碎骨或不明液體還是所謂的蟲子,但高宗頭上并沒有取出這些東西。綜合以上可以看出,秦鳴鶴之療法并非開腦出蟲。
三、針刺與眼疾
秦鳴鶴為高宗實施之療法是否與外來眼科醫術密切相關呢?
季羨林先生認為古代中國醫學受印度影響很大,而印度眼科尤為發達,且其眼疾治療方法在當時之中國廣為流傳,高宗之病雖在頭部,但兼及眼睛,所以秦鳴鶴為高宗治病之醫術當與印度眼科關系密切。陳明以為需要進一步了解當時波斯、大秦眼科技術的確切內容之后,才可能對秦鳴的身份和醫術做出清楚、準確的判斷。
根據文獻記載,針刺療疾在印度有悠久的傳統。這一點在義凈的《南海寄歸內法傳》中介紹的非常清楚。《南海寄歸內法傳》介紹了印度醫術的一般情況:“言八醫者,一論所有諸瘡,二論針刺首疾,三論身患,四論鬼瘴,五論惡揭陀藥,六論童子病,七論長年方,八論足身力。”在“針刺首疾”后面,義凈還加了一句:“首疾但自在頭。”這就將頭疾和針刺聯系起來。但印度以針刺治療頭疾的方法在唐代文獻中未見有明確使用的記載,而其眼科治療方法在唐代的知名度倒是相當高的。
唐代許多名人如白居易、劉禹錫、鑒真等都曾采用外來的醫學方法治療眼疾。如白居易有詩:“案上漫鋪龍樹論,盒中虛捻決明丸。人間方藥應無益,爭得金篦試刮看。”白居易被眼病嚴重困擾,不得不在服用治療眼病的藥物決明丸時。還翻閱醫書《龍樹眼論》,希望能從中找到更好的治療方法。在遍試諸方無效的情況下,白居易還透露出了打算用金篦術試刮眼膜,治療眼病。這里提到的《龍樹眼論》和金篦術都是來自古印度治療眼疾的方法,其中金篦術在治療白內障上更有獨特療效。
金篦術是指用金針刺入眼球,撥斷已經成熟的混濁晶體系帶,使其貼于角膜下方眼球壁內,不再阻擋光線進入。從而恢復光明。劉禹錫就曾做過這個手術。他請一位擅長治療眼睛的婆羅門僧人為自己施行金篦術。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這種幸運的事情不是每個人都能遇到的。鑒真在揚州逗留時,患了嚴重的眼疾,他也請了一位胡人治療,結果沒有成功,“眼遂失明”。
這種針撥治療白內障的醫術在南北朝時期應該就已經進入中國,《梁書》載:“后又目有疾,久廢視瞻;有北渡道人慧龍得治眼術,恢請之。既至,空中忽見圣僧,及慧龍下針,豁然開朗。咸謂精誠所致。”圓當然,這個針下在什么部位,采用什么手法,不得而知,但從豁然開朗的功效來看,應該是撥開云霧重見天日,推測可能是針撥白內障。但此道人是何身份,不得而知。
這種醫術在唐代不僅由婆羅門眼醫掌握,在其他胡人中也有非常精通者。如《樊川文集》中記載杜牧的弟弟杜顗在開成二年(837)時,眼疾發作,以致失明,遂請同州眼醫石公集為其診治。石公集看了杜顗的眼睛后說:“是狀也,腦積毒熱,脂融流下,蓋塞瞳子,名目內障。法以針旁人白睛穴上,斜撥去之,如蠟塞管,蠟去管明,然今未可也。后一周歲,脂當老硬,如白玉色,始可攻之。某世攻此疾,自祖及父,某所愈者,不下二百人,此不足憂。”顯然石公集對白內障的治療方法非常了解,知道必須等白內障成熟后才可以手術去除,所以請杜顗耐心等待,待其眼中白內障成熟之際,再行撥除。然而兩年后,當石公集認為可以治療時,卻接連兩次施針都沒有成功。無奈之下,杜顗只得另求名醫,請到了同州另一著名眼醫——石公集姑姑的兒子周師達,他的醫術也來自祖傳,所以與石公集醫療方法相同,但又比石公集更高明。周氏檢查了杜顗的眼睛后指出:“嗟乎!眼有赤脈。凡內障脂凝有赤脈綴之者,針撥不能去赤脈,赤脈不除,針不可施,除赤脈必有良藥。某未知之。”周氏比石氏高明之處就在于他能指出針撥白內障的禁忌癥,但遺憾的是他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即對不能施行白內障剝離術的情況只能指出,卻無法治療,所以最終周也是“不針而去”。杜顗之眼便始終不得治。除了石氏外,據蔡鴻生研究,唐代還有穆姓胡客亦擅長治療眼疾的。
當然,印度眼科的治療方法決不僅限于金篦術,在印度生命吠陀醫方和外科名著《妙聞本集》中,有大量關于眼科治療的藥物和方法。而這其中的有些方法和藥物也為唐人所認識。如烏賊魚骨,據陳明研究,在印度的許多醫方和成書于公元1世紀下半葉的古希臘《藥物志》中,均有對烏賊骨治療眼疾的認識。中國醫學家對烏賊骨的認識雖然很早,但在唐以前,中醫并未認識到烏賊魚骨有治療眼病的作用。到初唐蘇敬等修《神農本草》時才提到烏賊魚骨有治療眼病的功能。此后,唐人對烏賊骨能治眼病的功效才了解的更多了,在許多醫書中都提到了使用烏賊魚骨和其他藥物治療眼病的方法。《外臺秘要方》中收錄的治療目疾的藥方中有一個是《張文仲方》,張文仲是唐代名醫,以擅長治療風病而著稱,其治療眼疾的藥方中就有使用烏賊魚骨的記載。這體現了唐代醫人對外來文化的吸收。
實際上不止印度,在當時中國人的觀念中,大秦醫生也擅長治療眼疾。如上引杜環《經行記》中所載,大秦人善醫眼及痢。此外,李德裕也對大秦眼醫有記載:南詔攻入成都撤走,李德裕清點戶口,“蠻共掠九千人,成都郭下成都、華陽兩縣只有八千人,其中一人是子女錦錦、雜劇丈夫兩人、醫眼大秦僧一人,余并是尋常百姓,并非工巧。”此處“醫眼大秦僧一人”,在被擄掠的九千人口中被強調指出,可見大秦人確實擅長治療眼疾。
雖然以上材料顯示了隋唐時期外來眼科醫術在中國很受歡迎,其影響也較大,但從治療技術上來說,其與秦鳴鶴為高宗治療頭風并無關系。
四、中國傳統之針刺療法
通過以上層層剝離,足以顯示刺頭出血與外來鉆顱術及眼科治療術并無關系。而翻閱中國古代醫書,恰恰發現其與中國傳統針灸醫術高度吻合。雖然有學者已認識到秦鳴鶴之醫術能從中國傳統醫學范圍中找到依據。但他過多的將關注點放在政治因素上,對中國傳統醫學挖掘并不夠,沒有很好的將秦鳴鶴之療法與中國傳統醫學對接起來。
中國傳統醫學是中華民族在長期的生活、醫療實踐中積累總結而成的具有獨特理論風格和豐富診療經驗的醫學體系,它包括湯藥、針灸、外科、按摩、導引、食療等各種治療方法。
首先,從病情來看。從上引文獻資料中對高宗病癥的記載可知,高宗所患乃疾病在古代稱為“風眩”或“風疾”等,雖然這種疾病到底是現代意義上的什么疾病,現在還無確切結論,但在中國的傳統文獻中,患此類病癥的病人極多,如漢代大孝子酈炎,患有風疾,其母去世后,其病突然發作,“妻始產而驚死,妻家訟之,收系獄,炎病不能理對。”三國時的曹操,“苦頭風,每發,心亂目眩。”西晉時的劉聰也曾自言:“朕比得風疾。喜怒過常。”唐代患風疾的貴族也比比皆是,高宗之前,高祖、太宗都曾感染過風疾,其他官員和貴族等群體感染風疾的記載更是不絕于書,所以,風疾是長期困擾中國古人的一種常見病癥。
這種群體性的常見病癥,在中國傳統醫學著作中早有記載,《靈樞·大惑論》中說:“邪中于項,因逢其身之虛,其人深,則隨眼系以入于腦,入于腦則腦轉,腦轉則引目系急,目系急則目眩以轉矣。”《諸病源候論》中也說:“風頭眩者,由血氣虛,風邪人腦,而引目系故也。五臟六腑之精氣,皆上注于目,血氣與脈并于上系,上屬于腦,后出于項中。逢身之虛,則為風邪所傷,人腦則腦轉而目系急,目系急,故成眩也……風眩久不瘥,則變為癲疾。”這兩則材料表明風眩是因人體虛弱時,受到邪風入侵所致。當風侵入腦中,就會頭暈,頭暈又會影響眼睛,使兩目眩暈,視物不清。高宗之風眩病癥狀正與醫書所載相符合。而秦鳴鶴分析高宗病因時所說的“風毒上攻”、“風上逆”顯然也是來自于中國傳統醫學理論。
其次,從治療方法來看,由于風疾是長期困擾中國古人的一種疑難雜癥,漢晉以來的醫學家對其病因、癥狀及治療方法多有探索,總結出了不少治療方法。但主要還是以湯藥和灸法為主。
如《千金翼方》中所載:“圣人以風是百病之長,深為可憂,故避風如避矢,是以防御風邪,以湯藥針灸蒸熨,隨用一法,皆能愈疾,至于火艾,特有奇能,雖曰針湯散皆所不及,灸為其最要。昔者華佗為魏武帝針頭風,華佗但針即瘥,華佗死后數年,魏武帝頭風再發,佗當時針訖即灸,頭風豈可再發,只由不灸,其本不除。所以學者不得專恃于針及湯藥等,望病畢瘥,既不苦灸,安能拔本塞源,是以雖豐藥餌,諸療之要在火艾為良。初得之時,當急下火,火下即定,比煮湯熟,已覺眼明,豈非大要。其灸法,先灸百會,次灸風池,次灸大椎,次灸肩井,次灸曲池,次灸間使,各三壯,次灸三里五壯,其炷如蒼耳子大,必須大實作之,其艾又須大熟,從此以后,日別灸之,至隨年壯止。凡人稍覺心神不快,即須灸此諸穴各三壯,不得輕之,茍度朝夕以致殞斃,戒之哉,戒之哉。”這段文字表明,風疾是所有疾病中最令人困擾的。治療風疾的方法多樣,用湯藥針灸蒸熨,無一不可。但其中火灸是最具特效的。雖然三國時期的名醫華佗曾用針刺為曹操治療頭風,且下針即好。但華佗死后,曹操頭風再犯,可知單純針刺并不能完全根治頭風。所以孫思邈告誡學醫者治療頭風不可單純采用針刺或湯藥療法,而須與火灸結合起來,才能達到標本兼治的奇效。而且火灸一般是病情穩定后才采用的方法,病情緊急時還需用湯藥或其他方法。顯然針刺和湯藥療法一般是頭疾發作最劇烈時采用的,可以有效緩解病情,待病情穩定后再輔以長期火灸,便可徹底去除病根,萬不可因服食湯藥或采用針刺緩解了病情,便不再后續治療。
華佗用針刺之法為曹操治病的事情在《后漢書》中有明確記載:“操積苦頭風眩,佗針,隨手而瘥。”《三國志·華佗傳》中也說:“太祖苦頭風。每發,心亂目眩,佗針鬲,隨手而瘥。”華佗是三國時名醫,經其手治愈的疑難雜癥不計其數,可謂神醫。但這兩書中所記載的都是華佗僅采用針刺法為曹操治療頭風,并未有其它輔助措施。雖然曹操每次頭風發作,華佗都能“隨手而瘥”,卻也未能根除曹操的頭風之疾,“后太祖親理,得病篤重,使佗專視。佗曰:‘此近難濟,恒事攻治,可延歲月。”華佗雖醫術神奇,但即便他整日隨侍曹操,也不能遏制曹操之頭風病的惡化。
從以上材料可知,其一,頭風之疾可用多種方法治療,針刺療法只是方法之一;其二,頭風難治,須用多種方法相結合,尤其是用灸法結合其它方法,是治療頭風的上策;其三,華佗雖然是他那個時代的名醫,在各種疑難雜癥方面久負盛名,但對于頭風。他只采用了單一的針刺療法,所以他無法根治此病。而他之所以只采用單一的針刺法,并非他要暗藏絕技,密不示人,而是在他那個時代,就他個人來說,對頭風的治療還沒有更好的方法,只能用針刺法治療頭風。而孫思邈是隋唐時期的醫者,從漢到隋唐,經過幾百年的發展,中國的醫學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所以醫學家們總結出針刺以外,還須采用多種方法相結合治療頭風的經驗。
雖然從以上材料可以看出,針刺療法不是治療風疾的唯一方法,但確實是治療風疾的方法之一。在中國傳統醫學體系中,針刺療法著重對人體全身經絡的特殊穴位進行刺激,以疏通經絡。實施針刺療法的主要工具是九針,《靈樞·九針十二原》中對九針的形態及主療疾病都有詳細記載。
九針中,能夠刺絡出血的主要有鋒針和鈹針,有時也用镵針和毫針等,但使用不同的工具,其出血量是不同的。從秦鳴鶴所說的“微出其血”可知,其所使用的當是鋒針。因為鋒針的形狀是“刃三隅,以發痼疾”,相當于現在的三棱針,針人人體脈絡可使少量出血,達到治療疾病的目的。這種針刺出血療法在古代又稱“啟脈”或“刺絡”等,是中國傳統醫學中一種獨特的針刺治療方法,具有瀉熱、急救、止痛、消腫、鎮靜等醫療作用。
刺血絡能夠祛邪解表,在《素問·離合真邪論》中有明確記載:“此邪新客,溶溶未有定處也,推之則前,引之則止,逆而刺之,溫血也,刺出其血。其病立已。”
從秦鳴鶴為高宗施針部位來看,不同的史料記載中略有出入,上引新舊《唐書》中對所刺頭部穴位沒有明確記載,只表明在頭部。前引《資治通鑒》中記載鳴鶴所刺為頭部“百會、腦戶二穴。”《大唐新語》中則記載為“刺百會及月出戶出血。”關于放血的穴位,上述兩書記載略有不同,關于這一點,黃蘭蘭認為《中醫針灸學》中并無朏戶一穴,恐系筆誤。另外百會和腦戶穴是中醫所忌諱之穴,中醫鮮有在此二穴處放血的。
實際上,從傳統醫學文獻來看,刺血療法施針時多選擇四肢末端、頭部及病變局部穴位。在頭部百會和腦戶兩穴施針在文獻中是有明確記載的。如《素問》中所載“刺瘧者,必先問其病之所先發者,先刺之。先頭痛及重者,先刺頭上及兩額兩眉間出血。”所刺部位相當于頭頂部的上星、百會、兩額部的懸顱,兩眉間的攢竹等穴。三國兩晉時期的醫學家皇甫謐在《針灸甲乙經》中說:“百會。一名三陽五會,在前頂后一寸五分,頂中央旋毛中,陷容指,督脈、足太陽之會,刺入三分。灸五壯。”《備急千金要方》中也說:“‘風寒之氣客于中,滯而不能發,故痦不能言,及喉痹失聲,皆風邪所為也。入臟皆能殺人,故附之于治風方之末。凡尸厥而死,脈動如故,此陽脈下墜陰脈上爭,氣閉故也。針百會人三分補之。百會:‘主目不明,惡風寒。”以上資料說明,百會穴“主目不明”,如果頭痛頭暈是應該在百會穴施針放血的。
而腦戶穴亦“主頭重痛”,“主目痛不能視”,《針灸甲乙經》說:“頭重項痛,目不明,風則腦中寒,重衣不熱,汗出,頭中惡風,刺腦戶。”“腦戶,一名匝風,一名會顱。在枕骨上強間后一寸五分,督脈、足太陽之會,此別腦之會。刺入四分,不可灸,令人痦。”據此可以看出。頭痛目眩跟腦戶穴有關,通過針刺腦戶穴是可以治療頭痛目眩等疾病的。另外,此穴只可針刺不可灸。
據此可見,百會、腦戶二穴感染邪風在傳統中國醫學理論中均是引起人頭痛目眩的原因,對這兩個部位施針均可有效緩解病情。
通過以上各項分析可以看出,高宗之病乃當時國人之常見病,高宗之前,華佗已用針刺法為曹操長期診治,而秦鳴鶴之治療方案也并無新意,完全是中國傳統醫學治療方法的實踐。但促使諸多中外學者把目光放到域外,從域外醫學中去尋找其源頭的原因:一是因漢唐以來,中外文化交流空前頻繁,一些外來人口,尤其是僧侶,出于治療自身疾病的需求,也出于幫助宗教傳播的愿望,普遍傳播醫術和藥方,使中原人廣為受益;二來中國傳統的針刺療法雖然及時有效,但危險性也很大,所以醫者在采用此療法時多持謹慎態度。
針刺療法的危險性在《素問·刺禁論篇》中有詳細記載,其中提到了多種針刺禁忌以及施針不當可能造成的危險,嚴重者會使人致殘,或當即死亡。如針刺百會、腦戶二穴,雖是傳統中醫治療風疾的一種方法。但腦戶穴并非隨意可刺之穴,其事關生死。在《素問·刺禁論篇》中記載道:“刺頭中腦戶,人腦立死。”顯然,腦戶可以施針,但施針時必須把握好分寸,不能下針太深,否則針進人大腦,人會立即死亡。下針多深合適呢,前面所引《針灸甲乙經》中已明確提出:“刺入四分”。所以施針者需慎之又慎。
針刺療法的危險性在隋唐時期的醫學界是有共識的,《千金翼方》中引唐初名醫李襲興語:“夫欲行針者,必準軒轅正經;用藥者,須依《神農本草》。自余《名醫別錄》,益多誤耳。余退以《甲乙》校秦承祖圖,有旁庭臟會等一十九穴。按六百四十九穴有目無名;其角孫景風一十七穴,《三部針經》具存焉,然其圖缺漏。仍有四十九穴,上下倒錯,前后易處,不合本經。所謂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也。至如石門、關元二穴,在帶脈下相去一寸之間,針關元主婦人無子,針石門則終身絕嗣。神庭一穴在于額上,刺之主發狂,灸之則愈癲疾。”唐代醫學雖然進步很快,有了分科細密的官方醫療教育機構。但在中國古代出現較早且一直被沿用的針灸中的針科,在唐代的地位卻并不顯赫。《外臺秘要》作為隋唐三大醫書之一,收錄醫方頗為廣泛,但它卻“不錄針法”,并明確表明不錄針法的原因:“《經》云:針能殺生人,不能起死人。若欲錄之,恐傷性命,今并不錄針經,唯取灸法。”
針療法由于其巨大的危險性,其使用范圍必然受到限制,一些醫生可能會選擇危險系數較小的湯藥、火灸等方法來為病人治療,以減少風險。
雖然存在風險較大,但針刺療法能直接到達病灶,緩解病情,具有其他醫療方法所不具備的優勢,所以還是后繼有人。唐代醫療機構太醫署中就設有針科,置有針師教授學生,而為高宗施針的秦鳴鶴也是一位擅長用針的醫師,“秦鳴鶴以善針醫為侍醫。”可見,針刺療法雖然具有一定的風險,但其流傳和使用從未中斷過。
秦鳴鶴之前,緣于頭部穴位針刺療法巨大的風險,且高宗乃九五之尊,御醫不能不有所顧忌。所以高宗自患病后,一直采用了減負、“餌藥”靜養、避暑療養及溫泉治療等多種方法,而唯獨未見使用刺頭出血療法。但在高宗病情突然危急,眾御醫束手無策的情況下,只得冒險一試,采用秦鳴鶴之針法,為高宗實施刺頭出血。另外,久病成良醫,高宗常年困擾于風疾,必然對治療風疾的一些醫療手段有所了解。所以他才能說出“出血未必不佳”這樣的話。可見刺頭出血確實是治療頭風的一種方法。
從治療效果來看,秦鳴鶴為高宗刺頭出血雖然沒能根治高宗之疾,但其即時療效是顯著的,成功緩解了高宗的失明癥狀。其療效與前面《三國志》中華佗為曹操治療頭風的結果相類,也與前引《千金翼方》中所提到的針刺療法治療頭風的療效相同:即針刺療法可以在頭風劇烈發作時起到緩解病情的作用,但單純針療并不能完全治愈頭風。
有學者以高宗身邊的另一貼身御醫張文仲乃治療風疾的高手,卻不能為高宗施行針刺療法而推斷唐朝醫生不懂針刺腦部穴位,或將張文仲視為武則天黨羽,認為其刻意不為高宗施針。根據史書的記載,張文仲擅長治療風疾乃有目共睹之事。“文仲尤善療風疾。其后則天令文仲集當時名醫共撰療風氣諸方,仍令麟臺監王方慶監其修撰。”則天、中宗以后,張文仲還與李虔縱、韋慈藏并列為諸醫之首。張文仲年輕時即以醫術高明而聞達鄉里,在治療風疾方面尤其出名。然而,在唐代醫學發達,醫學分科細密的情況下,針科早已與醫科、按摩科及咒禁科分開,術業有專攻,張文仲雖是當時公認的治療風疾的名醫,但其所擅長的治療方法卻是湯藥,而非針法或灸法,這一點從史料記載中可以看出,張文仲“奏曰:‘風有一百二十四種,氣有八十種。大抵醫藥雖同,人性各異,庸醫不達藥之行使,冬夏失節,因此殺人。唯腳氣頭風上氣。常須服藥不絕。自余則隨其發動,臨時消息之。但有風氣之人,春末夏初及秋暮,要得通淺,即不困劇。于是撰四時常服及輕重大小諸方十八首表上之。文仲久視年終于尚藥奉御。”據此可見,張文仲引對起風疾的諸多原因及藥性都有深入研究。但歸根結底,他所擅長的還是用湯藥療病。因此,這就是為何在秦鳴鶴之前,張文仲不為高宗實施針刺療法的原因。
張文仲雖然不善施針,但作為一個醫學知識淵博的醫學家,其對針術及針術的基本治療方法應該還是有所了解的,所以當秦鳴鶴提出為高宗刺頭出血的時候,張文仲才沒有表示反對。
綜上所述,秦鳴鶴所采用的醫術當是中醫傳統的針刺療法,而非外來醫術。
五、秦鳴鶴應為中國醫者
以往學者目秦鳴鶴為異域醫者,多是因認為其所采用的醫術是域外醫術;更有人通過古代來華的外國人多以國為姓的傳統來判斷其為大秦人。《舊唐書》云:“蕃人多以部落稱姓,因以為氏。”但實際上,通過上面的論述可知,秦鳴鶴所采用的醫術是中國的傳統醫術。而秦姓也是中國的古老姓氏之一。所以雖然自東漢以來大秦國有遣使來國通好居留不歸者以“秦”姓自稱,但并不能據此判斷秦鳴鶴就一定就出自大秦。從他對中國傳統醫學理論熟悉的程度來看,其為中國人的可能性更大。
另外,秦鳴鶴的身份是侍醫,即侍御醫,其職責是侍奉皇帝并直接負責皇帝的醫療保健,作為皇帝的專職醫生。在唐代的醫療體系中,專門為皇帝服務的醫療機構是尚藥局,置有奉御2人,直長4人,侍御醫4人,主藥12人,藥童30人,司醫4人,醫傳8人,按摩師4人,咒禁師4人,合口脂匠2人。侍御醫主要掌管診候調和,在尚藥局中與尚藥奉御及直長兩級官員同為最重要的專業醫官,也是唐代官品最高的三種醫官。
這種職高位顯的高級醫官,其選任當是極其慎重的,非有高超醫術及良好口碑者不得為之。如高宗身邊的另一位侍御醫張文仲年輕時就已經以高超的醫術而聞名鄉里,所以才能成為皇帝的貼身御醫。“張文仲,洛州洛陽人也。少與鄉人李虔縱、京兆人韋慈藏并以醫術知名。”秦鳴鶴如果真是域外人士,出于政治和安全的考慮,他要進入皇帝的貼身御醫隊伍中當非易事,況且,在唐代的文獻記載中,皇帝病重時可能會請外國醫人診治,但尚未見到有專門任用外國人作為御醫的。
在唐朝的諸多侍御醫中,雖然有些人的籍貫有明確記載,如張文仲為洛陽人,但更多的醫官籍貫則并未見諸于史書,所以秦鳴鶴并不是唐代醫官中唯一一個里籍不詳之人。
因此,結合以上諸要素,筆者判斷秦鳴鶴應為中國醫者。
綜上所述,秦鳴鶴到底是否來自大秦的景教徒,其采用的醫療方法是否外來醫術,之所以會引起眾多學者的無限暢想,除了技術上相似性外,更是唐代對外開放,廣納外來文明的結果。由于唐朝的對外開放,造就了西方文明與印度文明在中原地區的交匯,這一交匯產生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結果。在古代中國、印度與古希臘之間,在各個方面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到底是誰影響了誰,影響有多深,我們可能無法輕易做出結論,但是,能引起我們深入思考的一點是,古代東西方之間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交流的情況可能比我們想象的還要豐富,因此,我們的視野要更廣闊一些,才能收獲更多。
(責任編輯 張衛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