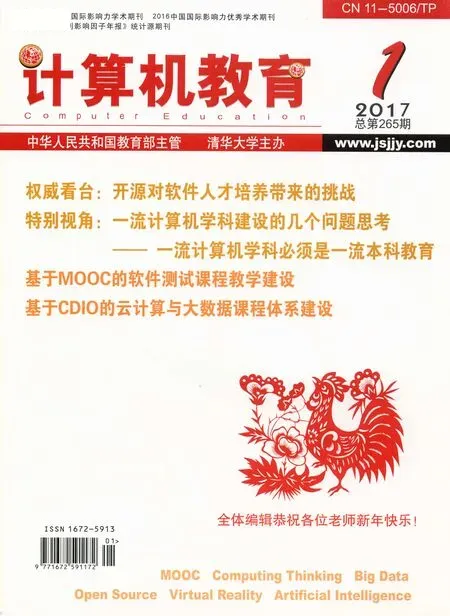基于“SPOC+任務驅動”的翻轉課堂模式研究
張 穎
(華東交通大學 現代教育技術中心, 江西 南昌 330013)
基于“SPOC+任務驅動”的翻轉課堂模式研究
張 穎
(華東交通大學 現代教育技術中心, 江西 南昌 330013)
為實現MOOC與傳統課程的融合,真正實現“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變革,提出構建基于“SPOC+任務驅動”的翻轉課堂模型,介紹該模型的3個核心階段,具體闡述非線性編輯課程翻轉課堂的實踐,最后說明翻轉課堂的實踐結果并提出反思。
SPOC;翻轉課堂;任務驅動;非線性編輯
1 背 景
教育部《教育信息化十年發展規劃(2011—2020年)》中指出:“教育信息化發展要以教育理念創新為先導,以優質教育資源和信息化學習環境建設為基礎,以學習方式和教育模式創新為核心”,提出信息技術應與教育全面“深度融合”的全新理念[1]。
近些年,MOOC在國內高校迅速升溫,然而其不足也逐漸顯現出來,具體表現為:結課率低、投人成本高、學生出勤率低、資源浪費嚴重等。因此,結合信息技術與教育全面“深度融合”的理念,SPOC應運而生,它是一種比MOOC更精致、更小眾的在線開放課程,既融合了大規模在線開放課程的優點,又彌補了傳統課堂教學的不足[2]。
基于“SPOC+任務驅動”的翻轉課堂教學,為學生創造一個“開放、共享、協作”的空間,形成“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模式,增強課程教學的互動性,賦予學生更多的個性化體驗,有助于發展學生的實踐能力和創新思維,有助于培養學生的自主協作學習能力,有助于因材施教。
SPOC(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小規模限制性在線課程) 最早由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Fox教授提出和使用,他認為SPOC 應用于課堂教學,可以增強教師的指導作用,提高學生掌握知識程度以及參與度[3]。其中small和private與MOOC的massive和open對應,Small指學生規模一般在幾十人到幾百人;Private指對學生設置限制性準人條件,達到要求的申請者才能被納人SPOC課程[4]。SPOC是MOOC與傳統教學融合的產物,讓MOOC資源應用于小規模用戶群,其基本形式是在傳統課堂采用MOOC視頻或在線評價等功能輔助課堂教學[5]。因此,SPOC并不否定MOOC,而是要更好地發揮 MOOC的潛能,將優質的MOOC資源應用于學校、課堂等小規模群體[6]45。
“SPOC+任務驅動”翻轉課堂教學模式是以任務驅動為手段,通過翻轉課堂教學模式,將線上SPOC模式與線下課堂學習模式進行融合創新,實現信息技術與教育全面“深度融合”。
2 基于“SPOC+任務驅動”的非線性編輯翻轉教學模型的構建
針對該類課程內容多、學時有限、實踐性強等問題,可以采用基于“SPOC+任務驅動”的翻轉課堂進行探索。通過學習眾多學者的觀點,結合課程目標以及SPOC的特點,筆者將翻轉課堂分為課前認知、課中內化和課后升華3個階段,見圖1。認知階段,主要是學生線上自主學習,在完成課前任務的過程中實現知識的認知;內化階段,主要是教師和學生線下的交流互動、答疑解惑,在完成課堂任務的過程中實現知識的內化;升華階段,主要是學習共同體線上合作學習,在完成課后綜合任務的過程中實現知識的升華。該模式實現了課堂教學與在線學習的融合、個人自主和小組協作的融合、學生間和師生間混合交互。

圖1 基于“SPOC+任務驅動”的翻轉課堂教學模型圖
2.1 知識認知階段
將教學內容進行模塊化組織,在模塊內再按照知識點分類,選取的知識點可分為基礎知識、提高知識、拓展知識[7]。
課前認知階段主要選取“基礎知識和技能”,教師設計好“學生如何認知”,學生學習的流程見圖2。
在該階段,教師是“SPOC+任務驅動翻轉課堂”內容的設計者,教師要根據學生的特點和教學內容,進行微視頻、學習資料、學習任務的設計,組織線上互動。學生是學習任務的執行者及自主學習進度的管理者,根據學習任務單完成相應內容的學習及在線交流互動。
2.2 知識內化階段
通過課前自主學習,學生掌握了基礎知識,在課堂上主要通過與教師的互動以及進一步的任務實踐操作,完成知識的內化。對于“SPOC+任務驅動翻轉課堂”的教學內容,教師首先進行作業講評,對作業中集中存在的問題進行解答和總結,并將講評結果上傳至SPOC學習平臺,學生可以隨時查看和補充;其次,給予學生新的提高任務,讓學生進行實踐操作,進一步強化技能、內化知識。學生學習的流程見圖3。
本階段,教師是“SPOC+任務驅動翻轉課堂”的設計者,也是組織者和主導者,點評學生提交的認知階段作業,并給予新的任務。教師對基礎性知識進行重點答疑,不再花時間具體講解,選取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對提高類知識和技能進行強化練習和難點突破,通過綜合任務對拓展知識進行實踐和創新。
2.3 知識升華階段
由于非線性編輯課程實踐性、藝術性強,利用課程終極任務(學生3~4人一組,自選主題,然后分別進行劇本創作、場景拍攝、后期制作),提高學生的創新實踐能力和協作能力,滿足學生的學習成就感。學生可以利用教師在“SPOC+任務驅動”翻轉課堂提供的拓展知識進行創作,并與小組成員、教師在線討論互動,更深層次地理解課程內容。學生學習的流程見圖4。

圖2 課前自主學習階段流程

圖3 課堂交流內化階段流程

圖4 課后協作學習階段流程
本階段,教師是“SPOC+任務驅動”翻轉課堂的設計者,也是輔助者,教師在學習小組完成綜合任務的過程中有針對性地進行線上指導,學生在教師的幫助下進行小組內和小組間的交流協作,使知識得到升華。導,為學生答疑解難。
3)課后階段。
根據字幕制作的內容,需要學習共同體根據任務要求完成視頻的制作輸出。教師提供大量視頻片段,小組首先根據這些素材選定主題,根據主題選取合適的素材片段。要求學生在開頭添加一個整屏式字幕,文字內容自定;在結尾添加一個向上滾屏字幕,文字內容為制作人員名單以及制作單位;在中間適當位置添加字幕及特效,最終輸出視頻。在此期間,教師可以通過各種社交工具為學生提供在線支持。

表1 字幕教學內容
3 翻轉課堂實踐及反思
3.1 課堂實踐
根據上述流程,我們在非線性編輯課程中開展基于“SPOC+任務驅動”的翻轉課堂教學。下文以片段剪輯教學內容為例,學習目標是掌握視頻剪輯、人出點的設置及片段的組接。
1)課前階段。
在課前一周教師將下次課的學習安排、學習材料、學習任務等發布至SPOC平臺,學生登錄平臺,在課程公告模塊查看教學安排和任務安排,自主學習階段主要安排基礎知識的學習,見表1。在學習資源模塊,根據學習任務找到相應的視頻和學習資料進行自學;自學完成后,將作業上傳至作業模塊;師生間、學生間可以通過論壇、微信等社交工具進行線上互動。
2)課中階段。
通過課前自主學習,學生已經掌握了基礎知識。課堂上,教師對課前作業進行針對性講評,主要就作業中集中存在的重難點、易錯問題、提高問題進行講解,并將講評結果發布到SPOC平臺;隨后教師提出新的任務,學生進行現場操作實踐,在此過程中教師及時查看學生的完成情況,并提供各種學習支持,給予學生個性化指
3.2 教學效果
教學評估數據主要來源于學生訪談、課堂觀察、問卷調查及期末學生作品的分析。問卷調查共發放問卷48份,有效問卷46份,目的在于了解學生對“SPOC+任務驅動翻轉課堂”模式的看法以及對課程改革的意見。
1)翻轉課堂的認知調查。
訪談了解到在開展教學活動之前,不了解翻轉課堂的學生占93.47%,但他們愿意嘗試這種新型的教學模式。
2)與傳統課堂對比調查。
對比傳統課堂,問卷進行了對翻轉課堂態度、翻轉課堂在提升自學能力及在提高合作學習效果等方面的調查,見圖5、圖6。另外,還針對翻轉課堂增進師生交流、促進傳統教學改革等方面進行調查。結果顯示,學生對“SPOC+任務驅動”翻轉課堂的滿意度達74%。

圖5 對翻轉課堂的態度

圖6 自學能力和合作學習效果
3)課前自主學習階段情況調查。
圖7、圖8分別為自主學習階段時間投人和參與度的調查結果,結果顯示學生的學習時間主要集中在半小時和一小時;仍有11%的學生從不按照教師的要求進行課前任務學習。另外,對于課前學習資源喜好度方面,28%的學生認為需要進一步豐富學習資源,37%的學生認為學習任務有些難度,部分難點知識需要教師課堂講解,大部分學生認為通過課前SPOC學習可以提高學習效率和學習興趣。
4)課堂學習階段情況調查。
圖9是教師課堂為學生答疑解惑和學生任務完成滿意度的調查結果。87%的學生認為任務完成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得到了較滿意的答案,僅有19%的學生對自己課堂任務完成情況不滿意。

圖7 自主學習時間投入情況

圖8 自主學習參與度

圖9 教師課堂解疑和任務完成滿意度
5)學生視頻作品分析。
影視作品能夠客觀真實地反映大學生運用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8]。調查結果顯示,能夠積極參與并按時完成相應任務的學生,視頻作品大多主題鮮明、鏡頭規范、剪輯精確、畫面唯美;參與較少和不參與的,視頻作品質量和水平很差。可以說,“SPOC+任務驅動”翻轉課堂能夠有效培養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和創新能力。
3.3 結論與反思
通過教學效果的評估,我們得到如下結論:第一,提升了學生對翻轉課堂的認知度。學生通過親身體驗,了解并適應了翻轉課堂模式,利于翻轉課堂在其他課程的推廣。第二,提高了學生的非線性編輯技能。翻轉課堂改變了以往枯燥的“填鴨式”教學模式,激發了學生的參與熱情。另外,學生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可以及時得到教師的指導和幫助,有助于增強學生的學習自信心,提高學習效率。第三,課堂學習滿意度較高。通過課前自學,學生已經對所學知識有了初步的認識,在課堂中學習目標更加明確,學生帶著問題聽講,教師有針對性地為學生解惑,改變以往被動的“傳遞—接受”教學模式,更有利于課堂任務的完成。第四,翻轉課堂比傳統課堂更受學生歡迎。增加了課前自學階段,延長了課堂師生的互動時間,學生在教師的指導下,有目的地完成任務。
同時,該模式也存在不足:參與度方面,少數學生沒有參與自學,今后將重點關注這部分學生,并積極引導;學習資源方面,學生希望獲得更豐富的資源,比如增加文本類型、增加針對課后任務的拓展資源;任務難度方面,大部分學生可以完成基礎任務,提高任務有些難度,需要教師的幫助和講解;學習監控方面,教師無法有效地監控、記錄、分析學生課前和課后的學習行為[9]。
針對以上不足,今后要從4個方面改進:
第一,進一步優化SPOC平臺的功能,增加學習行為記錄功能和消息提醒功能。比如教師可以隨時查看每個學生的學習記錄,便于教師及時了解學生的學習動態,對遲遲沒有參與學習的學生進行干預,通過消息中心給學生發送學習提醒。
第二,優化學習資源,提高資源的豐富性和針對性。除了各知識點的視頻、文檔,增加提高知識和拓展知識的視頻資料和相關文檔。
第三,進一步改進課程評價機制。合理的評價機制有助于調動學生的主動性。采用面向過程和面向結果的評價機制對整個課程周期進行全面的評價。在本課程的考核方案中,總成績分為平時成績(60%)和期末作品成績(40%),其中平時成績包括課前、課中任務的成績及課堂參與度成績。
第四,把握好翻轉課堂的度,爭取讓每個學生都積極參與。若過多采用翻轉課堂,勢必加重學生的學習壓力,可能導致學習疲勞。對于一門課程,采用翻轉課堂的次數、如何科學設計教學環節,需要教師重點研究[10]。
4 結 語
基于“SPOC+任務驅動”翻轉課堂模式,實現了MOOC與傳統課程的融合,實現了線上和線下的融合,真正實現了“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變革,受到了學生的歡迎。該模式可以在SPOC軟件技能類的實踐課程中推廣,但應把握好翻轉的度,如何把握好度需要一線教師進一步研究和探索。
[1] 教育部.教育信息化十年發展規劃(2011—2020年)[EB/OL]. [2016-07-13].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 moe/s5892/201203/133322.htm.
[2] 蘇小紅, 趙玲玲, 葉麟, 等. 基于MOOC+SPOC的混合式教學的探索與實踐[J]. 中國大學教學, 2015(7): 60-65.
[3] Armando F. From MOOCs to SPOCs[J].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2013(12): 38-40.
[4] 康葉欽. 在線教育的 “后MOOC時代” ——SPOC解析[J]. 清華大學教育研究, 2014(1): 86-93.
[5] 徐葳,賈永政.從MOOC到SPOC——基于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清華大學MOOC實踐的學術對話[J].現代遠程教育研究, 2014(4): 13-18.
[6] 李海龍, 李新磊.“后MOOC”時代基于分布翻轉的SPOC體驗式學習探討[J]. 電化教育研究,2015(11): 44-50.
[7] 林曉凡, 胡欽太, 鄧彩玲. 基于SPOC的創新能力培養模式研究[J]. 電化教育研究, 2015(10):46-51.
[8] 呂婷婷, 王娜. 基于SPOC+數字化教學資源平臺的翻轉課堂教學模式研究——以大學英語為例[J]. 中國電化教育, 2016(5): 85-90.
[9] 薛云, 鄭麗. 基于SPOC翻轉課堂教學模式的探索與反思[J]. 中國電化教育, 2016(5): 132-137.
[10] 楊方琦. 項目教學法在“非線性編輯”課程實驗教學中的應用[J]. 實驗室研究與探索, 2012(10): 380-382.
(編輯:孫怡銘)
1672-5913(2017)01-0131-05
G642
華東交通大學校立科研基金項目“任務驅動法在翻轉課堂中的創新實踐研究” (15QT01)。
張穎,女,助理工程師,研究方向為計算機應用技術,83654956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