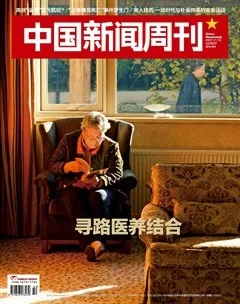數碼文化并非洪水猛獸

徐賁
許多人對互聯網文化的崛起充滿了焦慮:谷歌正在腐蝕我們的記憶力,把我們變得淺薄和愚蠢;互聯網代表了粗鄙者的崛起、剽竊者的勝利和高雅文化的終結。
當中世紀的手稿文化向早期現代的印刷文化轉化時,也出現過類似的焦慮。事實上,印刷文化的形成離不開手稿文化已經取得的進展和成就,印刷書籍吸收和改變了手稿的一些形式通例。印刷文化與手稿文化之間是一種一邊借助、一邊形成自己特色的變化過程。
開始,印刷的文本與手抄文本頗為相似。例如,印刷文本要求讀者在閱讀過程中提供輔助。書籍是沒有頁碼的,需要讀者自己添加頁碼,還需要他們在應該大寫的地方涂上紅色,在文句停留處添加標點符號等。后來書籍印刷者才承擔了越來越多的編輯責任。阿爾杜斯·皮烏斯·馬努提烏斯是文藝復興時期威尼斯著名的人文主義學者和印刷商。1502年,他出版奧維德(Ovid)作品時,還在要求讀者自己在書頁上標上頁碼。但是,很快,他就在書里印上頁碼了。
馬努提烏斯的印刷技藝是與時俱進的。中世紀手抄書籍的頁邊經常附有注釋(中國的古書也是正文與注釋或注疏混雜一起的),他改變了這種頁面樣式,采用了將注釋印在書頁底部的辦法。于是,正文與注釋的關系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注釋與正文分離開來,把頁面的主要部分還給正文。這受到當時新教改革作者們的歡迎,因為他們要求回歸《圣經》原意,要將中世紀經院評注的重要性降格,印刷書籍的新頁面處理正好符合這一需要。
今天,數碼傳媒帶來的寫作、閱讀和交流新特征,也應放到更大的社會文化價值變化中去理解。例如,作者與讀者的關系有了變化,作者不再是居高臨下向讀者灌輸權威知識的一方,也是讀者們可以詰問、補充、糾正的平等對話者一方。知識的主體不再是作者,而且也是讀者。
這標志著社會和文化價值從“他控”向“自控”、從“服從”向“自律”的轉變。上司指示、政治領導、道德教誨,這些都隨著知識話語向普通人轉移而發生了變化。
然而,數碼文化的每種形式都可以看到印刷文化的某種相應形式。維基百科讓我們聯想到百科全書。百科全書提供由專家構建的明確知識;維基百科提供由讀者構建、評議并可再行編輯的知識。博客讓我們聯想到日記。日記是在時間中串成的個人私密思考;博客發出的是個人的聲音,但并不私密,而且歡迎他人的回應。電子游戲令人聯想到小說和戲劇。小說或戲劇人物的經歷讓我們感同身受,在電子游戲里我們自己成了影響故事結果的主角。凡此種種,文化行為和行動者在變化,在擴展,與其說是取代,不如說是變換,新的并沒有消滅舊的,而是新舊并存,并因此形成新的復合型態。
大學里,教授和學生的關系也在發生變化。雖然教授還站在講臺上授課,但也已經出現了以學生為主體的課堂小型討論班。雖然滿堂灌的教學沒有絕跡,但也有了更多的師生互動。雖然教科書仍然是課程的主體內容,但“批判性思維”正在悄悄地進入教育課程。雖然專業課仍被視為核心課程,但“通識教育”和“人文教育”已經不再是一個陌生的教育理念。雖然絕大部分學生仍在封閉的課堂里求學,但互聯網的線上開放課程或視頻公開課正在吸引學生群體中那些更好學、更勤思的部分。雖然每個教室里還有黑板和粉筆,但電視設備已經廣泛地在教學中運用。
大學的知識生產和傳播正處在一個轉型的時代,既是新舊交替,也是新舊交融,也許在這個交替和交融中會形成一個新的知識秩序。我們對它有所期待,但我們并不能充分想象那將是一個怎樣的秩序,因為秩序是充滿變數的歷史副產品,不是任何人可以憑想象設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