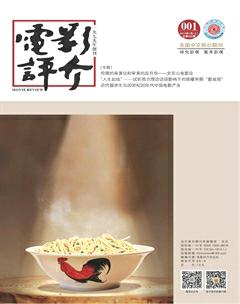文化探秘影片的主題探析
賀莉
美國導演朗·霍華德十分熱衷于將暢銷作家丹·布朗筆下的有關羅伯特·蘭登教授的懸疑故事搬上銀幕,從2006年的《達·芬奇密碼》到2009年的《天使與魔鬼》再到最新上映的《但丁密碼》,羅伯特教授系列影片在為觀眾展現符號與破譯魅力的同時,也掀起了大眾對文藝復興時期藝術作品的再度關注。如果說《達·芬奇密碼》著力表現羅伯特教授利用專業知識解開宗教之謎的特技,那么,在影片《但丁密碼》中,羅伯特教授擔負著更為艱巨的使命——用他的符號學知識幫助整個人類得以繼續繁衍。本文重點闡釋這兩部影片在主題意蘊表達方面的共通性。
一、 主體性精神的張揚
自文藝復興時期開始,人的主體性精神就成為西方思想家孜孜以求的目標,但人們對于自身主體性的自覺意識卻經歷了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作為西方哲學重要的研究對象,人的主體性精神的形成與凸顯,經歷了一個從原始社會主客混沌不分到古希臘哲學試圖通過本體論的建構初步區分人與周圍世界,再到近代哲學在認識的主客體關系中突出主體性以及德國古典哲學把主體性理論發揮到極致的過程。
影片《達·芬奇密碼》中,一條主要的線索即為白化病教徒塞拉斯為獲取圣杯的秘密,不惜先后殺死郇山隱修會的盟主及三位大長老,而男女主人公羅伯特·蘭登與索菲·奈芙正是在找尋殺人犯的過程中開始了他們的破譯之旅的。所謂的圣杯的秘密,其實是指耶穌之妻抹大拉的馬利亞的靈柩所在地,郇山隱修會的幾位長老誓死保護圣杯不受迫害的背后卻隱藏著有關信仰與權力的重大問題。自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后的幾百年來,耶穌的神性與人性之爭成為基督教內不同派系的重要分歧點,現代教會推崇耶穌的神性至上,并宣稱只有透過耶穌基督才能獲得救贖,其實質則為妄圖利用宗教實現對民眾的統治與控制;而郇山隱修會則主張耶穌的人性大于神性,他們認為透過男女結合能夠體驗到神圣,并相信女人是幫助他們通往天國的神秘力量。由此,郇山隱修會對耶穌人性的推崇以及對抹大拉的馬利亞之身的保護引來其他派系的不滿與暗殺。在西方,宗教信仰的傳統根深蒂固,成為每個人的精神之魂,但是在戰亂的年代,宗教往往被邪惡勢力所利用,為爭取權力的集中,他們濫殺無辜,使宗教蒙上一層血腥的外衣。郇山隱修會在防止宗教權力壟斷統治的同時,以張揚人的主體性精神的姿態抵制宗教神學對人的貶斥,極力推崇耶穌的人性,推崇耶穌作為凡人,其精神是可以隨著血脈無限延續的,他們誓死保護圣杯的秘密,更誓死保護耶穌的每一個后代。
影片《但丁密碼》中,巨大陰謀的制造者貝特朗·佐布里斯特是個有著狂熱妄想癥的天才遺傳學家,他把地球上的環境、生態等問題的產生及惡化,全部歸于人口過剩問題,并研制了一種能夠殺死全球一半人口的超級病毒,待到時機成熟便開始實施自己的“拯救計劃”。盡管貝特朗將人類自身看作是《神曲》所描繪的地獄的創造者,他企圖毀滅的也是人類自身,但貝特朗的整個計劃無不滲透著人的主體性精神的張揚,他從當下的社會問題與環境問題出發,以維護人類自身的生存與發展為目的,在透析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時,他并不強調人類對大自然的征服,而是在人與自然的相互作用中把握人類的整體利益,表現出頗具理性的主體性精神。另一方面,貝特朗秉持古希臘以來對人的主導地位的強調——“人是萬物的尺度,是存在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他堅信自己理論的至高性與計劃的完美無缺,他堅信高智商群體有能力解決地球上的各種難題,他肯定人的地位與力量,他在張揚主體性精神的同時,把人的主導作用力上升到不切實際的對整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控制與變更的高度。
二、 女性崇拜的復蘇
人類在從母系社會向父系社會轉變的過程中,女性逐漸喪失了話語權,其后數千年的歷史一直是以父權為中心的男尊女卑的社會,性別歧視成為社會文化的劣性產物。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女性在獲取一定的經濟地位的同時,要求改變長久以來自身的從屬地位,要求重新獲得話語權及以平等的姿態與男性共同參與社會競爭。在此背景下,愈來愈多的藝術作品標榜女性崇拜的復蘇的主題,它們以激進的筆法凸顯女性的反叛精神。
影片《達·芬奇密碼》主要圍繞尋找圣杯的所在地而展開,但從羅伯特與雷·提彬兩人的講述中,導演試圖通過圣杯秘密的解開暗示女性神圣地位的回歸,而影片中郇山隱修會對抹大拉的馬利亞的忠誠與崇拜則昭示著女性尊嚴與地位的提升。此外,影片著重塑造了索菲·奈芙這樣一個集美貌與智慧于一身的現代女性形象。年幼的索菲·奈芙在一次車禍中失去了雙親與哥哥,祖父雅克·索尼埃成為她唯一的親人,在祖父的悉心教導下,索菲對密碼破譯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對未知的事情則有著強烈的探索意識,她思想獨立、個性張揚,在與羅伯特教授逃亡的路途中,總能表現出個人對待事物的獨到見解與判斷。如果沒有索菲,羅伯特不可能進入蘇黎世存托銀行拿到藏密筒;如果沒有蘇菲,羅伯特便不可能最終破譯拱心石的密碼,完好無損地取出標有圣杯所在地的地圖。當雷·提彬貪婪地追捧索菲作為最后一個圣杯的守護者,她可以阻止一切罪行的發生,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影片對獨立女性的推崇與召喚。
影片《但丁密碼》中,著重塑造了正反兩個女性形象,一個是年輕貌美的女醫生西恩娜·布魯克斯,一個是世界衛生組織的高管伊麗莎白·辛斯基。西恩娜·布魯克斯以熱心善良的女醫生形象出場,她不畏暴力與血腥,冒險幫助羅伯特教授逃脫于多種不明勢力的追殺,在表現出自身對破譯有著極大的興趣之后,西恩娜更是深得羅伯特教授的信任,兩人共同踏上“Seek and find(尋找與發現)”的探秘之路。然而,就在兩人一邊逃命一邊解密的過程中,西恩娜在關鍵時刻終是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作為人類毀滅者貝特朗·佐布里斯特的摯愛,她在貝特朗死后,需要利用羅伯特教授的專業知識獲取有關病毒隱藏地的信息,與其他成員一起完成貝特朗的遺愿,實現“拯救人類”的偉大計劃。另一位“女強人”伊麗莎白·辛斯基則給觀眾留下優雅穩重的深刻印象。作為羅伯特教授多年的好友,她在危急時刻選擇信任與幫助羅伯特。面對陰謀家哈里·西姆斯的威脅,她以大局為重,與西姆斯聯手展開對西恩娜計劃的破壞;面對西恩娜等人瘋狂的“殺戮”行為,伊麗莎白不顧個人性命的安危,在水中與邪惡勢力殊死搏斗。最終,在伊麗莎白的努力下,封鎖病毒的隔離箱沒有被打開,貝特朗·佐布里斯特的“完美計劃”沒能得逞,人類的生命得以繼續延續下去。無論是毀滅計劃的終極實施者,還是病毒隔離箱的最后守護者,影片《但丁密碼》安排由兩位女性擔此重任,表現出一種脫離于原始的生殖崇拜的,對現代女性智慧與力量無限推崇與肯定的新女性主義觀點。
三、 現代危機意識的凸顯
在西方影視劇作中,危機意識的表達成為一個古老且重要的主題呈現。人類作為地球上最高等的智慧生物,有著極強的求索自然奧秘與解釋人類生存真相的本能,但是對死亡的未知,以及由此引發的對死亡的恐懼,催生著人們潛意識中的生存危機的表達。基督教中存在關于末世論的說法,一定程度上構成西方人危機意識的文化傳統,然而,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現代社會的多重災難加重了人們有關危機意識的思考,核戰爭的威脅、恐怖主義的泛濫、生態環境的惡化、科技對傳統倫理秩序的顛覆等等,都讓人們深感自身在災難面前的弱小與無奈。影片《達·芬奇密碼》與《但丁密碼》同樣傳達出一種無法消解的危機意識,加強了影片的悲劇意蘊。
影片《達·芬奇密碼》具有濃厚的宗教色彩,在劇情的推進中,影片為觀眾呈現了不同教派的信仰主張。例如,郇山隱修會負責保護羅馬教廷在世上的權力來源,他們將古代的女性象征符號視為圣杯的標志,相信人們透過女性會通往天國;而現代教會則認為女人是阻礙人們獲得救贖的邪惡力量,他們將擁有獨立思想的女性視為獲取統治權力的阻礙者,視為威脅人類生存的女巫。在歐洲長達三個世紀的捕獲女巫的行動中,數以萬計甚至百萬計的女性被殘忍殺害……影片《達·芬奇密碼》并非單純地給觀眾普及一段宗教歷史,也無意深入探索何種信仰主張更為科學更為理性,導演朗·霍華德在羅伯特教授與雷·提彬的爭辯中,表達出信仰之爭對于人類生命殘害的荒謬,表達出由信仰危機引發的關于人類生存危機的深刻思考:對于擁有宗教信仰的人來說,個人的精神世界與信仰密切相關,信仰構成他們終身堅定的生存理念,他們深信只有在信仰中生命的價值和意義才能得以實現,然而,現實中信仰主張的狹隘性讓人們逐漸意識到信仰同樣可以作為統治的工具甚至是殺人的武器,人們不禁陷入難以排解的精神危機之中。
影片《但丁密碼》中,億萬富翁貝特朗·佐布里斯特以演講的方式,在網絡上宣傳自己有關人口過剩問題的看法,他以近50年來人口增長速度為例,深度剖析之后百年人口的增長率以及計劃生育控制手段的無效性,他以近乎洗腦的方式堅定自己對于毀滅人類的邪惡計劃,以近似仇恨的態度“誠摯”地邀請每個人參與到爭取自身生存權利的斗爭中,貝特朗宣稱“人類正是惡疾,地獄才是解藥”,他成功地利用了西恩娜對他的迷戀以及其他組織成員對他的無限迷狂,將個人對于人口過剩問題的局限理解,對于整個人類生存的危機意識擴散到全球,他認定只有通過毀滅1/2的人口,生態環境才會日漸得到改善,生態平衡才能繼續得以維持。盡管如貝特朗的極端做法只會出現在電影當中,但貝特朗幽深的危機意識卻不得不引起人們的重視,導演旨在利用反例加以警醒人們對于人類整體發展前景的關注與思考。
結語
相比10年前的《達·芬奇密碼》,導演朗·霍華德在此次執導影片《但丁密碼》時,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整個人類命運的挽救過程,其懸疑程度及故事進展節奏都稍有減弱,“但丁”的作用亦旨在引出《神曲》中有關地獄的建構與描述,并非如“達·芬奇”能夠提供諸多的密碼線索,構成故事主要的發展脈絡。盡管在影片《天使與魔鬼》上映的時候,就有評論指責朗·霍華德執導懸疑驚悚片的有限功力,認為他的改編不過是對過往成功的一再復刻,但通過對《達·芬奇密碼》與《但丁密碼》兩部影片的比較分析,依然能夠體會出朗·霍華德于現代意識和獨到思考中對于文化探秘類影片的深入探索及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