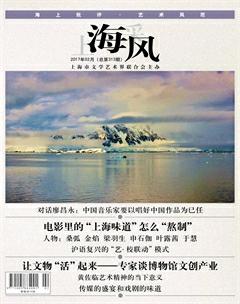走向遺忘的觀看
張閎
各位好!我在這里要做一個“反動”的發言,是和會議主題(注:中山大學舉行的“視覺,觀看與記憶研討會”)“反向而動”的發言。會議主題講“記憶”,我卻要講“遺忘”。為了使我所講的保持內容與形式相一致,我放棄了制作一份可供觀看的PPT的企圖。
關于視覺,關于觀看,我們能說什么呢?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問題。早上開幕式的時候楊小彥教授(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用四幅漫畫表達了會議的宗旨,說到學術會議要討論問題,但不能被問題壓倒。可是,我常常被問題所壓倒,許多問題對我來說依然是個問題。我接下來要跟諸位談論的,就是我的一些困惑。
首先,所謂“觀看”,在我看來并不是無條件成為視覺問題,乃是在轉化為對“圖像”的觀看的時候,它才是視覺問題。只有在觀看事物本身的不在場的時刻,而且事物以圖像的形式來呈現的時刻,我們再去觀看它的時候,才產生了所謂“視覺問題”。如此看來,實際上視覺問題是一個關于事物的缺席,關于我們對于事物有可能產生的“遺忘”的產物。所以,觀看圖像是克服遺忘的技術。
接下來我要講一個事例。我有一位愛好拍照的同事,每次外出,隨身總要帶上相機,把所有能拍下來的景點和場景,都拍下來。我們將他的拍照行為稱作“地毯式拍攝”。有一回,我們一同去歐洲旅游,這位朋友很高興,早早地做了許多的功課,包括準備相機。他準備了兩架相機:一架數碼傻瓜機,一架配備多個鏡頭的單反相機,還特地多買了幾塊備用電池板和大容量的存儲卡,以及一臺用來儲存照片和視頻文件的筆記本電腦。他準備“好好拍一下”!在歐洲,這位朋友大顯身手,除了吃飯、睡覺的時間之外,他幾乎都在拍照。坐在大巴上隔著玻璃窗拍,下車后對著景點拍,自拍和與同伴互拍。導游指點的景點拍,導游沒有指點的地方,他覺得好的,也拍。短短十來天里,“地毯式拍攝”戰果赫赫,共計有好幾千張照片。在回國后的一個多月時間里,他幾乎閉門不出,在家里整理照片,分門別類,給照片命名,用電腦軟件修飾……他讓我看他的照片,而他自己卻不時地發出驚嘆,仿佛是第一次見到照片中的場景。事實上,他已經不記得自己究竟到過何處,也不記得照片中的場景是在哪里、在怎樣一種情形下拍攝的。他經常打電話給我,詢問他照片中某一建筑是哪個地方的什么建筑。他的整個旅游過程都在拍照,根本就沒有留心觀看所到之處的情形。只是等到他整理照片的時候,旅游才真正開始。
旅游讓他收獲了一堆照片,通過這些照片,象征性地占有了照片中的景物。但在他靠不住的記憶里,這些景物與其他任何陌生的照片一樣,僅僅是一種“象征”的存在。在具體的旅游過程中,他的真身似乎并不在場,只有照相機鏡頭代替他,而他僅僅是相機的支架而已。而在照片中旅游,似乎比他的真身在現實中旅游,來得更為真實。地毯式拍照一路拍過去以后,和他記憶相關的非常稀薄。作為記憶喚醒的圖片反倒是關于遺忘的圖式,他抱怨自己記性不好,又說,幸好拍了這些照片,不然,這歐洲算是白跑一趟。其實是自己的眼睛根本沒有看。這個攝影的例子很有趣地揭示了觀看和記憶遺忘之間的關系。我們為了記憶而拍攝,可是,拍照并不能夠幫助我們記憶,相反,它讓我們陷于關于照片的記憶而非事物的記憶。照片成為我們的觀看與事物之間的隔膜和障礙。我們的觀看和拍攝,與其說是關于“記憶”的,不如說是關于“遺忘”的。
觀看從以下幾種途徑走向遺忘:
第一種:“誘導性遺忘”。圖像作為記憶,毋寧說是一種誘導性記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謂“工農兵”圖像。文革期間的“工農兵”圖像體系乃是關于政治性記憶的建構,是對于“工農兵”的選擇性的記憶。這種抽象的關于“工農兵”的記憶,實際上是不存在的,或者說,是以壓抑具體的“工農兵”記憶為條件的,有時甚至以消滅的私人記憶為前提。而且往往需要通過暴力的手段來實現。上午有發言者提到對于照相館的改造、管理,乃至以后對私人性照片的焚毀,這些行動表明,政治權力在壟斷記憶權。圖片記錄并非必然地指向每個具體個人的記憶。政治權力介入,導致一種選擇性記憶和對具體私人記憶的消除,進而構成歷史“遺忘”的基礎。文革后我們看到仍有大量的私人照片重新浮現水面,這里呈現出來的是一種關于記憶權的“壟斷”與“反壟斷”的爭奪。
第二種:“記憶短路”。正如普魯斯特在《追憶似水年華》中所呈現出來的那樣,記憶會有各種各樣的形態,時間延伸、放大或壓縮,但還有一種“記憶短路”現象。在當代藝術中,紅色波普藝術的初衷是出于對政治記憶提醒,作為克服遺忘的手段,但實際上大量的當代紅色波普藝術卻更像是一種遺忘的技術。如王廣義的“大字報系列”把文革的宣傳畫、墻報和當下文化結合在一起,似乎提示著當下的文化和文革的政治之間的關聯。但這一點簡單的關聯,在我看來是一種“記憶短路”。在完成了相似性的簡單連接之后,繪畫的意義生成過程就結束了,所表現的事物以及要指向的意義就歸于終結。這樣的圖像里面包含的語境和政治性的創傷經驗就很快被耗散,并很容易迅速進入到視覺消費領域,進而被遺忘。關于政治記憶、歷史記憶、在圖像表達方面應該有更豐富、更多的手段。
第三種:“記憶固化”。記憶沒有彈性了。晉永權先生在發言中提到的“標準照”問題。在我看來,“標準像”就是對照片的謀殺。“標準照”表面上看似乎是對活著的人物的記錄,但它卻是死亡的標志。在所謂“標準照”中,時間和空間的凝固不動。人的“標準照”常常用來做遺像,因為在那一刻,生命結束了。所以說,“標準照”與其說是指向記憶的,不如說是基于對死者的緬懷。通過“標準照”,喚起一種追悼和緬懷的記憶,但是一體化的和固化的“標準照”背后,更多是凝固的記憶,除非放在特殊領域里面,否則沒有意義。藝術家張曉剛曾對此做了反諷性處理,他用文革時期拍“標準照”的方式,作為對文革期間家庭記憶的反諷。以記憶的褪色、標準化形式下的漏洞和補丁的圖像,來作為抵御和批判“視覺固化”“記憶固話”的手段,同時也是對“遺忘”的批判。
第四種:“圖像膨脹”。在今天,這種現象特別引人注目。如前面所說的,我的同事從歐洲回來拍了數以千計的照片,還從其他同事里面要了很多,他整理完了以后,我想他也再不會去看它們了。這是記憶死亡的另一種表征。現在每個人都有手機,機械的反應在一瞬間的抓拍捕捉光影的投射,建立視覺與記憶之間的最淺表的關聯。大量的膨脹使我們視覺和記憶回到最原始的狀態,記憶如同原始生物一般,依靠機械的反應,依靠圖像無限的自我復制和自我增殖,但是留在記憶淺表,而且被大量覆蓋。這樣淺表的記憶對一個光影刺激機械反應的記憶,實際上是視覺歷史記憶關聯的一種松弛甚至是剝落。在藝術史上,安迪·沃霍爾曾經通過對這種膨脹和自我增殖的圖像的戲仿,表達了對這一現象的反思批判。在今天這種視覺影象工具特別發達的情況下,圖像膨脹如同無法遏止的視覺腫瘤,嚴重侵蝕著正常的視覺記憶。重新思考視覺藝術以及記憶的技術如何面對當下大量的事物膨脹和遺忘的現實生活,這是一個我們必須直面的問題。
由于時間的關系,我就講到這里。很抱歉,我的這一場“反動的”發言,不過淺嘗輒止,又未能滿足諸位的觀看欲,徒然占用了諸位的時間。請原諒!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