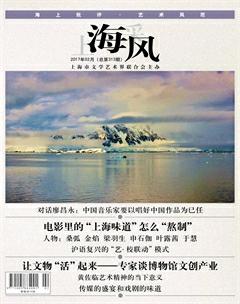中國(guó)網(wǎng)絡(luò)小說(shuō)首次進(jìn)歐美百姓日常生活
北京日?qǐng)?bào)刊文說(shuō),知名中國(guó)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英譯站W(wǎng)uxiaworld(武俠世界)近日對(duì)外宣布,已與閱文集團(tuán)旗下的起點(diǎn)中文網(wǎng)簽下翻譯和電子出版合作協(xié)議,武俠世界將擁有20部作品的授權(quán)。事實(shí)上,中國(guó)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已在多個(gè)海外翻譯網(wǎng)站走紅,老外呼天喊地猛追網(wǎng)文一點(diǎn)兒都不稀罕了。對(duì)業(yè)內(nèi)人士來(lái)說(shuō),他們更樂(lè)見(jiàn)的是,中國(guó)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已介入到老外閱讀生活中,這意味著龐大的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生態(tài)輸出已逐漸成為現(xiàn)實(shí)。Wuxiaworld(武俠世界)、Gravity Tales等以翻譯中國(guó)當(dāng)代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為主營(yíng)內(nèi)容的網(wǎng)站上,隨處可見(jiàn)眾多外國(guó)讀者“追更”仙俠、玄幻、言情等小說(shuō)。中國(guó)網(wǎng)友還貼出了老外喜愛(ài)的十大作品——《逆天邪神》《妖神記》《我欲封天》《莽荒紀(jì)》《真武世界》《召喚萬(wàn)歲》《三界獨(dú)尊》《巫界術(shù)士》《修羅武神》《天珠變》。而這些小說(shuō)也被稱(chēng)作“燃文”,多為平凡無(wú)奇的男主角一路打怪、外加各路神仙師傅輔助、成了開(kāi)天辟地第一人并抱得美人歸的故事。
“追更”是這些網(wǎng)站的一大亮點(diǎn)。一家網(wǎng)站留言區(qū)中,讀者都在翹首期盼《我欲封天》第1138章,一邊留言催著更新,一邊表示悔恨:“為什么我以前沒(méi)學(xué)中文?現(xiàn)在還來(lái)得及嗎?”很多時(shí)候,更文速度肯定滿(mǎn)足不了讀者的胃口,于是論壇時(shí)常有人發(fā)帖咨詢(xún):“如果我想贊助一位志愿者翻譯完一整本書(shū),大概要多少錢(qián)?”還有人追看了一部還不過(guò)癮,趕緊發(fā)問(wèn):“我想說(shuō)這是我看過(guò)的最棒的小說(shuō),你們還知道類(lèi)似《逆天邪神》這樣的小說(shuō)嗎?”很多人為了更好地理解小說(shuō),還苦哈哈地自發(fā)學(xué)起了中文。
半年前,北京大學(xué)中文系創(chuàng)意寫(xiě)作研二學(xué)生吉云飛和他的同學(xué),通過(guò)國(guó)內(nèi)貼吧、論壇的一些零星線(xiàn)索,關(guān)注到海外網(wǎng)站自發(fā)翻譯網(wǎng)文的現(xiàn)象。第一次進(jìn)入到武俠世界網(wǎng)站,他驚訝地發(fā)現(xiàn),網(wǎng)絡(luò)作家“我吃西紅柿”的長(zhǎng)篇作品《盤(pán)龍》竟全部翻譯完畢,不僅故事大致上沒(méi)有改變,語(yǔ)言甚至比原來(lái)還要講究。而此時(shí),該網(wǎng)站已建立一年多了。吉云飛和這家網(wǎng)站的創(chuàng)始人賴(lài)靜平(RWX)通過(guò)網(wǎng)絡(luò)相識(shí),后者是一位華裔,3歲時(shí)隨父母到美國(guó),今年30歲,做過(guò)七八年的外交官。因?yàn)閷?duì)中國(guó)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的喜愛(ài),賴(lài)靜平辭掉工作,一頭扎進(jìn)了網(wǎng)文翻譯世界里。賴(lài)靜平說(shuō),最初自己只會(huì)簡(jiǎn)單中文,后來(lái)通過(guò)努力學(xué)習(xí),曾經(jīng)花六七年時(shí)間把金庸、古龍幾乎所有的小說(shuō)都翻譯完了,但遺憾的是讀者并不多。直到某天受一位越南華僑的引領(lǐng),走進(jìn)中國(guó)網(wǎng)文世界,并決定將網(wǎng)絡(luò)作家“我吃西紅柿”的《盤(pán)龍》翻譯成英文,貼在網(wǎng)上供大家閱讀。他漸漸發(fā)現(xiàn)一天點(diǎn)擊量也有十幾萬(wàn)次了,于是決定自己弄個(gè)網(wǎng)站,他翻譯的中國(guó)網(wǎng)文風(fēng)生水起,很多人后來(lái)不惜捐錢(qián)也要“追更”。當(dāng)分析中國(guó)網(wǎng)文為何能征服老外時(shí),賴(lài)靜平說(shuō),最重要的是網(wǎng)文給讀者帶來(lái)的新鮮感,“因?yàn)橹袊?guó)的武俠玄幻世界對(duì)國(guó)外讀者來(lái)說(shuō)是嶄新的,像‘修仙這個(gè)概念在西方也是沒(méi)有的。更何況很多玄幻小說(shuō)還吸收了西方文化,尤其是游戲文化,所以更容易讓人覺(jué)得熟悉”。
中國(guó)網(wǎng)文被老外網(wǎng)民“追更”,凡是第一次聽(tīng)到這個(gè)消息的人,還都暗暗有些吃驚。而被主流文化熏陶多年的人,更愿意咂摸其中的深意。“我吃西紅柿”說(shuō),自己之前想過(guò)把作品傳播到海外,不過(guò)沒(méi)想到是讀者自發(fā)翻譯在論壇上傳播,“看到那些評(píng)論,感覺(jué)很美妙”。他覺(jué)得,遭遇這樣的驚喜,也會(huì)激勵(lì)網(wǎng)絡(luò)作家們努力寫(xiě)出更好更優(yōu)秀的小說(shuō)。北京大學(xué)中文系副教授邵燕君開(kāi)心地表示,這回真給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提氣,“一直以來(lái),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被認(rèn)為是快樂(lè)文學(xué)、低俗文學(xué),是給人逗樂(lè)、解悶的,而此番可以正視自己的地位了”。她認(rèn)為,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其實(shí)已經(jīng)承擔(dān)了主流文學(xué)的職能,也越來(lái)越精品化、越來(lái)越正能量,擁有最大量的讀者,反映了人們的焦慮,也撫慰了人們的心靈。文學(xué)評(píng)論家李敬澤認(rèn)為,中國(guó)文化輸出,過(guò)去更多經(jīng)過(guò)文學(xué)獎(jiǎng)、圖書(shū)展、電影節(jié)、版權(quán)輸出等主流渠道,而這一次,真正意味著中國(guó)流行文化首次走進(jìn)歐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自發(fā)翻譯、在線(xiàn)閱讀、粉絲社區(qū)的出現(xiàn),意味著我們整個(gè)文化生態(tài)的輸出已經(jīng)開(kāi)始。讀者看書(shū)、追更、互動(dòng)、評(píng)論,這才是完整的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文化。”
觸摸流行語(yǔ)背后的時(shí)代體溫
人民日?qǐng)?bào)刊文說(shuō),《咬文嚼字》發(fā)布了“2016年十大流行語(yǔ)”,熱詞的背后體會(huì)到民意,年度流行語(yǔ)雖然只有短短數(shù)字,卻能勾起大家對(duì)2016年一些社會(huì)事件的回憶。無(wú)論是“小目標(biāo)”,還是“藍(lán)瘦,香菇”,這些詞語(yǔ)看似有些無(wú)厘頭,放在具體語(yǔ)境中解讀,卻戳中了人們的內(nèi)心。另一方面,詞語(yǔ)能迅速成為人們熱議的話(huà)題,不僅在于符合網(wǎng)絡(luò)社會(huì)短平快的傳播方式,更因?yàn)樗鼈冊(cè)从谏鐣?huì)生活、反映很多人的心理訴求。“吃瓜群眾”表面上是調(diào)侃沉默的圍觀者,其實(shí)反映了網(wǎng)民對(duì)熱點(diǎn)事件的關(guān)注;“小目標(biāo)”看似宏大,某種程度上也勾連了創(chuàng)新創(chuàng)業(yè)的高漲熱情……讀懂流行語(yǔ)背后所反映的民情民意,把握社會(huì)思潮的風(fēng)向標(biāo),方能準(zhǔn)確體察輿情,更精準(zhǔn)地服務(wù)民眾,幫助他們排憂(yōu)解難。“以我口說(shuō)我心”,流行語(yǔ)是時(shí)代的折射,也是時(shí)代個(gè)體的內(nèi)心表白。之所以能流行,是因?yàn)閵A帶有亦莊亦諧的意味,暗合了隱晦的情感表達(dá),戲謔中不乏愉悅。不過(guò)仔細(xì)推敲,評(píng)選出的熱詞中,“藍(lán)瘦,香菇”是諧音的變體,“葛優(yōu)躺”是偶然現(xiàn)象的描述,“小目標(biāo)”是草根的自嘲……似乎并沒(méi)有真正表達(dá)新事物,因此有可能像之前的“火星文”“甄嬛體”一樣,慢慢沉入語(yǔ)言的長(zhǎng)河之中。其實(shí),真正能記錄時(shí)代、反映時(shí)代的詞語(yǔ),才會(huì)被人們沿用。可以說(shuō),詞語(yǔ)有“內(nèi)核”,才能歷久而彌新。流行語(yǔ)帶有時(shí)代印記,諸如“工匠精神”“供給側(cè)”等,彰顯了國(guó)家改革發(fā)展歷程,讓人深切感受到時(shí)代發(fā)展的脈搏。不過(guò)隨著網(wǎng)絡(luò)的日趨發(fā)達(dá),有些流行語(yǔ)卻流行得莫名其妙,給人泥沙俱下、眼花繚亂的感覺(jué)。語(yǔ)言之美在韻味、在內(nèi)涵、在傳承,盲目跟風(fēng)使用,可能會(huì)消解語(yǔ)言本身的美感。時(shí)代在變遷,流行語(yǔ)也會(huì)層出不窮,我們應(yīng)當(dāng)警惕某些“新奇”用語(yǔ)對(duì)語(yǔ)言美感的侵蝕,多給孩子留一方表達(dá)的凈土。
棚戶(hù)區(qū)改造莫忘留住鄉(xiāng)愁
光明日?qǐng)?bào)刊文說(shuō),北京城西,群山綿延。元、明以來(lái),群山之中漸漸有了這么一條路,東至北京城,西至內(nèi)蒙古,成群結(jié)隊(duì)的駝馬拉著煤炭、石材和毛皮往來(lái)其上,日夜不絕。古道隘口,西風(fēng)蕩蕩,駝鈴伴著寺廟的鐘鼓,成就了這片區(qū)域經(jīng)濟(jì)文化的繁榮發(fā)展,也見(jiàn)證了歷史更迭。今天,這條路被稱(chēng)作“京西古道”。然而,曾經(jīng)的商旅重道如今不復(fù)昔日容顏。石景山區(qū)的模式口曾是古道重鎮(zhèn),有多處文物保護(hù)單位、博物館和古民居,歷史文化底蘊(yùn)深厚,但隨著城市迅速發(fā)展,竟成了一處以臟亂差聞名的地方,低端業(yè)態(tài)密布,基礎(chǔ)設(shè)施薄弱,道路擁堵嚴(yán)重,占道經(jīng)營(yíng)屢禁不止,居民和乘興而來(lái)的游人不免發(fā)出“古道斷絕、好景不再”的嘆息。最近召開(kāi)的北京市石景山區(qū)人大會(huì)議上,有關(guān)部門(mén)表示,在近兩年棚戶(hù)區(qū)改造和環(huán)境整治工作的基礎(chǔ)上,將全力推進(jìn)“模式口再現(xiàn)古道街景建設(shè)”,修繕、改造已經(jīng)列入文保單位的民居院落,植入文化功能,將山景、水景、古街景有機(jī)融合起來(lái),再現(xiàn)京西古道特色意境,力爭(zhēng)“在兩年內(nèi)實(shí)現(xiàn)模式口大街的全段復(fù)興”。近年來(lái),國(guó)家大力推進(jìn)老城區(qū)和棚戶(hù)區(qū)改造,成為提升城市品質(zhì)、改善民生的“民心工程”。但值得注意的是,老城區(qū)和棚戶(hù)區(qū)往往是一個(gè)城市歷史文化氛圍最濃厚、歷史沉淀最集中的區(qū)域,如果改造中只注重商業(yè)利益、缺乏人文思考,只顧眼前利益、不作長(zhǎng)遠(yuǎn)考量,不加辨別地大拆大建,難免會(huì)出現(xiàn)偏差。城鎮(zhèn)化要讓居民望得見(jiàn)山,看得見(jiàn)水,記得住鄉(xiāng)愁。我們需要現(xiàn)代化的城市,需要舒適便捷的居住環(huán)境,但這不等于丟掉過(guò)去,那里面藏著的往往是一個(gè)城市寶貴的文化基因和幾代人的情感記憶。環(huán)境的改造、商業(yè)布局的鋪開(kāi)和基礎(chǔ)設(shè)施的改善,與歷史文化的保護(hù)并不存在必然矛盾。歷史文化不是現(xiàn)代化改造的負(fù)擔(dān)和包袱,相反,老城區(qū)的景觀價(jià)值、文化價(jià)值、旅游價(jià)值如果能得到深入挖掘,還會(huì)成為城區(qū)改造的切入點(diǎn)和絕佳創(chuàng)意。更進(jìn)一步說(shuō),棚戶(hù)區(qū)和老城區(qū)改造是城市發(fā)展的必然要求,我們需要在實(shí)現(xiàn)功能性的同時(shí),將它深埋在久遠(yuǎn)時(shí)光中的價(jià)值重新發(fā)掘,保護(hù)好滲透在其中的歷史文化,才能真正留住一方水土,留住它獨(dú)特的歷史風(fēng)貌和格局,留住那份獨(dú)特的鄉(xiāng)愁,才不會(huì)出現(xiàn)“千城一面”的尷尬。
爛俗也算幽默的話(huà),郭德綱真是“一代宗師”了
新京報(bào)刊文說(shuō),近日在某慶典上,明星沙溢的兒子登場(chǎng)表演節(jié)目,卻遇到了嘴欠的怪叔叔郭德綱。舞臺(tái)上,郭叔叔連續(xù)數(shù)次提起,“我是你親爸爸”,當(dāng)著孩子和父母的面,調(diào)侃其是自己和沙溢夫人胡可的兒子,弄得沙溢夫婦好生尷尬。對(duì)此,網(wǎng)友怒不可遏,于是——早年郭德綱調(diào)侃柳巖穿得像洗澡的,調(diào)侃主持人“叫春”等等言論,紛紛被扒出來(lái)。更可怕的是,郭德綱的老毛病又出來(lái)了,明明是個(gè)山大王,非自以為是宗師,但見(jiàn)他大手一揮,在微博上開(kāi)始教育網(wǎng)民什么是幽默:“這世界很樂(lè)呵,這世界沒(méi)有不能開(kāi)玩笑的。”呵呵。“如果爛俗也算是幽默的話(huà),那郭德綱真是毫無(wú)疑問(wèn)的一代宗師了。”網(wǎng)友評(píng)論。
以前央視批判郭德綱,反而是給郭德綱做了這些年最成功的公關(guān)。我們還以為,這個(gè)被央視批評(píng)的說(shuō)相聲的跟我們是一伙兒的,現(xiàn)在才發(fā)現(xiàn),自己人欺負(fù)自己人原來(lái)更狠。郭德綱吸收了中國(guó)俗文化里最市儈和勢(shì)利的一套,中國(guó)民俗里那套欺凌取笑弱小的東西,郭德綱全學(xué)會(huì)了,用肆無(wú)忌憚的床笫之事調(diào)侃女性,用綠帽子調(diào)侃男性,說(shuō)到底,都是把街頭菜場(chǎng)聊八卦那套搬到臺(tái)面上。再想想趙本山大叔所代表的春晚綜藝,嘲諷農(nóng)民工兄弟、殘疾人士和個(gè)別地域,也是同樣邏輯。在這一點(diǎn)上,不能因?yàn)楣戮V會(huì)幾句民間曲藝,能說(shuō)幾句央視不能播的黃段子,拉來(lái)民俗文化的大旗,就輕易放過(guò)他。我們現(xiàn)在的曲藝文化,很多都去掉了民俗文化中嘲諷解構(gòu)強(qiáng)者的元素,只剩下拿弱者尋開(kāi)心。鄭振鐸在《中國(guó)俗文學(xué)史》中歸納過(guò),中國(guó)俗文學(xué)表現(xiàn)著“中國(guó)過(guò)去最大多數(shù)人民的痛苦和呼吁,歡愉和煩悶,戀愛(ài)的享受和別離的愁嘆,生活壓迫的反響以及對(duì)于政治黑暗的抗?fàn)帯薄6@些元素到了我們這個(gè)年代,只剩下兩個(gè)字:爛俗。無(wú)論是鄉(xiāng)村二人轉(zhuǎn)還是云南山歌,調(diào)戲叔嫂弟媳家庭亂倫,刻薄殘障窮人,說(shuō)到底,無(wú)非是用打壓弱者賦予觀眾以強(qiáng)者的滿(mǎn)足感。幽默當(dāng)然百無(wú)禁忌,但郭德綱說(shuō)錯(cuò)了一點(diǎn),幽默永遠(yuǎn)是對(duì)強(qiáng)權(quán)和不公的,而不是對(duì)著婦女和兒童。嘲諷弱者不叫幽默。當(dāng)然,如果爛俗也算是幽默的話(huà),那郭德綱真是毫無(wú)疑問(wèn)的一代宗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