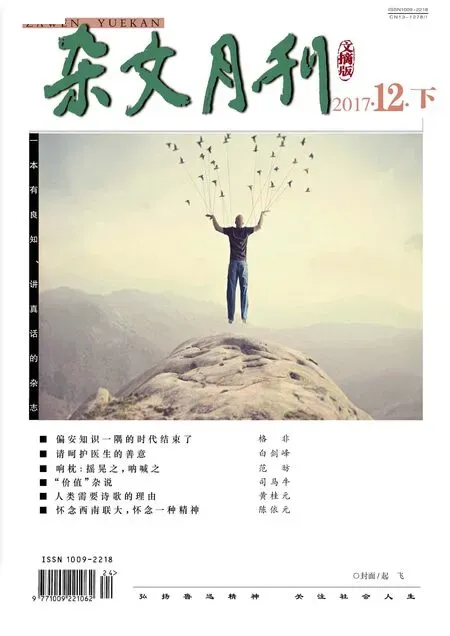什么是一流人才
□李新宇

人們常說某人的大腦“真好用”,又常說某人的腦子是“糨糊”,是“榆木疙瘩”。看來,大腦真有質量上的差異。它決定著一個人的愚與智,以及其才能的偏與全。
從過去科舉取士的八股,到現在招考的標準答案,都有許多弊端,但仔細想來,對于選擇人才,卻并非完全無效。所謂高分考生,歷來有不同情況,即使狀元,也多有只會背書的庸才。但必須承認的是,狀元肯定不是最愚蠢的,而且其中確有天才。
眾所周知,科舉的八股取士是足以使天才變成庸才的。因為它本來就并非只為取士而設,試想,天下人才如果太多,朝廷用不了怎么辦?人才藏于民間,皇帝豈能安睡?這就需要一種教育和選拔的機制,使被選擇者好用,使被淘汰者無用。嚴復在《論世變之亟》中曾經說過:“宋以來之制科,其防爭尤為深且遠。取人人尊信之書,使其反覆沉潛,而其道常在若遠若近,有用無用之際。懸格為招矣,而上智有不必得之憂,下愚有或可得之慶。于是舉天下之圣智豪杰,至凡有思慮之倫,吾頓八纮之網以收之,即或漏吞舟之魚,而已暴鰓斷耆,頹然老矣,尚何能為推波助瀾之事也哉?”可是,畢竟有一些人很頑強,雖是傷痕累累,但任你一遍又一遍將其摁入模具,甚至進行冷凍和烘烤,他都仍然能保持生命的活力;你一松手,其枝葉就又任性地生長起來。這些人才是天才,或者說:是一流人才的坯子。
不過,這些人也有一個問題:他們很容易成為模具的簡單反抗者,有很強的叛逆性,習慣于逆向思維,因而導致一個后果——他們考試難得高分,只能被淘汰。人們常為這些人惋惜,嘆息不合理的選拔機制,使有頭腦的英才敗于無頭腦的庸才。但仔細想來,那些在劣勝優汰機制下被淘汰的才子們,其實還是二流人物。因為如果真的很聰明,就應該能適應各種考試,玩得轉最荒唐的規則。玩得轉規則,卻不讓規則改變自己,這樣的人才是真正的一流人才。
以上這些感想,是我面對張謇的文集、日記和自訂年譜所想到的。在我看來,張謇就是這樣的一流人才。盡管他在科舉路上也曾屢屢受挫,但無論怎么說,最后能中進士,又中狀元,說明他已把科舉考試的那些規則吃得很透。一般人就是在吃透那些規則的過程中完全失掉了自我,變成了欽定知識的復寫機器。而張謇卻是進得去又出得來,拿得起也放得下。中狀元,對于走仕途、混官場而言,那是一個無與倫比的高起點。這一點張謇不是不明白,他后來的事業也充分利用了這個身份;但張謇卻對官場失掉了興趣,所以很快改弦易轍,借丁憂而還鄉,辦工廠做生意去了——那本是不必中狀元、甚至連秀才都不必考的。可是,他再次證明了自己,成為舉國矚目的實業界領袖。
然而,你以為張謇鉆進錢眼里了嗎?只關心富己、富民、富國嗎?辛亥革命爆發,他卻成了政壇上的活躍人物,為終結帝制和創建共和做出了別人無法做出的貢獻。結果是無論孫文當臨時大總統,還是袁世凱當大總統,都要請他出山——無法推托,就為孫文當一把實業總長,再為袁世凱當一把農商總長。他盡心盡力幫人,卻總在適當的時機轉身而去,不為任何人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