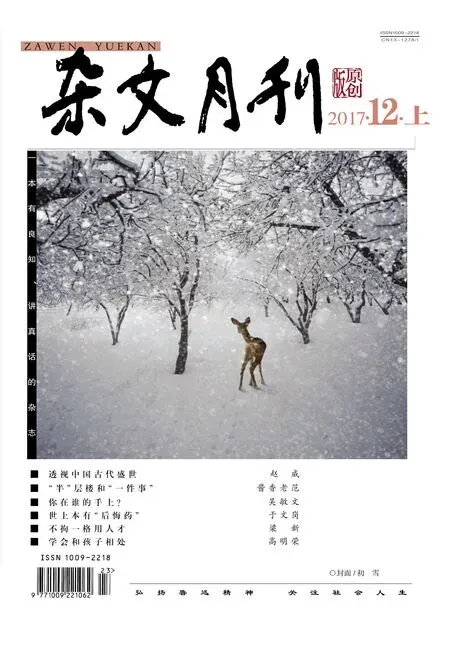好大膽的王璡
●嚴(yán) 陽

明人朱國禎的《涌幢小品》卷之十三“埋羹撤茶”中,講了這樣一個故事:王璡(音 jīn,意思是像玉的石頭,很美),昌邑人,洪武初,以儒士歷寧波知府。堂饌用魚肉,命埋之,號埋羹太守。有給事來謁,具茶,給事為客居間,公大呼撤去。給事慚而退,又號撤茶太守。
昌邑,位于山東半島西北部,濰河下游,萊州灣畔,今天是濰坊市下轄的縣級市。明朝洪武年間,從這里走出的一個名叫王璡的人,這個人待人接物很有些個性。他擔(dān)任寧波知府的時候,竟然讓人將“堂饌”(時政事堂的公膳,類似于今天的公務(wù)餐)埋了——顯然是他對高標(biāo)準(zhǔn)的“堂饌”看不慣,決意取消它。更夸張的則是,有給事中來拜訪,手下之人為其準(zhǔn)備了茶水,他在發(fā)現(xiàn)之后居然也讓人撤下了——這應(yīng)該因為他試圖節(jié)約這筆費用。
前者從操作層面來說,難度并不是很大——只要做知府的嘴巴不太那么饞,問題較好解決,因為他可是地方政府的一把手,屬于他權(quán)力范圍內(nèi)的事,他可以說了算,但是,公然讓人撤下用來招待給事中的茶水,那是需要一定底氣和膽量的——給事中品級未必很高,但因為負(fù)責(zé)的是彈劾百官的監(jiān)察工作,權(quán)力很不小。所以,王璡命人撤去茶水,有斗膽摸老虎屁股的意思;而老虎的脾氣我們是知道的,那可并不好惹。
這讓人想起了今天我們常說的這樣一句話:無私者無畏。為什么“無私者”能夠“無畏”?道理很簡單:當(dāng)一個人少一些私心雜念的時候,自然可能行得正、坐得也正,屁股上沒有不干凈的東西;而且屁股上沒有不干凈的東西,那么,哪里會怕人掀你的褲子?與此同時,這樣的人通常也不會把官帽太當(dāng)回事,如此這般,別人能拿什么威脅與嚇阻你呢?
如果一個社會里像王璡這樣的官員不是一個兩個,而是層出不窮、遍地都是,那么,這個社會官場腐敗發(fā)生的可能性必然大大降低;如果官場上“官風(fēng)”很清、很正,那么,“民風(fēng)”絕對不會差到哪里去——前者對后者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是眾所周知的。可惜的是,因為人性的弱點,更因為封建社會娘胎里帶來的很多毛病,決定了即便是在開國之初還有幾個王璡的話,隨著時間的推移,這樣的人最終也會越來越少,并且對社會、對國家的影響逐漸變得無足輕重。
因此,我們不由得感嘆,這王璡真的好大膽。而在明朝末年,社會和朝廷頹勢難挽的背景下,曾經(jīng)的朝廷首輔朱國禎為什么會想起王璡這個“埋羹太守”“撤茶太守”呢?這一定是有原因的。然而,到底是什么原因我們卻永遠(yuǎn)也不會知道了,因為他有關(guān)王璡的故事講到這里就戛然而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