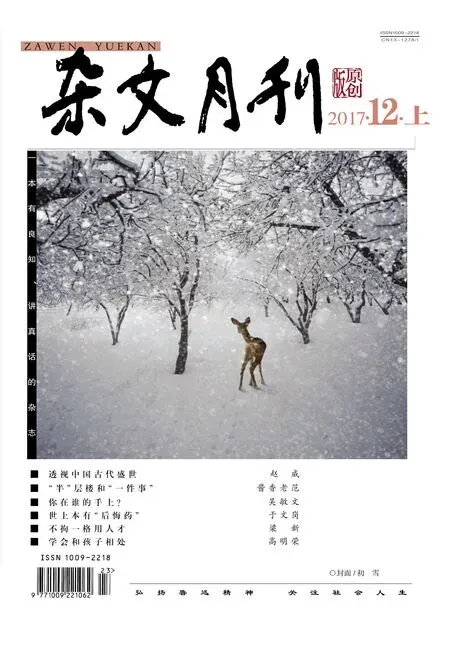柴科夫斯基的誠(chéng)實(shí)
●郁 土

凡熱愛音樂(lè)的人,沒(méi)有不知道俄羅斯大作曲家柴科夫斯基(1840~1893)的。即使像我這樣的音樂(lè)門外漢,對(duì)于芭蕾舞曲《胡桃夾子》《天鵝湖》《睡美人》也是略知一二的。所以,當(dāng)在舊書店看到柴科夫斯基的《論音樂(lè)與音樂(lè)家》一書時(shí),我就毫不猶豫地把它收入囊中,并于昨日讀完,結(jié)果便是從中了解到了評(píng)論的真諦——真誠(chéng)。
在《關(guān)于里姆斯基-科薩科夫的〈塞爾維亞幻想曲〉》中,他這樣寫道:“讀者需要明白,如果一個(gè)評(píng)論者錯(cuò)了,是錯(cuò)得誠(chéng)實(shí);評(píng)論者可以不懂,但他必須要求懂。”“這份報(bào)紙(指《幕間休息報(bào)》)上出現(xiàn)的音樂(lè)評(píng)論,表明作者其人可能不很內(nèi)行,但無(wú)論如何對(duì)待自己的工作是誠(chéng)實(shí)和熱愛的。”老柴把誠(chéng)實(shí)看得十分重要。
而他的誠(chéng)實(shí)表現(xiàn)在其毫不客氣地指出名家的缺點(diǎn)來(lái)。他如此評(píng)論莫扎特:“莫扎特的弱點(diǎn)是他寫的一些冗長(zhǎng)的、適合音樂(lè)會(huì)演唱用的詠嘆調(diào)。這些詠嘆調(diào)使歌手們有機(jī)會(huì)炫示其藝術(shù),但本身不具備真正的音樂(lè)上的美。”(《意大利舞臺(tái)上的莫扎特歌劇〈唐-璜〉》)。
他這樣評(píng)價(jià)舒曼的第三交響曲:“交響曲的結(jié)尾是最不成功的部分。顯而易見,舒曼為了對(duì)比,打算在陰郁的第四樂(lè)章后面接上歡快性的樂(lè)曲。但是舒曼這位擅長(zhǎng)于表現(xiàn)人間悲愁的歌手應(yīng)付不了歡快性樂(lè)曲。”(《第二次交響音樂(lè)會(huì)——舒曼的第三交響曲》)
老柴十分推崇瓦格納,認(rèn)為“瓦格納顯然是本世紀(jì)下半葉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他對(duì)音樂(lè)界的影響是重大的”,并不惜篇幅介紹了瓦格納的巨作《尼貝龍根的指環(huán)》三部曲。而這并沒(méi)有妨礙他指出:“但是我確信,他是一個(gè)走錯(cuò)了路的天才。瓦格納是一個(gè)偉大的交響樂(lè)作家,但不是一個(gè)偉大的歌劇作曲家。如果這位不同尋常的人物畢生不在歌劇形式中用音樂(lè)刻畫德國(guó)神話的人物,而去寫交響樂(lè),那么,我們可能就會(huì)得到一些與貝多芬的不朽創(chuàng)作完全可以媲美的杰作。”(《瓦格納及其音樂(lè)》)
老柴對(duì)于自己,也有著清醒的認(rèn)識(shí)。他曾寫到著名的音樂(lè)評(píng)論家居易,在他剛開始作曲時(shí)曾說(shuō):“柴科夫斯基先生差極了,他沒(méi)有半點(diǎn)才能。”而當(dāng)柴科夫斯基1887年3月5日在彼得堡貴族俱樂(lè)部舉行的愛樂(lè)協(xié)會(huì)音樂(lè)會(huì)上親自指揮演奏自己的作品時(shí),這位評(píng)論家又“說(shuō)我是一個(gè)‘卓越的’指揮”,對(duì)此,老柴有著清醒的認(rèn)識(shí):
“一個(gè)47歲的人,第一次手執(zhí)指揮棒演出,是不可能成為‘卓越’指揮的,盡管具有必要的天賦資質(zhì),也是不可能期望成為一名卓越指揮的。我很了解,天生的畏葸、性情軟弱和缺乏自信妨礙并將始終妨礙我在指揮工作上與瓦格納、彪洛夫和納普拉甫尼克一爭(zhēng)短長(zhǎng)。”(《1888年國(guó)外旅行自述》)
當(dāng)然,柴科夫斯基之所以能夠指出莫扎特、舒曼、瓦格納作品的缺點(diǎn),是因?yàn)樗救艘彩且晃淮笞髑遥蜕鲜鲋T人處于一個(gè)平等的地位,他具備這個(gè)能力。但更重要的,是因?yàn)樗恼\(chéng)實(shí)。有評(píng)論的能力,并不等于非要如此評(píng)述,他完全沒(méi)有必要實(shí)話實(shí)說(shuō),來(lái)得罪那些莫迷、舒迷與瓦迷們的。
老柴寫的是音樂(lè)評(píng)論,但無(wú)論音樂(lè)評(píng)論,還是文藝評(píng)論,其本質(zhì)是相通的。正因如此,我從中窺見了文藝批評(píng)的真諦,那就是誠(chéng)實(shí)。無(wú)能力當(dāng)然談不上評(píng)論,但有水平而無(wú)誠(chéng)實(shí)的態(tài)度,也是寫不好評(píng)論的。鄙人每日從報(bào)刊上讀到的文藝評(píng)論不在少數(shù),但真正有見地又誠(chéng)實(shí)者鳳毛麟角,多的是溜須拍馬、相互吹捧的文章。這些文字,非但無(wú)助于讀者對(duì)作品的理解,反而徒令人增添反感。而當(dāng)這些披著“評(píng)論家”外衣的假貨滿天飛舞時(shí),那些真正意義上的嚴(yán)肅評(píng)論,人們也就不會(huì)去相信矣,因?yàn)椤凹僮髡鏁r(shí)真亦假”。而這些假貨,既無(wú)助于提高讀者的鑒賞能力,又起不到推廣作品的功效,徒然浪費(fèi)了捉刀人與讀者的許多寶貴時(shí)間與精力,可謂雙輸。不像我讀老柴的這本薄薄小冊(cè)子,讀過(guò),我就對(duì)莫扎特、舒曼、瓦格納,及柴科夫斯基本人,有了進(jìn)一步的認(rèn)識(sh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