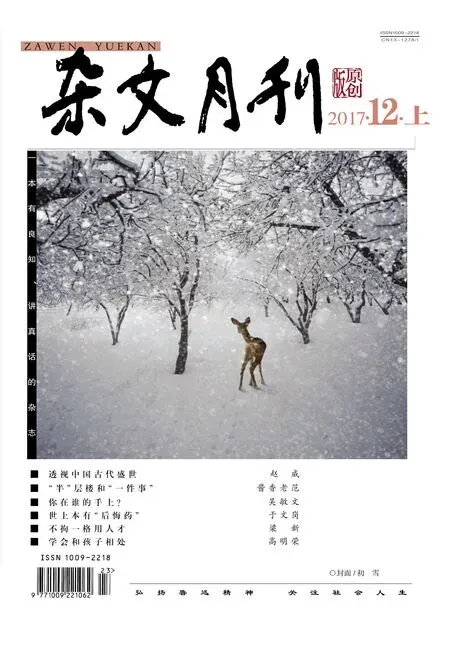孫犁先生文字中的史家之筆
●王文靜
說(shuō)到讀書(shū),四十歲以后,重讀文學(xué)前輩孫犁先生的散文,我更感趣味。常常讓我手不釋卷,反復(fù)閱讀的就是《耕堂劫后十種》,十本素雅清淡的小冊(cè)子。
十年浩劫,孫犁花甲晚年后的衰年變法的大量文字,依然散兵游勇一樣,在歲月的巷道里,沉寂下來(lái),停駐,凝眸,回望,踱步,思考,轉(zhuǎn)身,一個(gè)人,獨(dú)自一人,用他文壇邊緣人的獨(dú)特筆法,撿拾生命里重要?dú)v程里的那些人那些事。
我的老家一路十八橋,離孫犁的老家安平距離不太近,可離他青少年讀書(shū)的安國(guó)和保定,都不太遠(yuǎn)。他的故鄉(xiāng)紀(jì)事,他的少年讀書(shū)歲月,他的文學(xué)啟蒙,他的愛(ài)國(guó)情懷,他的投奔革命,以我的淺陋的學(xué)識(shí),讀起來(lái)并不深?yuàn)W難懂。
他的晚年文字,在四十歲以后,拿起來(lái)再讀,況味別與從前。近些日子我常常從書(shū)中孫犁先生的影像資料,讀他的那雙眼睛,讀著讀著似曾見(jiàn)過(guò)。認(rèn)真想過(guò),原來(lái)和我少年讀過(guò)一本史記故事書(shū)中扉頁(yè)上的作者的那雙眼睛重合了。
少年時(shí)讀《史記》,更多是喜歡故事中的精彩歷史情節(jié),也知道越是人生倒霉的角色,太史公越是傾注情感,傾情為之大書(shū)特書(shū),比如那個(gè)和虞姬一起亡命烏江的西楚霸王。再長(zhǎng)大些,讀歷史,知道司馬遷是個(gè)仗義說(shuō)真話(huà)的好人。但是好人卻不得好命,為李陵之事,他同情李陵,在漢武帝面前說(shuō)了幾句好話(huà),結(jié)果遭到肉體的摧殘。之后忍辱負(fù)重,完成《史記》。
孫犁先生不是史學(xué)家,他是文學(xué)家,有著十足美學(xué)和美好思想的散文大家,從他的散文里,能享受他詩(shī)意般的文筆,讀著讀著就仿佛看見(jiàn)一個(gè)文弱書(shū)生,遠(yuǎn)離家鄉(xiāng),別家棄舍,不停地奔走在抗日戰(zhàn)爭(zhēng)、解放戰(zhàn)爭(zhēng)、土改運(yùn)動(dòng),解放初的經(jīng)歷過(guò)往,用他史家一樣的文學(xué)之筆,做著最真實(shí)的歷史記載。
司馬遷的《史記》,魯迅先生評(píng)價(jià):史家之絕唱,無(wú)韻之離騷。中年以后再讀孫犁散文,特別是他的衰年變法,我更加確定了他的“史家大手筆”。他的云齋小說(shuō),我一直當(dāng)敘事散文來(lái)讀,從原來(lái)詩(shī)意的小說(shuō)文學(xué)創(chuàng)作到哲學(xué)思想,從情感表達(dá)到情理抒發(fā),他的雜文,他的讀書(shū)記,他的書(shū)衣文錄,處處蘊(yùn)含著他對(duì)世人的警世提醒。

而這種筆法,毋庸置疑,應(yīng)該源自魯迅先生最推崇的史學(xué)大家司馬遷,這種傳統(tǒng)文學(xué)筆法脈絡(luò),只要將先生的中晚期的各種文字,甚至后來(lái)被收納在小說(shuō)集中的散文篇章集中閱讀,很容易就能發(fā)現(xiàn)。看到精彩結(jié)尾文字,我更加相信,此乃太史公的文字遺風(fēng),他的“耕堂曰”“云齋主人曰”,這種文言版的評(píng)述,正是脫胎于太史公曰。
正如魯迅先生說(shuō)的:悲劇就是將人生有價(jià)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越是美好的事物,它的毀滅帶給人的震撼就越大,悲劇的感染力也就越是強(qiáng)烈。孫犁先生的遭遇和史學(xué)大家一樣,他曾為被定為“分子”的某作協(xié)同事說(shuō)過(guò)不少好話(huà),但這位詩(shī)人很快被逮捕。如果不是熟人主持會(huì)議,他必受牽連。他因而“受了很大刺激,不久以后就得了神經(jīng)衰弱癥”。那時(shí)的孫犁先生,萬(wàn)念俱灰時(shí)也觸床頭前的電燈自殺過(guò),未遂。
和偉大的史學(xué)家一樣,盡管曾遭受摧殘,但恨還有一支“戀戀寫(xiě)作”的創(chuàng)作初心。十年浩劫,花甲第三年,孫犁先生遠(yuǎn)離喧囂,獨(dú)居陋室,在津門(mén)耕堂衰年變法,讀書(shū)寫(xiě)作,終于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里,完成了他的十本劫后十種淡雅的小書(shū)冊(cè)。就像完成《史記》的史學(xué)家司馬遷,孫犁先生的《耕堂劫后十種》,在近當(dāng)代文學(xué)史上,一樣堪稱(chēng)絕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