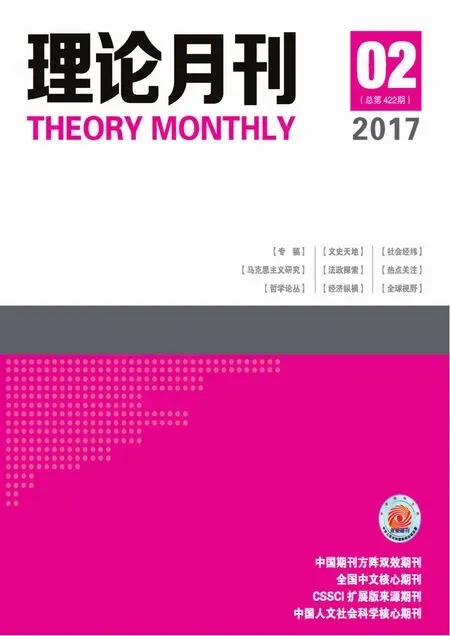“文化例外”的歷史演變及當代啟示
□王軍
(武漢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北武漢 430072)
“文化例外”的歷史演變及當代啟示
□王軍
(武漢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北武漢 430072)
“文化例外”是指以電影和音像制品為代表的文化產品不能完全遵從市場邏輯,貿易自由化原則不完全適用于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因為文化產品不是一般普通的商品,它不僅有商品屬性,而且有文化屬性,是傳播一定思想價值觀念的重要載體。為避免過度市場化、商業化帶來的文化標準化、同質化,保護本國文化的多樣性,使廣大民眾能夠擁有和享受豐富多樣的文化生活,政府有權力和義務對文化產品、文化事業進行管理。“文化例外”不等同于文化保守和文化排外,而是蘊含著強烈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
法國;文化例外;文化自覺;文化自信
2016 年上半年,一部名為《百鳥朝鳳》的電影引起廣泛關注,拋開“跪求排片”的爭議舉動不論,影片本身所傳遞的對傳統文化傳承的焦慮,以及市場經濟大潮下傳統文化面對西方文化的沖擊所展現出的無力感,都讓人沉思。不過令人欣慰的是,傳統文化在當下正受到越來越多的肯定和重視,較之影片中的落魄處境有了很大的改善。當然,在經濟全球化、文化全球化、信息全球化不可逆轉并且日益深入的情況下,傳統文化的當代危機依然未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就他山之石而言,由法國倡導和捍衛的“文化例外”頗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
談及“文化例外”,大家或許還不太熟悉,甚至有些不知所謂,但是另外一個詞匯——“文化多樣性”,大家肯定不陌生。實際上,對“文化多樣性”的認識以及200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的《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都與“文化例外”有著直接關聯。所謂“文化例外”,是指文化產品(主要是電影和音像制品)不能完全遵從市場邏輯,貿易自由化原則不完全適用于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因為文化產品不是一般普通的商品,它不僅有商品屬性,還有文化屬性,是傳播一定思想價值觀念的重要載體。為避免過度市場化、商業化帶來的文化標準化、同質化,保護本國文化的多樣性,使廣大民眾能夠擁有和享受豐富多樣的文化生活,政府有權力和義務對文化產品、文化事業進行管理[1]。
1 “文化例外”的歷史演變
“文化例外”的概念由法國在1993年的關貿總協定“烏拉圭回合”談判中正式提出,迄今不過二十余年的歷史,但是與其有關的政策卻由來已久。1928年2月法國開始實施互惠配額制,規定美國必須先購買和放映法國電影,然后才能在法國發行和放映美國電影;1932年又推行配音配額制,對外國配音電影在法國的放映數量進行限制;1946年實行銀幕配額政策,明確要求每個季度至少要放映4個星期的法國電影[2]。1948年法國議會通過了一項影響深遠的電影資助法案,其中重要一條是對所有電影院的觀眾征稅,并用稅收所得建立一個專門資助法國電影人的國家基金(這個機制成為1993年法國和美國爭論的核心,雙方為是否該對電影實行保護主義爭論不休)。1958年法國政府成立了文化事務部,下設國家電影中心,這表明電影不再是一個普通的產業,因而具有里程碑意義。
此后的20年間,瑞典、荷蘭、丹麥等歐洲國家也通過一些政策保護和發展國產電影,并強調質量。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歐洲對電影的資助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即在各國政府和地方權力機關采取資助措施外,歐洲各機構也采取措施加大對電影的資助力度。1988年,來自歐洲理事會的12個成員國共同開展了一項“歐洲影像計劃”,到20世紀90年代絕大部分中東歐國家相繼加入。“歐洲影像計劃”推出不久,1990年歐洲各機構又開始實施名為“MEDIA”的五年計劃,支持音像產業發展。這兩個計劃都支持歐洲各國電影的發展以及在整個歐洲的發行。正是因為歐洲各國普遍對本國電影實施補貼和資助,所以美國代表團成員在1993年的“文化例外”論戰中大聲疾呼:“各國政府都有權資助古典音樂、歌劇、戲劇和舞蹈,因為這些是藝術,美國政府也正是這么做的。但是電影和電視無論如何都不能算是藝術:電影和電視只是娛樂,就像玩牌和騎自行車散步。”[3]14-20也就是說,在美國人看來,電影和電視都不算藝術,歐洲各國對電影和電視采取扶持政策有違貿易公平,這阻礙了美國電影、電視在歐洲的輸出。
在1993年的“烏拉圭回合”談判中,美國認為法國等國家對電影和音像制品的資助措施違反了《關稅和貿易總協定》的貿易公平原則,要求這些國家取消電影電視的配額制并對外國影視公司給予國民待遇和最惠國條款,而法國、加拿大等國家則始終認為文化產品不是一般的商品,堅持要求“文化例外”。此外,由于對電影的國籍、音像制品的定義等問題存在模糊認識和分歧,因而各代表團沒能(或者不想)就電影和音像制品達成協議,但最后還是找到了一個折中方案:第一,電影和音像制品將來肯定會被列入世貿組織的最終協議,各成員方都將嚴格執行協議;第二,這兩種產品的列入并不會迫使各成員方在這兩個有爭議的領域遵守世貿組織的各項規定,各成員方仍可按自己的意愿繼續支持本國電影、音像的生產,除非他們另有安排。在1993年的論戰中,法國和加拿大都采取了非常堅定的立場。兩國官員認為他們不能孤軍奮戰,應該讓盡可能多的國家參與其中,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可以成為這種合作的平臺。此后經多方努力,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于2001年起草完成了《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之所以沒有在題目中寫入“文化例外”,一是因為“文化例外”不能被很好地理解,二是因為“文化例外”只不過是手段,文化多樣性才是目標所在[3]40-79。
時間到了2013年,此時距離1993年的論戰已經過去了20年,一場關于“文化例外”的新的斗爭再次展開。在經歷了長時間的經濟低迷之后,歐盟和美國籌謀簽署新的歐美自由貿易協定(TTIP)以推動歐洲和美國經濟的復蘇,但文化觀念、立場上的嚴重分歧,使得歐盟內部在文化產業領域長時間未達成一致。以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和法國總統奧朗德為首的兩方陣營為此紛紛發表評論,展開了唇槍舌劍的交鋒。巴羅佐在接受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的訪談中宣稱,他贊成保護文化的多元性,但是不能因此在歐洲四周設置一條防線,法國堅持將視聽產業排除在貿易談判外是違背歷史潮流的行為,是反全球化綱領的一部分。巴羅佐還聲稱,那些“文化例外”的捍衛者完全沒有理解全球化的好處,即使從文化角度也是如此[1]。巴羅佐的此番言辭令法國朝野震驚,引發抗議聲浪。6月14日,法國文化部長奧雷利·菲利佩蒂女士在《世界報》發表題為《法國——直面自由市場堅持“文化例外”的先鋒》的文章,堅稱:“‘文化例外’是法國深深懷有的政治信念和思想原則信念。我們認為,文化產品非一般商品,文化產品因其特殊價值不能屈從于市場。一個國家具備在世界上展現自身特色的能力是十分重要的,我們不能在盲目的市場法則中拋棄文化、迷失自己。”[4]為了捍衛“文化例外”,法國不惜動用否決權阻攔談判進行。經過法國上下一心、毫不妥協的誓死斗爭,歐盟27個成員國最終達成一致,宣布將影音等文化產業完全排除在此次歐美自由貿易的談判范圍。至此,關于“文化例外”的爭議在歐盟內部得到暫時平息,法國終于贏得“文化例外”斗爭的階段性勝利。
雖然法國視之為信念的“文化例外”其前途依然崎嶇坎坷,但是其中所蘊含的強勁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精神深深感染了眾多國家,法國為捍衛本國文化安全以及保護文化多樣性的努力也贏得越來越多國家的認同。
2 “文化例外”的國際經驗
在商品貿易中堅持“文化例外”政策最堅決、最徹底的兩個國家當屬法國和加拿大,而這兩個國家矛頭所指的也主要是美國,因為美國擁有全世界最強大的文化娛樂產業,對別國的文化安全危害最大。在2013年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議談判”中,法國之所以堅持強硬的“文化例外”立場,是因為在法國看來,美國電影在歐洲影院中占據高達60%的內容,而歐洲電影在美國市場僅占3%-6%。在市場份額對比如此懸殊的情況下,如果進一步向美國開放文化產業和電影市場,那么歐洲的文化產業將遭遇嚴重的生存危機。法國還擔心,數字和互聯網服務的日趨流行以及美國互聯網科技公司在其中占據的主導地位,只會使這種文化貿易上的不平衡繼續加劇[5]。正是懾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全球化浪潮中的文化霸權以及對自身文化價值安全的擔憂,由法國倡導和捍衛的“文化例外”原則得到越來越多國家的了解和認同,一些國家也實施了本國的“文化例外”政策或者采取了類似的措施。
面對西方文化特別是美國文化的強勢,以沙特為代表的阿拉伯國家提出了“伊斯蘭文化例外”的主張,最核心的便是捍衛自己的宗教文化。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中,盡管沙特作出了許多承諾和讓步,但是入世條款中沒有要求沙特進口豬肉、含酒精飲料等與宗教信仰抵觸的商品。在自由貿易和對外商務活動中,沙特堅持宗教信仰神圣不可侵犯,因一本書、一部電影而引起伊斯蘭世界憤怒的場景屢見不鮮。一些與伊斯蘭文化不相符的形象、元素,在沙特也被予以禁止或改造。例如,沙特認為,猶太芭比娃娃暴露的衣著和可恥的姿勢是西方墮落的象征,因此沙特國內禁止出售芭比娃娃,取而代之的是體現穆斯林道德價值觀的芙拉娃娃——芙拉被設計成傳統的圍繞著家庭和家人生活的穆斯林婦女,她身披長袍和頭巾,肩膀永遠被遮住,裙子也總是低于膝蓋。一些穆斯林家長認為,如果女孩們愿意給娃娃帶頭巾,那她們也會愿意給自己戴,所以芙拉一直被譽為穆斯林女孩的好榜樣[6]。
巴西對“文化例外”的態度比較靈活、務實,一方面主張實行自由貿易以便于出口具有優勢的文化產品,另一方面又反對不加任何區別的自由化,頗富遠見地為以后的自由貿易和投資談判預留了“例外”的空間。巴西認為,各國應擁有文化自主權和實施各種文化政策的能力來保護和發展文化的多樣性,以防止某種文化產品的壟斷。同時各國也應該努力豐富本國的文化產品,保證人民有機會充分接觸和了解世界各種不同的文化,而不應該采取文化隔絕措施。巴西政府還建議世貿組織對視聽文化產品采取逐漸開放的原則,并意圖淡化文化產品的商業性,而強調文化產品的公共性和文化政策的重要性。巴西從本國文化產品的實際出發制定文化政策和文化戰略,對具有優勢的電視劇和電視節目竭盡全力擴大國際市場,而對處于劣勢的電影和有線電視則是頒布法令、規定銀幕配額,同時又選擇有線電視作為扶持重點[7]。
印度雖然沒有明確提出“文化例外”的口號,但是在文化產品上也是小心翼翼、加強管理。以電影為例,外國電影雖然可以不受限額限制在印度“自由”地放映,但前提是必須通過印度政府的審查。當然,印度政府并不直接干預電影審查,而是交由“審查委員會”執行,其成員則需政府任命。為了使審查委員會依法有效地履行職能,印度政府還設立了電影審查顧問團以及解決電影審查糾紛的專門上訴法庭。總體來看,盡管印度的電影審查制度還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卻對維護健康的社會文化環境以及促進電影市場的發展繁榮發揮了積極作用[8]。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印度電影還對保護和發揚本國傳統文化不遺余力。印度80%的人口信奉印度教,他們認為是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的濕婆創造了舞蹈。濕婆最典型的一個形象姿勢是雙手合抱、左腳右抬,幾乎所有印度電影的女主角都會秀出這樣的舞姿,向印度教的神明致以敬意。因此,作為印度寶萊塢電影一大特色和重要標簽的歌舞,首先滿足的是本國人民宗教信仰的需求。通過華麗精彩的電影歌舞,印度人民的精神信仰得以維系和傳承,并且實現了價值觀傳遞和文化輸出[9]。
綜合沙特、巴西、印度等國家實施的“文化例外”不難看出,商品自由貿易不能與本國的文化傳統、價值觀念相抵觸和違背,文化政策的實施和文化產品的管理必須從本國的實際出發。另外,就一國而言,無論是外國文化產品的輸入,還是本國文化產品的輸出,都應該積極打上本國文化的烙印,如此外國文化產品不至于水土不服,本國文化產品則可以作為文化輸出和價值傳播的重要載體。當然,就文化產品的輸出國和輸入國而言,雙方始終存在一個文化價值觀念的輸出和反輸出的動態博弈過程。
3 “文化例外”的當代啟示
“文化例外”政策對于抗擊文化霸權、保護傳統文化、發展文化產業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但是這一措施也面臨諸多質疑。有專家認為,基于“文化例外”而實行的文化貿易保護戰略是一把雙刃劍,一旦過度使用也可能導致多個方面的問題,比如:對外國電影、電視節目的過度限制會使人們的需求得不到正常滿足,從而給盜版留下空間;個別企業會為了得到政府補貼而生產出沒有多少市場競爭力的文化產品,從而造成資金、資源的浪費;企業如果長期處于過度保護下,就會因缺乏外來競爭而產生惰性,久而久之就會喪失活力和競爭力[10]。
有批評者認為,“文化例外”對民族產業的保護采取的是一種純防衛性或者說是負面的姿態,這就如同修建馬其諾防線一樣解決不了問題。另外,想要保護一種文化就是承認它是弱的,甚至是衰落的。強勢的、有力的文化是不需要保護的,因為它自己就能支持、保護自己[3]62。美國人認為,“文化例外”的結果與其保護和推動文化多樣性的目標背道而馳,因為只有自由開放的市場,才是文化多樣性的基礎,才能使各種文化、各種聲音在同一個平臺同等展示、公平競爭。法國、加拿大等國的文化保護主義妨礙了“聲音的自由表達”,限制了受眾的自由選擇,因而損害了文化多樣性[11]。
盡管法國主張的“文化例外”政策有貿易保護主義乃至狹隘民族主義的嫌疑,在政策實施過程中也有不盡完善的地方,但是法國對“文化例外”的執著追求所體現出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精神頗值得我們敬佩和學習。
第一,文化產品應堅持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有機統一。“文化例外”強調文化產品不是一般的商品,它事關一國的文化血脈和文化安全,對提升公民素質和促進社會和諧繁榮也有重要作用,因而不能盲目服從資本市場的規律。當前不少國產電影過分追求明星效應以及華麗的特效場面,以致于邏輯紊亂、內容空洞、文化缺失。在惡評如潮、罵聲不絕中,這些缺乏匠心、誠意的電影也偏離了文化產品的本質,淪為沒有靈魂的空殼。對此,習近平在2014年10月主持召開的文藝座談會上強調:“一部好的作品,應該是經得起人民評價、專家評價、市場檢驗的作品,應該是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同時也應該是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作品。……文藝不能當市場的奴隸,不要沾滿了銅臭氣。優秀的文藝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藝術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場上受到歡迎。”[12]
第二,發展文化產業應將適度保護與刺激相結合。溫室里的花朵固然長不成參天大樹,但是將瘦弱的嬰兒丟在豺狼虎豹面前也極不明智。面對極具影響力、統治力的外來強勢文化產品,“文化例外”既不是盲目徹底的文化保守和文化排外,也不是麻木不仁地文化虛無和文化自賤,而是以一種折中、調和的方式為本國的文化產業營造最適宜的生存環境。“文化例外”要求對本國文化產業給予補貼、扶持,對于發展中國家具有啟發意義。中國在加入世貿組織時,雖然沒有提“文化例外”,但是在電影市場對好萊塢大片實行配給制,這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國產電影,同時好萊塢大片所帶來的鯰魚效應也增強了中國電影的質量和競爭力。從加入世貿組織初期好萊塢大片占據中國電影票房的大半江山,到最近幾年國產電影票房和好萊塢大片分庭抗禮,中國電影的質量和競爭力得到明顯提升,由此也成為“文化例外”的生動詮釋以及成功典型。
第三,守望精神家園需要繼承和發揚傳統文化。我們不能將“文化例外”等同于文化保守和文化排外,但是“文化例外”注重對本國傳統文化的保護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值得一提的是,法國和美國雖然同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根本的價值觀念上不存在沖突,但是法國卻對自己的文化傳統、文化資源格外重視,對美國文化入侵的威脅時刻警醒。這使得法國在文化精神上能夠保持獨立并且獨樹一幟,不至于在全球化的文化場域中淪為美國的附庸,同時也為世界文化的多樣性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反觀我們這個有著五千年文明、與美國文明根本迥異的社會主義國家,在走向現代化的進程中,還一度天真、自卑地認為現代化就是美國化,美國文化就是先進文化的樣板和代表。這種仰人鼻息的心態使得我們賴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園日益荒蕪和貧瘠,并產生了嚴重的精神信仰危機。總而言之,傳統文化是中國人的精神命脈,也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智慧源泉,我們必須守護好、維系好。
總之,文化多樣化不是西方發達國家的文化多樣化,廣大發展中國家如果不注重保護自己的文化,那么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強勢文化就會憑借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主導地位取代這些發展中國家的文化,如此一來諸多富有地方特色個性的文化就會消失殆盡,文化多樣化也就無從談起。作為一項文化政策,“文化例外”或許還有待商榷,但是“文化例外”所體現出的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是尤為寶貴的。我們不僅要在全球化的市場交往中有“文化例外”的睿智和勇氣,即使是在國內的經濟社會發展中也要有“文化例外”的意識和眼光,時刻注意保護傳統文化、歷史古跡,為中華文明留住根脈。
[1]劉望春.法國贏得“文化例外”斗爭勝利[N].中國文化報,2013-06-25(10).
[2]黎文宇.法國將“文化例外”堅持到底[N].環球時報,2013-07-12(13).
[3]貝爾納·古奈.反思文化例外論[M].李穎,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4]劉望春.法國誓將“文化例外”進行到底[N].中國文化報,2013-06-20(10).
[5]何農.從法國到歐洲的“文化例外”[N].光明日報,2013-12-05(8).
[6]吳毅宏.沙特阿拉伯:在貿易談判中堅持“伊斯蘭文化例外”[J].紅旗文稿,2014(19).
[7]陳家瑛.巴西:一邊主張自由貿易,一邊反對不加區別的自由化[J].紅旗文稿,2014(20).
[8]詹得雄.印度:對外來文化廣采博收的同時保持自身文化特色[J].紅旗文稿,2014(20).
[9]梁坤.印度電影為什么那么多歌舞[N].北京青年報,2014-09-23(B09).
[10]葉飛,樊煒.歐洲抗衡美國文化的一盤棋—解讀“文化例外”政策[N].中國文化報,2014-01-30(11).
[11]李寧.“自由市場”還是“文化例外”:美國與法-加文化產業政策比較及其對中國的啟示[J].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06(5).
[12]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N].光明日報,2015-10-15(1).
責任編輯文嶸
10.14180/j.cnki.1004-0544.2017.02.009
G114
A
1004-0544(2017)02-0044-05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資助項目(2016VI014);湖北省社科基金一般項目(2015062)。
王軍(1985-),男,湖北咸寧人,法學博士,武漢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