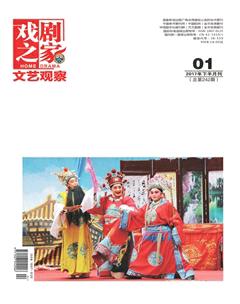《七月與安生》:愛、流浪、宿命
【摘 要】《七月與安生》作為一部女性主義電影,以獨特的風格樣式、巧妙的情節設置,隨著人物性格的逐漸豐滿、情緒的層層遞進,改變了以往青春電影“無墮胎,不青春”的青春命名,給青春電影帶來一絲新奇,是中國大陸青春電影的一次“另類書寫”。
【關鍵詞】女性電影;青春;女性主義;三角戀
中圖分類號:J90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7)01-0152-01
自小說推出以來粉絲們對于更喜歡安生還是更喜歡七月的討論就從未停止過,你愿意成為七月還是安生?是大多數人讀完安妮寶貝的小說《七月與安生》之后都會思考的問題。在安妮寶貝的筆下,宿命似乎是永恒不變的主題。電影將兩個女孩的人生分解和重建,在細節描寫上作了有效處理,有意拉長故事的節奏,使電影的主題得到了深化。
一、人物性格的塑造表現真實情感
電影理論家閔斯特貝格從審美心理生成的角度出發,認為人在觀影時,不僅僅是消極地接受,“在這一過程中,觀看者是一個合作者”。“電影不存在于銀幕,只存在于觀眾的頭腦里”。[1]所以觀眾在觀看時都會把自己和劇中角色聯系起來。能夠成為閨蜜,大多數是因為脾氣、性格都很相似,安生和七月從表面來看兩個人是完全相異的兩種女孩,一個是放蕩不羈的女生,一個是文藝乖乖女。然而這樣兩個看似平行線般相異的女孩卻成為了最好的閨蜜,其實她們就是同一類人,安生渴望像七月一樣過安定的生活卻為了生計一路漂泊。
蘇家明的出現打破了原有的兩個女孩之間的平衡,七月愛他,安生也愛他,因為安生愛七月,所以安生選擇離開,她希望自己愛的人能夠幸福,女生之間的友誼既深厚又脆弱。蘇家明就是游走在七月與安生現實和理想界線上的那根繩索,他活在七月穩定的現實里,也活在安生理想的生活中,直到有一天蘇家明從安生的理想中走進了她的現實世界,并在那里碰見了七月,七月從懷疑試探再到質問爭吵,她和安生現實和理想的界限就此崩塌,隨之崩塌的還有兩個人的深厚又脆弱的友誼。
作為女性主義電影,影片真正的主角就是兩位女主,影片對愛情的刻畫點到為止,蘇家明作為該電影的男主角,他在兩個女孩之間搖擺,但從沒主動做出過選擇,家明愛著七月的安靜平和,又被安生的放浪不羈所吸引,誰他都不愿割舍,因此他只能被動等待。電影中蘇家明的戲份雖然不多,但這一角色的生動刻畫,讓原有的故事情節更加豐富,出色的表現也成功塑造了這一角色。
二、巧妙的敘事手法烘托主題
《七月與安生》導演采用倒敘的手法,前半段七月以作者視角回顧了少年時和安生的相處片段,但后半段揭示真正的作者是安生,敘事主體的變換也揭示了兩人互換人生的謎團。劇情敘述自然平和,背景更樸實,也更貼近生活,同時,文藝氣息的襯托又讓影片質感高于生活,影片的最后展現了三種不同的結局,分別是小說中的結局、安生告訴家明的結局和真實的結局,小說中的結局是七月等了家明一個月,家明回來了,兩個人結婚。安生出國,再次寫信是告訴七月她懷了家明的孩子,七月照顧安生,最后安生因為難產死了,七月和家明一起照顧這個孩子。安生告訴家明的結局是:七月生了家明的孩子后不告而別,她要去尋找自由的生活,這是安生為家明安排的結局。電影中真實的結局是七月生完孩子后大出血,沒有搶救過來,七月死了,這個結局只有安生一人承受。導演醞釀、鋪墊呈現出大反轉的劇情,為了深入體現兩個女孩最本質的關系,導演柔化了悲劇和沖突,同時加入了理想化的解讀,在細節描寫上作了有效處理,拉長故事的節奏,突出表現兩個女孩隱藏的性格,使電影的主題得到了深化。
三、脫離俗套的“三角戀”悲情敘事
《七月與安生》上映的時候被定義為愛情片,通常的愛情片基本都會圍繞暗戀、打胎、劈腿到最后大圓滿而敘述,然而《七月與安生》卻表現得清新脫俗,區別于俗套的“三角戀”的悲情敘事。故事的開始講述性格相異的兩個女孩在十三歲時成為了不可分離的好朋友,她們兩個彼此相通相融,卻因為同時愛上一個男生故事開始變得錯綜復雜,導致七月與安生后來截然不同的人生。導演運用巧妙的方法,讓曾經互相羨慕的兩個人開始交換人生,各自都活成了自己內心渴望的樣子,一個擁有了安定的生活與完整的家庭,一個擺脫了設計好的人生,走遍世界見到了很多從未見過的風景。安生活成了七月,七月變成了安生,當預設的角色性格發生大的轉變的時候,這個關于成長的故事就變得更加絢麗多彩。
四、總結
《七月與安生》是一部用真誠講述青春、友情、愛情和宿命的電影。是一部有別于俗套“三角戀”的愛情故事,電影從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巧妙的敘事結構等都體現出女性主義的色彩。電影讓人審視人生,它對于每一個人來說,也許是一次生命的審視,一次靈魂的叩問。
參考文獻:
[1]閔斯特貝格.電影——一次心理學研究[J].電影文化,1916.
作者簡介:
晁紅秀(1992-),山東肥城人,曲阜師范大學傳媒學院2015級廣播電視碩士生,主要研究方向:廣播電視;
董從斌(1967-),山東日照人,曲阜師范大學研究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影視節目制作和影視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