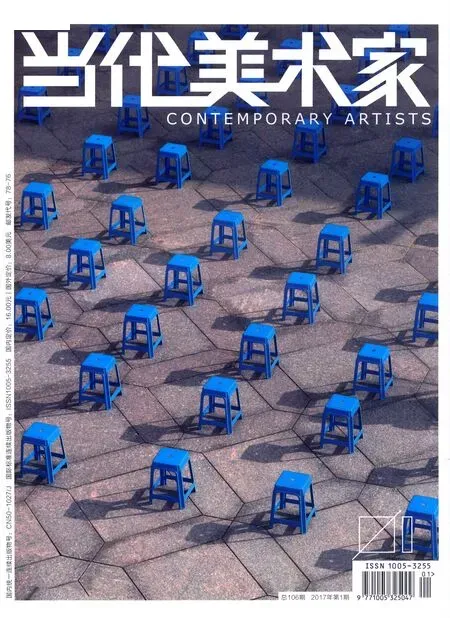與《藝術當代》共同前行
徐可
與《藝術當代》共同前行
徐可
《藝術當代》創(chuàng)刊于2001年,始終堅持專業(yè)性強,學術標準高,媒體信服力強的辦刊準則,擁有雄厚的遍及世界各地的作者資源和編委陣容,成為中國目前舉足輕重的藝術期刊,并在海外獲得了良好的反響。主編徐可自2001年進入藝術媒體行業(yè),與《藝術當代》共同見證了中國當代藝術和藝術媒體的發(fā)展。
當代藝術,藝術媒體

1 劉任 承受 雞蛋和綜合材料 80×80×43 cm 20162016年第一屆藝術媒體提名展《藝術當代》提名作品
《當代美術家》(以下簡稱“當”):請談談您是如何與藝術媒體結緣的。
徐可(以下簡稱“徐”):《藝術當代》雜志是2001年創(chuàng)辦的,我也是那一年從哈爾濱師范大學藝術學院調到上海書畫出版社來的,在此之前曾擔任《藝術交流》、《振龍美術》的編輯。當時的上海書畫出版社是一家主要從事傳統(tǒng)繪畫出版的出版社,但總編盧輔圣先生很關注當代藝術,打算創(chuàng)辦一本當代藝術的期刊。一方面,是出于對當代藝術的關注,同時,也試圖通過辦這樣一本雜志來拓寬上海書畫出版社的文化視野。當時搭建這個編輯部也比較特別,或許盧輔圣先生有他特別的考慮,啟用了兩個當年剛剛進社的新人,一個是我,一個是漆瀾,他也曾在高校任教,當時剛從南京藝術學院碩士畢業(yè)。
我們兩人幾乎都可以說是白手起家。盡管我已經有從事編輯工作的經驗,但所學專業(yè)是古典文學及美學,轉向當代藝術,這個跨度確實讓人有點“休克”的感覺;而漆瀾,他是美術科班出身,但從本科到研究生都是中國畫專業(yè)。我知道,他當時的排異反應也比較強烈。我們在一起工作了一兩年,才漸漸進入了工作狀態(tài)。摸著石頭過河,與我們的作者們一起學習進步,通過差不多兩年的學習,漸漸知道了當代藝術的大致研究方向,并初步掌握了一些觀察和研究的方法。當然,這也是自我嶄新的知識結構和文化觀念的建構過程。這個過程很多時候其實是針對既往學習經驗的反思甚至自反的過程。從古典到當代,我們現在回想起來也覺得吃驚,真應該感謝《藝術當代》雜志這個平臺,讓自己的文化性格得以重塑。16年來,特別感謝當代藝術界同仁的支持,我們有幸與他們共同進步,共同見證了當代藝術的發(fā)展和變遷,與他們分享這個時代全新的藝術靈感和智慧成果——這確實是一種榮幸!
當:當代藝術的發(fā)展歷程中,藝術媒體占據了重要的地位。它不僅是當代藝術發(fā)展的見證者,有時甚至直接影響了當代藝術發(fā)展的方向。在您的從業(yè)經歷中,是否有發(fā)揮“媒體人力量”的經歷?比如以媒體人的身份參與藝術事件,或推介藝術家,改變了藝術家的事業(yè)軌跡?
徐:在起步階段,媒體人的意識是不太自覺的。當時我們出去參加活動或約稿,很謙虛甚至羞怯。漆瀾有點知識分子的清高,也不善于社交。并且,我們當時嚴格來說都是傳統(tǒng)主義者,甚至可以說有文化保守主義的傾向,這種傾向其實是一種交流障礙。張晴老師、楊荔老師給予了很多幫助。《藝術當代》的刊名是范迪安院長建議起的。當時許江、沈揆一、鄭勝天、魯虹、俞可、殷雙喜、王林、馮博一等許多老師給予了我們很多鼓勵和支持。很多重要的海外約稿都通過沈揆一、鄭勝天老師幫忙聯絡,沈揆一老師甚至親自為我們編譯海外資訊和展覽報道,當時我們稿酬非常微薄,沈老師完全是無私地幫助我們,現在想來太讓人感動。
這些前輩的工作熱情和嚴肅、認真的工作態(tài)度深深感染了我們。我們也逐漸越過觀念障礙,認真研究和借鑒他們自新潮美術以來積累的文獻經驗,這其實也是一種傳統(tǒng)。一本期刊,能否為當代藝術所承認,能否切中當代藝術的時效命題,能否真實的呈現當下的藝術生態(tài),能否在紛繁復雜的案例中選取出典型——這是我們嚴肅的課題,也是媒體人的責任和使命。
從2001年創(chuàng)刊,我們就強調對新形態(tài)、新媒材的推介和研究。這個傾向在當時的上海書畫出版社完全是一個全新的領域,當然,也很難被人理解。況且,當時當代藝術并沒有市場,從2001年至2005年,這五年時間非常艱難,我們甚至為能爭取到一次展覽主辦方的車旅費都不太容易。當時上海的藝術機構也處于起步階段,大家完全憑熱情做事情。對新媒體藝術的關注,我們是繼《江蘇畫刊》以后的另一陣地,一大批在這個領域有成就的新生代藝術家都在《藝術當代》發(fā)表過他們的早期作品或成名作品。
自2003年以來,我們一直非常關注中國當代架上繪畫,尤其關注具有東方書寫性的語言。“中國新繪畫”這個概念也是我們比較早提出的。2007年,在上海美術館我們舉辦了“超越圖像中國新繪畫”提名展,對這個概念進行了比較深入、系統(tǒng)的理論假設。實際上,之后幾年,這個概念已經逐漸被人們接受,引起人們對東方書寫語言的關注。這個概念本身就具有形態(tài)學和價值趣味的開放性,試圖在以往的“國畫”和“油畫”之間假設一種全新的通約方式,同時,也是對靜態(tài)的圖像復制、平面挪移的一種反駁。自2002年以來,我們在70后、80后畫家中陸續(xù)推薦了不少人才,尤其像張小濤、韋嘉、屠宏濤、賈靄力、李青、唐可等等,他們從一出道,《藝術當代》就持續(xù)關注他們,并在展覽中進行推介展示,目前,他們已經成為當代架上藝術的生力軍。

1 張云垚 低落 色粉石墨毛氈 116.5×112.5cm 20152016年第一屆藝術媒體提名展《藝術當代》提名作品
當:20世紀初,藝術網站興起,以海量的內容、強大的時效性、多元的視聽感受成為了藝術媒體中新興的巨大力量。而近幾年的新媒體形式上的便捷、內容上的風趣易懂,使藝術媒體逐漸多了一份風趣幽默、平易近人的氣質。《藝術當代》在2001年創(chuàng)刊,當時正是藝術網站開始興起的時期。在網絡時代誕生的《藝術當代》,在欄目編排、內容選擇上是否受到網絡文化的影響?與傳統(tǒng)老牌藝術媒體相比,相對年輕的《藝術當代》是否更能承受新媒體帶來的沖擊?
徐:可能受上海書畫出版社傳統(tǒng)文化性格的影響,《藝術當代》一直是比較嚴肅的,受網絡文化影響相對較小。我們的作者隊伍都是相對具有學術資歷的作者,寫作態(tài)度和文風也都是比較嚴肅的,講求文獻性,這跟網絡話語差距較大——這反而是我們自覺追求的。時效性、學術性、嚴肅性,這三點我們一直沒有放棄。當然,《藝術當代》也鼓勵實驗精神,甚至實驗性的寫作方式,對一些寫作比較有獨到性的稿件,即使存在一些缺點,也會放寬一些尺度而網開一面。當然,這樣的寫作成功案例實際上并不多,大概是2003年,韓東為毛焰寫的評論《其他及毛焰》就是一篇非常獨到的評論,寫作的文風與毛焰的繪畫氣質很匹配,語言有詩性的想象力,但同時又具有敏感的視覺經驗,這樣的文章很難得。
《藝術當代》已經進入第17個年頭,對于雜志來說,已經不再“年輕”——作為編輯我們也都快老了。當代藝術是一個發(fā)展變化的過程,并不是一種以風格、趣味為標志的群落劃分,這個過程的本質就是變化。因為研究對象是變化的,那么研究的方法和觀念,以及表達的媒介都得與之發(fā)生變化。這是新陳代謝的動態(tài)過程,在當代藝術領域,所謂的“老牌的”媒體是不存在的,如果一個媒體還存在,它肯定不是“老牌的”,而應該是不斷“新生的”。今天自媒體日益發(fā)達,我們都面臨空前的挑戰(zhàn),但回頭一想,只要具有新陳代謝的文化觀念,只要有足夠深刻的文化認知和鑒別能力,媒體的形態(tài)可以變遷,但媒體的功能、責任以及品質內涵,不會改變太多——我們還會一如既往地堅持下去,與當代藝術界共同進步。
當:有人認為藝術媒體是當代藝術的話筒、擴音器,您如何看?
徐:我這只能這樣說:在開始工作時,是因為對這個領域好奇。逐漸,我們越來越意識到,這個領域需要一種力量,需要一種想象的、或假設的自由發(fā)展、展示空間。同事漆瀾曾經這樣說,“以前我們的學識和工作經驗是知識考古性的,針對過去;現在,是新聞工作,還不僅僅是新聞工作,是在新聞工作中去發(fā)現和推導未來。”我比較認可他這樣的說法,這或許比話筒、擴音器的想法好一些。
當:80、90年代,當時的藝術傳播主要依靠紙媒,且媒體數量較少,幾大藝術媒體能比較集中地記錄當時藝術發(fā)展的情況,甚至直接影響藝術發(fā)展的進程。如80年代《美術》雜志對傷痕美術、鄉(xiāng)土美術的報道,雖與當時的政治因素不無關系,但在美術史上足以作為標志性事件。今天的藝術媒體百家爭鳴,豐富多樣,但這也意味某一家媒體的聲音有可能被淹沒。您如何看待今天藝術媒體發(fā)展的現狀?
徐:被淹沒很正常,但是,這種“被淹沒”的狀態(tài)也正是我們觀察和研究的對象。
聲音可能會被淹沒,因為眾聲喧嘩、信息普泛貶值——但我們很清楚,“知道”與“知識”、“信息”與“文獻”、“瀏覽”與“研究”之間永遠不可能劃等號。當信息泛濫時,知識的權威價值和中心價值被分化為多元,權威性也成為大眾文化消費的對象。人們在淺嘗即止、唾手可得的信息環(huán)境中很容易獲得知性的自信與滿足,這其實是消費文化景觀的假象,很具有欺騙性。這不是什么好事情,相反,非常有害,它阻斷了人們向真正理性、深刻發(fā)展的可能性,低分化地將人們的知性淹沒在廉價、普泛的信息海洋中,以至于窒息。出于這樣的現實,媒體的真正的責任是什么呢?其實,不用說了吧,我想大家也該清楚了。
當:在您看來,一家藝術媒體的生命力在于準確的讀者定位?嚴謹的學術態(tài)度?或是其他的因素?
徐:這兩個因素都很重要。但稍微補充一點,作為支持實驗精神的媒體,還有責任去爭取盡可能多的文化認可和支持,不能簡單地把讀者看成讀者,應該把他們看成可以交流的同道。實際上,作為實驗性的文化媒體,編者、作者、讀者,三位一體,自由創(chuàng)造的空間都是通過大家的共同想象而逐漸建構出來的。而讀者,是這個想象的文化空間的支持者和參與者,并且,他們占這個群體的絕大多數。
當:您對目前《藝術當代》的欄目設置、內容編排是否滿意?是否考慮轉型?
徐:目前我們常設的欄目有6個。“視點”是嚴肅的理論研究欄目,這個欄目的文章都是高品質的學術研究課題。16年來,我們曾經發(fā)起過多次專題討論,其中,很多命題在國內都是首次發(fā)起。這些重要的學術選題后來成為研究領域的參考文獻。這些文獻非常有價值,目前最明顯的就是,不少高校研究生的論文頻繁的采用和轉引這些文獻,這不容易!“個案”欄目是重要藝術案例推薦,這個欄目要求較高,具有藝術語言成就的藝術家才能進入這個欄目。16年來,這個欄目已經成為英雄榜,推薦了百余位70、80后實驗藝術及架上繪畫的重要藝術家,很多藝術家的首發(fā)就是在本刊。“現場”欄目負責時效性的重要展覽和活動報道。另外“生態(tài)”、“資訊”、“書蟲”三個欄目也各有明確的定位和分工。六個欄目共同構建了立體的報道和呈現視角。這樣的欄目設計也是反復摸索了好多年后確定下來的。目前運行效果比較理想,欄目相對穩(wěn)定,我們將工作重點放在對報道對象的發(fā)現、選擇和評介方面,此外還會花更多精力與作者交流,在寫作方式、呈現方式上做一些改進。特別是對微信平臺的轉發(fā)稿件,質量嚴格把關,為了照顧網絡閱讀,也在內容和版面上做了一些區(qū)別于平面發(fā)表的調整,目前收效還是明顯的。
當:最后請您談談藝術媒體行業(yè)吸引您的地方。
徐:作為編輯和記者,本人有幸在這16年中分享了當代藝術界的智慧成果,這些學術閱歷已經逐漸積淀出與當代藝術發(fā)展緊密相關的文獻價值。回顧16年的學習、工作歷程,深感欣慰。文獻性、學術性和時效性三條原則一直是《藝術當代》不改的初衷。本人與《藝術當代》雜志相伴而行,同步成長,見證了16年來中國當代藝術觀念和語言形態(tài)的嬗變,以及藝術生態(tài)的巨大變化。同時也在工作中結識了志同道合的工作伙伴,并成為知心朋友。這或許是做編輯最大的幸運——始終在第一時間了解甚至參與當代藝術觀念的變化與進步。
Marching with Art China
Xu Ke
Art China was established in 2001, always sticking tothe publishing guideline: highly specialty, high standard of academy,strong persuasiveness, also, it owns writer resources and editorial boardthroughout the world, which win itsellf a high reputation both homeand abroad. Xu Ke, chief editor, together with Art China has witnessed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and art media, since herentering in the industry of art media in 2001.
Contemporary art, Art med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