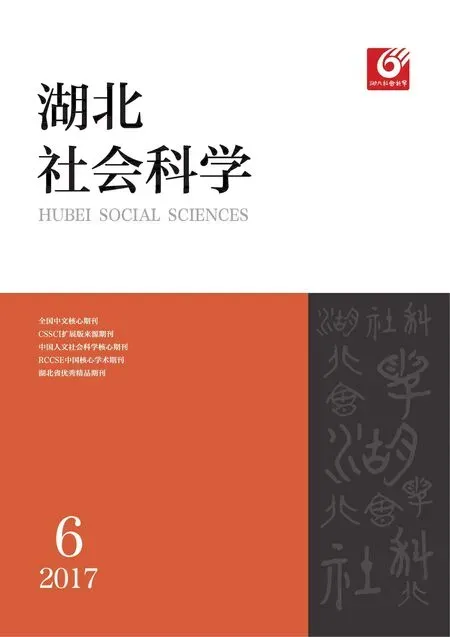觀念、話語、修辭:政治科學(xué)中建構(gòu)制度主義的三重取向
馬雪松
(吉林大學(xué) 行政學(xué)院,吉林 長春 130012)
·政治文明研究
觀念、話語、修辭:政治科學(xué)中建構(gòu)制度主義的三重取向
馬雪松
(吉林大學(xué) 行政學(xué)院,吉林 長春 130012)
新制度主義政治學(xué)近期的發(fā)展受到社會學(xué)、語言學(xué)較多影響,在處理結(jié)構(gòu)和能動性關(guān)系問題與制度變遷的內(nèi)生解釋問題時(shí)更傾向以建構(gòu)性而非結(jié)構(gòu)性或因果性的動態(tài)視角思考相關(guān)理論命題和動力機(jī)制。建構(gòu)制度主義以此為契機(jī)成為新制度主義政治學(xué)的新興流派,但其內(nèi)部包含各異的研究取向。通過借鑒新制度主義政治學(xué)觀念分析、話語分析、修辭分析的有益成果,汲取社會學(xué)、語言學(xué)特別是組織理論的洞見,建構(gòu)制度主義能夠?qū)⒂^念、話語、修辭進(jìn)一步內(nèi)化為其理論演進(jìn)的關(guān)鍵取向。
建構(gòu)制度主義;新制度主義政治學(xué);觀念;話語;修辭
新制度主義政治學(xué)自20世紀(jì)80年代正式興起以來,在其演進(jìn)歷程中持續(xù)拓展了制度分析的理論前沿,并就來自社會科學(xué)不同學(xué)科和研究領(lǐng)域的爭鳴商榷及質(zhì)疑批判進(jìn)行系統(tǒng)而深入的反思,由此逐漸成為當(dāng)代西方政治科學(xué)研究的主導(dǎo)范式。綜合審視新制度主義政治學(xué)的發(fā)展趨勢,可以發(fā)現(xiàn)各流派特別是其中活躍的研究者相較早期階段而言,呈現(xiàn)出愈發(fā)高漲的身份自覺意識、兼容并包的理論建構(gòu)取向以及不斷累積的現(xiàn)實(shí)解釋能力。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政治科學(xué)中的建構(gòu)制度主義從各流派分庭抗禮的格局中脫穎而出,并在推進(jìn)新制度主義研究領(lǐng)域擴(kuò)展和內(nèi)容深化方面取得可觀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