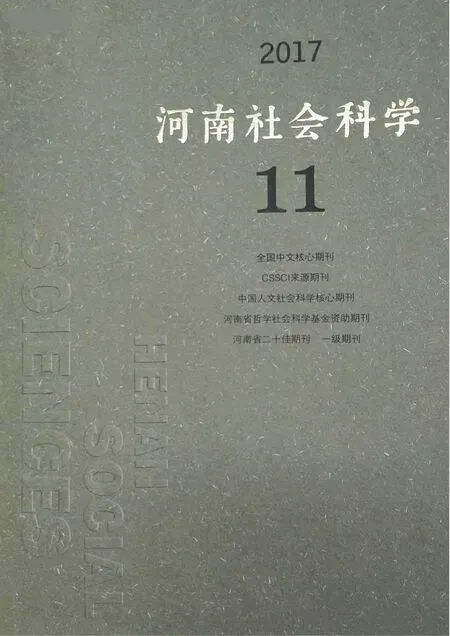“司馬光砸缸”的版本源流研究
鄭達威
(鄭州大學 新聞與傳播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2)
“司馬光砸缸”的版本源流研究
鄭達威
(鄭州大學 新聞與傳播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2)
以“司馬光砸缸”為研究對象,通過考證古代的歷史文獻與近代的小學教材,系統梳理橫跨千年的版本源流。在綜合與劃分各種文獻版本的基礎上,對“司馬光砸缸”的千年出版現象進行因果解釋。參考“司馬光砸缸”的研究結論,嘗試給出關于中國故事繼承和傳播問題的若干建議。
司馬光砸缸;中國故事;古代刻本;小學教材
一、研究緣起
“司馬光砸缸”的故事可謂家喻戶曉。這個故事始于北宋年間,之后代代相傳,橫跨千年。尤其是近代以來,科舉模式終結,現代小學教育興起,要求少年兒童的德、智、體全面發展;司馬光機智勇敢的少年形象很適合教育兒童,成為歷來小學課本的首選內容,影響更加廣泛。類似的中國故事很多,例如北宋時期著名政治家文彥博,官至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位極人臣,《宋史》有傳;后世記載他曾經有過“幼年之浮球”[1],近代以來的小學課本也曾收錄這個故事,中國郵政還于2010年6月1日發行《文彥博灌水浮球》特種郵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充分融入世界,一些來自西方文明的類似故事開始在中國廣泛傳播。比較著名的有“華盛頓砍櫻桃樹”“牛頓與蘋果樹”“莫扎特五歲譜曲”“愛迪生救媽媽”等,通過載入中小學課本或者課外讀物,廣為人知。一個應該注意的問題是:無論“文潞公幼年浮球”,還是后來的西方故事,知名度都不及“司馬光砸缸”。如此著名的歷史文化現象,很值得我們深入研究。尤其是在人人皆可“微出版”的移動互聯網時代,東西方文化彼此激蕩,相互交融,以“司馬光砸缸”為代表的中國故事不僅需要繼承,而且需要向世界傳播。因此,本研究不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緊迫性。
中國歷史源遠流長,綿延不絕,環顧世界,獨一無二。究其原因,一是具有記錄歷史和傳抄文獻的文化傳統,二是較早發明并應用了印刷術。兩者相互結合,構成了具有中國古代特色的出版傳播活動。在大眾媒介不發達的古代社會,“司馬光砸缸”的故事能夠流傳至今,各個歷史時期的出版傳播功不可沒。所謂出版傳播,是指“人類創作、編輯作品,經過復制公之于眾并被接收或接受的社會傳播現象(活動)”[2]。無論是官方的編輯出版還是民間的抄寫印刷,最后都保留下來大量珍貴的歷史文獻,成為本研究的關鍵依據和重要資料。本文將緊密圍繞記載“司馬光砸缸”的歷史文獻,梳理版本源流,探究其中原委。依據版本內容和出版媒介的不同,保存至今的歷史文獻可以分為古代刻本與小學教材兩大類。首先考證宋、元、明、清四個時期的古代刻本,然后考證晚清、近代直至現代的小學教材,辨析各個文獻版本的異同,歸納總結“司馬光砸缸”能夠實現“千年出版”的諸多原因,以此探究中國故事的繼承與傳播問題。
二、版本源流
(一)古代刻本
1.宋代的文人筆記兩則
宋代的文人筆記流傳廣泛,保存至今的為數不少,僅《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和小說類著錄的就有151部,其中有兩部記載了“司馬光砸缸”的故事,一個是北宋時期惠洪的《冷齋夜話》,載于卷三“活人手段”的目錄下,參考中華書局1988年版的點校本內容[3]:
司馬溫公童稚時,與群兒戲于庭。庭有大甕,一兒登之,偶墮甕水中。群兒皆棄去,公則以石擊甕,水因穴而迸,兒得不死。蓋其活人手段已見于齠齔中,至今京洛間多為小兒擊甕圖。
另一個是南宋時期羅大經的《鶴林玉露》,載于乙篇卷六“臨事之智”的目錄下,參考中華書局1983年版的點校本內容[4]:
小而文潞公幼年之浮球,司馬公幼年之擊甕,亦皆于倉卒之中,有變通之術。
以保存至今并面世的文獻版本來看,“司馬光砸缸”的故事內容發軔于《冷齋夜話》;后者被《宋史·藝文志》收錄于小說家類,屬于故事類型的筆記與詩話;后世認為此文獻版本的真實程度不高,語多非議。參考《四庫提要》和中華書局1988年版點校本,有如下總體評價:“然惠洪本工詩,其論詩實多中理解,所言可取則取之,其托于聞之某某,置而不論可矣。”《鶴林玉露》成書于南宋后期,主要記述宋代文人軼事,參考《四庫提要》和中華書局1983年版點校本,評價如下:“其體例在詩話、語錄、小說之間;其宗旨亦在文士、道學、山人之間。大抵詳于議論和略于考證。”由此可知,《冷齋夜話》和《鶴林玉露》皆屬文人筆記的性質,雖然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但是“司馬光砸缸”的真偽難以確定。
2.元代的民間記錄與官方元典
按照成書先后,元代的文獻版本分別是《言行龜鑒》和《宋史》。《言行龜鑒》作者張光祖的生平不可考證,《元史》無傳,從書序中可知《言行龜鑒》大致成書于元代大德年間,主要記錄古人的言行事跡,分為八卷,名曰八門,其中卷二的德行門中記錄了司馬光的言行事跡[5]:
司馬溫公童稚時,與群兒戲于庭。庭有大甕,一兒偶墮甕水中,群兒嘩然棄去,公即以石擊甕,水因穴而迸出,兒得不死。蓋其活人手段已見于齠齔中,至今京、洛間多為《小兒擊甕圖》。
《宋史》成書于元代至正五年(1345),由脫脫和阿魯圖先后主持修撰,是二十四史中篇幅最龐大的一部官修史書。《宋史·司馬光傳》以“司馬光砸缸”為開篇內容[6]:
群兒戲于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眾皆棄去,光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其后京、洛間畫以為圖。
參考《四庫提要》和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點校本,《言行龜鑒》的史料價值不高,被評價為“是編所記雖平近無奇,而篤實切理,足以資人之感發,亦所謂布帛菽粟之文,雖常而不可厭者歟”。再通過文獻內容的比對,顯然是直接抄錄自宋代的《冷齋夜話》。《宋史》篇幅巨大,成書倉促,歷來批評甚多。清代文人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用大量事實指出《宋史》列傳中存在回護、附會、錯謬、遺漏、失當等問題,但是涉及司馬光的僅有“駁夏竦謚”一事,尚未有文獻版本質疑“司馬光砸缸”。通過文獻內容的比對,《宋史·司馬光傳》應是對宋代《冷齋夜話》內容的刪減和凝練。盡管“司馬光砸缸”的真偽依舊難辨,但是載入元典的意義巨大,使得這個故事從此獲得權威地位。
3.明代的大型類書
明代暫有《山堂肆考》這一個文獻版本。《山堂肆考》目前僅有兩份善本傳世,是萬歷年間民間學者彭大翼編寫的大型類書,全書共240卷,其中卷一百八記錄了歷史上有關人品的各種神童故事,并有“以石擊甕”篇[7]:
《冷齋夜話》:司馬溫公童稚時,與群兒戲于庭,庭有大甕,一兒失足跌墜甕中,群兒皆棄去,公則以石擊,甕水迸出,兒得不死,蓋其活人手段已見齠齔中,至今京濟間多為小兒擊甕圖。
《四庫提要》認為《山堂肆考》“所收雖多,掇拾群籍,不盡采自本書,而網羅繁富,存之亦足備考焉”。作為類書,文獻內容明確指出取自《冷齋夜話》;再通過文獻內容的比對,與《冷齋夜話》差別不大。
4.清代的《四庫全書》
以上列舉的《冷齋夜話》《鶴林玉露》《言行龜鑒》《宋史》《山堂肆考》等文獻版本,皆收錄于《四庫全書》;《四庫全書》的目錄提要(上文簡稱為《四庫提要》)都有對以上文獻版本的內容評價。至此,“司馬光砸缸”古代刻本的源流正式結束。
(二)小學教材
資料顯示,至少從明代起,“司馬光砸缸”就被編入一些啟蒙讀物,作為“機智勇敢”的榜樣教育少年兒童,只是具體文獻版本不可考證。晚清時期,尤其是鴉片戰爭之后,中國開始近代化的歷程,古代刻本的出版模式終結,近代意義的印刷出版業勃興;“四書五經”的仕途經濟逐漸偏廢,經世致用的學校教育開始萌發。從高等教育到啟蒙教育,教學方式和教學內容都有翻天覆地的變革;小學教育不僅是讀書識字,還要兼顧德、智、體全面發展。2013年7月10日《中華讀書報》第14版發表了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姚穎老師的論文《百年語文教科書中的“司馬光砸缸”》,文中詳細考證了近代百年以來的小學教材,參考上述千年以來的古代刻本,結合當前國內的小學通用教材,現將該論文有關內容按照時間順序匯總如下[8]:
1.文言版本
近代意義的小學教材中,最早見于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十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最新初等小學國文教科書》第二冊,有一篇名為《司馬溫公》的課文:
司馬溫公幼時,與群兒戲庭前。有一兒,誤墜水缸中,群兒狂叫,皆驚走,溫公俯取石,急擊缸,缸破水流,兒得不死。
全文共43個字,基本是參考《宋史》的故事內容,而不是《冷齋夜話》,元典文獻的影響力可見一斑。需要注意的是,文中首次將甕改為缸,“司馬光砸缸”的故事名稱由此誕生;另外,還有插圖配合文字,《小兒擊甕圖》首次實現近代出版。此后,“司馬光砸缸”分別入選1912年出版的《最新國文教科書》,1921年出版的《共和國教科書新國文》第三冊,文獻內容基本遵從1905年的版本。
2.白話版本
1923年,中華書局出版《新小學教科書國語讀本》第三冊,篇名為《司馬光打破水缸》,首次以白話文來講述“司馬光砸缸”:
司馬光也是宋朝有名的人,他小的時候和幾個小孩玩耍,有個小孩爬到大水缸上,偶然不小心,失足掉在水缸里;大家嚇慌了,瞪著眼睛,沒有辦法。司馬光一想:水缸里有水,若不趕緊救他,恐怕就要淹死呀。他情急智生,隨即拾起一塊石頭,打破了水缸,終于使水都流出來了。
除了白話文之外,文獻內容增加了司馬光心理活動的描寫,直接寫出“情急智生”的故事主題。1929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新時代國語教科書》第四冊選入了“司馬光砸缸”,文獻內容與中華書局1923年版大同小異,都是白話文,只是沒有心理描寫。
3.童謠版本
1929年,世界書局出版的《新主義教科書前期小學國語讀本》第五冊有一篇名為《急智都稱司馬光》的課文,首次用童謠的形式出版“司馬光砸缸”:
草地上,捉迷藏。
墻邊有只大水缸,一兒爬到缸邊上;
撲通一聲響,跌在水中央。
缸既高,水又深,沒法可救落水人。
不要慌張不要忙,拿塊石頭敲水缸。
缸破水流兒不死,急智都稱司馬光。
1933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復興國語教科書》,在第四冊中出現了一篇名為《聰明的司馬光》的課文,同樣是以童謠的形式講述“司馬光砸缸”,文獻內容與世界書局1929年版本大致相同,只是細節更多演義,描寫更加生動,語言更趨白話。
4.復古版本
1947年新華書店出版的《初小國語》第四冊的課文名為《司馬光擊缸》,之前的課文通常是“砸”和“敲”,此處使用“擊”,回歸《宋史》元典記載的“光持石擊甕破之”。復古版本不僅是對元典的尊重,而且“砸”和“敲”的動作連貫,“擊”則是一次完成,更加符合司馬光機智勇敢的神童形象。文獻內容依舊是白話,同樣增加了孩子們的對話內容和動作描寫,渲染了危險、緊張的情緒和氣氛,營造了身臨其境的感覺。
5.當前版本
1949年以后,從五六十年代到80年代,直至90年代的小學教材,文獻內容都是白話,大多配有插圖;從90年代開始,《小兒擊甕圖》由黑白變成彩色。以當前全國通用的小學教材為例,人教版一年級下冊第20課,課文名為《司馬光》;蘇教版一年級下冊第22課,課文名也是《司馬光》;長春版一年級下冊第七單元“故事里的智慧”第二課,直接命名為《司馬光砸缸》。當前各種版本內容相近,形式多樣,為了順應互聯網的發展,以上列舉的小學教材都有電子版,甚至真人朗讀版。
三、歸納總結
按照時間順序:北宋的《冷齋夜話》首次提到“司馬光砸缸”,并有《小兒擊甕圖》的說法;南宋的《鶴林玉露》是對“司馬光砸缸”的評價;元代的《言行龜鑒》與《冷齋夜話》內容相近,《宋史》將“司馬光砸缸”正式編入《司馬光傳》;明代的《山堂肆考》直接取自《冷齋夜話》。以上五個文獻版本,一并收錄于清代的《四庫全書》。從晚清到民國,直至現代的小學教材,都是以元典《宋史》為模板,經過白話文的轉譯和演義,內容有所損益;《小兒擊甕圖》也延續至今,形式多樣,從黑白變成彩色。
從飽受爭議的《冷齋夜話》發軔,兩宋文人認為“司馬光砸缸”的性質為“活人手段”和“臨事之智”,元明時期拔高至“德行”和“人品”的層次。“司馬光砸缸”在古代從故事進入正史,在近代又從正史演義出新故事。小學教材無論是文言、白話還是童謠,故事主旨基本一致,故事結構大體一樣,大多配有不同樣式的《小兒擊甕圖》,只是細節稍有差異,比如“擊甕”變成了“砸缸”,增加了故事人物的對話、動作和心理描寫,目的都是有利于少年兒童的記憶和理解。對比古代刻本與小學教材的各個文獻版本,可以認定:“司馬光砸缸”屬于歷史事實不可考證的中國故事。
四、研究啟示
經過版本源流的梳理,雖然“司馬光砸缸”的歷史事實不可考證,但是從邏輯上推理,很明顯有兩個疑點:第一,“擊甕”為何變成“砸缸”;第二,司馬光兒時為何如此機智勇敢,家喻戶曉。先看第一個疑點:甕是一種窄口寬腹的容器,缸是一種寬口窄底的容器;登甕落水,甕的口窄,難以施救,只能“持石擊甕”,而擊比砸更加果斷有力;古代刻本的擊甕更能體現司馬光的機智勇敢,至于小學教材為何演變為砸缸,確切原因尚未可知,大概是“司馬光砸缸”比“司馬光擊甕”讀起來更加朗朗上口。再看第二個疑點:登甕落水之后,其他小朋友都驚慌失措,只有司馬光臨危不懼,實在令人疑惑不解,唯有稱其神童;尤其是家住現今信陽市光山縣的一個七歲兒童的家常事跡,竟然時隔不久就能傳遍東京和洛陽兩地,不僅難以考證,而且難以置信,其間是否存在人為因素呢?對于以上兩個疑點,后世深信不疑,并且不疑而傳,著實費解。后續研究應該從司馬光的生平事跡入手,結合北宋時期的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有可能得到某些佐證和合理解釋。
綜上所述,“司馬光砸缸”能夠實現千年出版,流傳至今,家喻戶曉,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首先,北宋時期印刷出版活動空前活躍,有利于故事傳播;其次,無論古代還是現代,這種“機智勇敢”的神童故事容易拿來教育少年兒童,以此獲得記憶和傳承;再次,“京、洛間畫以為圖”,類似現在大眾傳播的效果,《小兒擊甕圖》功不可沒。綜合以上三點,為了歷史傳承與全球傳播以“司馬光砸缸”為代表的中國故事需要做到以下三點:第一,深入挖掘故事的文化價值,擴大闡釋范圍;第二,參考世界各國神童故事的傳播方式,整合書籍、動畫、電影等各種現代出版媒介;第三,統一制定“中國故事戰略”,針對國內外的多元文化,強化中國故事的宣傳導向。中國故事還有很多,需要研究者廣泛參與,充分利用中國五千年的寶貴歷史資源,為現實服務,為社會服務。
[1]羅大經.鶴林玉露[M].北京:中華書局,1983:220.
[2]李新祥.出版傳播學的基本概念及其理論體系的提出[J].出版科學,2004,(5):35.
[3]惠洪.冷齋夜話[M].北京:中華書局,1988:31.
[4]羅大經.鶴林玉露[M].北京:中華書局,1983:220.
[5]張光祖.言行龜鑒[M].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17.
[6]脫脫,等.宋史[M].北京:中華書局,1982:10770.
[7]彭大翼.山堂肆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8]姚穎.百年語文教科書中的“司馬光砸缸”[N].中華讀書報,2013-07-10(14).
Study on the Version of Origin and Development about Sima’Story
ZhengDawei
Aimed at Sima’Story as the research object,the article teases millennial versions of origin and development systematically,through verifying both the ancient historical literature and the modern elementary school textbook.On the basis of synthesizing and dividing various literature versions,the article makes the causal explanation on the millennial publishing phenomenon of Sima’Story.Referred to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of Sima’Story,it attempts to give several proposals on the issues of inheriting and propagating Chinese story.
Sima’Story;Chinese Story;Ancient Photocopy;Elementary School Textbook
I2
A
1007-905X(2017)11-0105-04
2017-07-03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16BXW044)
鄭達威,男,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鄭州大學歷史學院2016級博士研究生。
編輯 張志強 張慧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