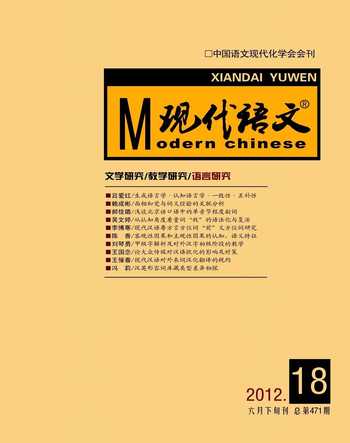淺談越南喃字與漢字之關系
2012-04-29 04:33:18楊垂楊
現代語文 2012年6期
關鍵詞:歷史
楊垂楊
摘 要:本文主要探討喃字與漢字的關系。越南從開始使用漢字到19世紀中期實行字母化,其間有一千多年歷史。這期間曾一度使用喃字作為越南正式文字。喃字是古代安南國家的文字。越南民族創制喃字,體現出了民族精神和思想,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本文主要探討喃字在漢字影響下是如何衍生的、喃字造字方法與漢字關系以及喃字消亡的原因。
猜你喜歡
小天使·一年級語數英綜合(2022年2期)2022-03-30 11:38:17
環球時報(2022-03-16)2022-03-16 12:17:18
作文大王·笑話大王(2019年8期)2019-09-09 07:34:21
全體育(2016年4期)2016-11-02 18:57:28
小天使·四年級語數英綜合(2016年9期)2016-10-09 22:40:45
科普童話·百科探秘(2015年6期)2015-10-13 07:21:18
科普童話·百科探秘(2015年9期)2015-09-22 07:36:52
科普童話·百科探秘(2015年8期)2015-08-14 07:13:06
科普童話·百科探秘(2015年7期)2015-07-25 07:42:53
科普童話·百科探秘(2015年5期)2015-05-26 07:2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