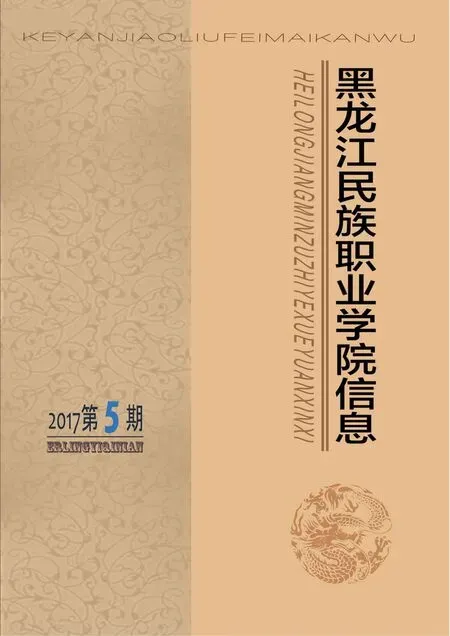黑龍江朵兒邊部的教育方式與特點
包玉林
(杜爾伯特文化研究會,黑龍江 杜爾伯特 166200)
黑龍江朵兒邊部的教育方式與特點
包玉林
(杜爾伯特文化研究會,黑龍江 杜爾伯特 166200)
黑龍江朵兒邊部是最早來到松嫩平原的蒙古部落。朵兒邊部在杜爾伯特草原上生活400多年間,經(jīng)歷了金、元、明三個朝代。金代,蒙古族沒有創(chuàng)立自己的文字,朵兒邊人主要用口傳心授的方法進行傳承教育。元代,東北地區(qū)普遍建有蒙古字學,朵兒邊人的后代開始學習蒙古文字。明代前期,在北元與明廷的長期拉鋸戰(zhàn)中,蒙古地區(qū)教育落后,但已經(jīng)有了家庭“榜什”教學。文章依據(jù)史籍記載和杜爾伯特努圖克人口耳相傳的史料,敘述明中葉前的朵兒邊人的民族起源、祖先譜系傳承教育和文字教育情況,分析其教育方式及其特點。
黑龍江;朵兒邊部;教育方式與特點
黑龍江朵兒邊部是最早來到松嫩平原的蒙古部落。朵兒邊部在嫩江中下游左岸生活的400多年間,經(jīng)歷了金、元、明三個朝代。金代,蒙古族沒有創(chuàng)立自己的文字,朵兒邊人主要用口傳心授的方法進行子女的教育。元代,東北地區(qū)普遍建有蒙古字學,朵兒邊人的后代開始學習蒙古文字。明代前期,北元與明廷長期拉鋸戰(zhàn),蒙古貴族封建割據(jù),蒙古地區(qū)教育落后,但已經(jīng)有了家庭“榜什”(老師)教學。
朵兒邊,蒙古文版的《蒙古秘史》記作“杜爾伯德”,漢文史籍卻記作“朵兒邊”。朵兒邊部,遼代形成于蒙古高原斡難河畔,是成吉思汗的第11世祖朵奔·蔑兒干的兄長都娃·鎖豁兒的四個兒子組成的部落。大約在金天會二年(1124年),經(jīng)一百多年的三次遷徙,來到了嫩江中下游左岸草原游牧。明代中葉(1547年)后,朵兒邊部被奎蒙克·塔斯哈喇的第八孫愛納嘎吞并,融入嫩科爾沁杜爾伯特部中。
下面就依據(jù)史籍記載和杜爾伯特努圖克人口耳相傳的史料,敘述明中葉前的朵兒邊人的民族起源、祖先譜系傳承教育和文字教育情況,分析其教育方式及其特點。
1 遼金時期的口傳心授教育方式與內(nèi)容
遼金時期的朵兒邊人的語言是古代蒙古語,由于沒有創(chuàng)立蒙古文字,民族歷史文化靠口述傳承。拉施特說:“蒙古人自古以來有保持(對)自己的起源和世系(記憶)的習慣。”[1]這是未創(chuàng)造文字前的各少數(shù)民族普遍使用的民族歷史文化的記憶傳承方法。
蒙古族是一個十分注重歷史文化傳承教育的民族,尤其像朵兒邊這樣的部落,在蒙古高原的部落兼并中顛沛流離,又在遼末金初的戰(zhàn)爭中遠離故土,更加重視民族歷史、祖先譜系的記憶,把對下一代的傳承教育當作了頭等大事。
1.1 神職人員“孛額”講述民族起源與祖先譜系
“孛額”是蒙古族原始宗教“孛額教”(清代后記作薩滿教,以下稱薩滿教)的神職人員。遼金時期,朵兒邊人信奉薩滿教。在部落里,孛額是薩滿巫師,主持祭祀禮儀,是醫(yī)師,給人治病,也負責歷史記憶教育。那一時期的孛額是世襲的,上一代孛額的民族歷史文化教育內(nèi)容,由下一代孛額爛熟于心,世襲后,便承擔起教育任務(wù)。
生活在嫩江中下游左岸的朵兒邊人,每年正月(又稱白月)初始日開始,部落首領(lǐng)和分支的貴族家庭將其子孫集聚起來,接受孛額的傳承教育。孛額在開講前,舉行隆重的祭祀儀式,擺供桌、上供品、燃草香,率領(lǐng)聽講者祭祀天地,祭祀祖先,然后再開講。講述的是一個個祖先故事,主要內(nèi)容是民族起源、祖先譜系、部落形成與遷徙路線及重大事件。連續(xù)講述三天,聽者必須牢記。由此方法,代代相傳。
從杜爾伯特努圖克人口耳相傳的史料分析,那時的孛額主要講述以下內(nèi)容:
第一,講述蒙古始祖“化鐵開山”走向草原的故事。很早的時候,蒙古人生活在高山峻嶺額爾古涅昆(大興安嶺)。后來人口越來越多,形成了18個部落,為了打開新天地,始祖孛爾帖·赤那帶領(lǐng)大家化鐵開山來到蒙古高原。關(guān)于這個故事,后來波斯史學家拉施特的記載最為經(jīng)典:“大約距今兩千年前,古代被稱為蒙古的那個部落,與另一些突厥部落發(fā)生了內(nèi)訌,終于引發(fā)戰(zhàn)爭。另一些部落戰(zhàn)勝了蒙古人,對他們進行了大規(guī)模的屠殺,使他們只剩下兩男兩女。這兩家人害怕敵人,逃到了一處人跡罕至的地方,那里四周唯有群山和森林,除了通過一條羊腸小道,歷盡艱難險阻可達其間外,任何一面別無途徑。在這些山中間,有豐盛的草和(氣候)良好的草原。這個地方叫額爾古涅昆。當這個民族在這些山里和森林里生息繁衍,(他們所占的)地域顯得日益狹窄不夠時,他們就互相商量,有什么好辦法可使他們走出這個嚴寒的峽谷和狹窄的山道呢?于是,他們找到了一處從前經(jīng)常在那里熔鐵的鐵礦產(chǎn)地。他們?nèi)w聚集在一起,在森林中整堆整堆地準備了許多木柴,宰殺了七十頭牛,剝下整張的皮做成了風箱,(然后)在那山坡腳下堆起木柴,安置就緒,使這七十個風箱一起煽起(火焰),直到山壁溶化。(結(jié)果)從那里得到了無數(shù)的鐵,(同時)通道也被開辟出來了。他們?nèi)w一起遷徙,從那個山隘里走出到原野上”[2]。
遼金時期,朵兒邊人每年除夕家家都要在門前攏一堆火,放進鐵塊,燒紅后,拿出來鍛打。這個習俗是他們對祖先開天辟地壯舉的敬仰與懷念,延續(xù)至今。
第二,講述始祖遷徙到肯特山后的繁衍故事。關(guān)于繁衍故事,實際上講的是祖先譜系。朵兒邊人的始祖是托諾依、多克新、額木尼克、額爾克四位兄弟,他們的祖先要從蒙古始祖講起。“奉天命而生的孛兒帖·赤那和他的妻子豁阿·瑪蘭勒,渡過大湖而來,來到斡難河源頭的不兒罕·合勒敦山扎營住下。他們生下的兒子為巴塔赤罕。巴塔赤罕的兒子為塔馬察。塔馬察的兒子為豁里察兒·蔑兒干。豁里察兒·蔑兒干的兒子為阿兀站·孛羅溫勒。阿兀站·孛羅溫勒的兒子為撒里·合察兀。撒里·合察兀的兒子為也客·你敦。也客·你敦的兒子為撏鎖赤。撏鎖赤的兒子為合兒出。合兒出的兒子為孛兒只吉歹·蔑兒干。孛兒只吉歹·蔑兒干的兒子為脫羅豁勒真·伯顏。脫羅豁勒真·伯顏的兒子為都娃·鎖豁兒、朵奔·蔑兒干”[3]。
第三,講述部落形成與遷徙的故事。關(guān)于部落形成,講的是都娃·鎖豁兒死后,他的四個兒子托諾依、多克新、額木尼克、額爾克與叔父朵奔·蔑兒干分牧,組成新的部落,“成為杜爾伯特氏,成為杜爾伯特部”。
后來,部落由肯特山一帶順著克魯倫河遷徙到貝爾湖周圍游牧,遼末越過大興安嶺遷徙到洮兒河流域,金初來到嫩江中下游左岸駐牧,這里開始稱杜爾伯德草原。
1.2 通過神話傳說進行歷史記憶教育
蒙古族口傳歷史的教育方式,一直到成吉思汗命塔塔統(tǒng)阿創(chuàng)制蒙古文字后還在流行。因為即使有了文字,學習與使用也局限于貴族和政府官員,絕大多數(shù)普通牧民不掌握文字。沒有學會文字的家庭,還是要用口傳方式進行民族歷史和祖先譜系的教育。這一方面,神話故事發(fā)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除了“冶鐵祭祖”的習俗和“化鐵開山”傳說外,朵兒邊人還有許多關(guān)于蒙古高原不兒汗山的故事,那是對故土的眷戀,是對祖先的懷念,也是蒙古族與自然災(zāi)害、社會邪惡勢力斗爭經(jīng)歷的反映。
“雄鷹與山丹”的傳說,講的是蒙古族少年英雄哈爾其嘎少布(山鷹)與未婚妻薩日郎琪琪格(山丹)為了保衛(wèi)家鄉(xiāng)、保護部落與三個惡魔即嘎倫蟒古斯(火魔)、楚侖蟒古斯(石魔)、烏孫蟒古斯(水魔)拼死搏斗,變成山鷹和山丹花的故事。“傳說在很早很早的時候,阿勒坦烏拉(金山)剛剛形成,蒙根高勒(銀河)水剛剛匯集成溪流的時候,道布莫爾根(成吉思汗第11世祖朵奔·蔑兒干)和阿倫高娃夫人(阿瀾·豁阿),率領(lǐng)著他們的部落屬民西遷,遷到額爾古涅河上游的寶兒罕山麓的草原扎寨。這里牛羊遍野,水草豐美,人丁興旺”[4]。這個故事中的人物、山水,都是祖先從阿爾泰山逃到大興安嶺的歷史記憶。
“奧蘭琪琪格的傳說”,講的是朵兒邊部的三王子額爾尼克與不兒汗哈勒敦(肯特山)山神奧蘭額真的女兒奧蘭琪琪格的愛情故事。《蒙古秘史》開篇就說:“奉天命而生的孛兒帖·赤那和他的妻子豁埃·瑪闌勒,渡過大湖而來,來到斡難河源頭的不兒罕·合勒敦山扎營住下”。“奧蘭琪琪格的傳說”,就是委婉地講述了祖先西遷后駐牧地的這一史實,告訴后人有關(guān)朵兒邊部的起源。雖然故事中充滿神話色彩,奧蘭額真運用魔力再三刁難三王子額爾尼克,但從愛情的夢想成真中卻清楚地述說了遠離故土,生活在杜爾伯特草原的朵兒邊人尋根問祖的愿望,反映了朵兒邊人心系蒙古高原的情懷。“他們夫婦二人一路奔命,造就的大自然一直留存至今:你看那兩面鏡子變成的呼倫湖和貝爾湖,由木梳和胭脂變成的大興安嶺和大森林,由篦子變成的蘆葦蕩,還有那綠腰帶變成的嫩江,至今還是湖面如鏡,松濤作響,蘆花競放,江水流長”[5]。此故事竟將朵兒邊部一遷之地呼倫貝爾和三遷之地杜爾伯特草原也說得清清楚楚。
朵兒邊部第一任酋長是四兄弟的長兄托諾依。“托諾依”的故事和“杜爾伯特的傳說”,就是朵兒邊部始祖托諾依組成杜爾伯德部落的傳說,充滿了朵兒邊人對蒙古高原的親情,也深刻地表達了他們不怕千難萬險,追求幸福和歡樂的向往。“托諾依”講述的是朵兒邊部酋長踏遍草原尋求幸福之路的途中,遇見了巴彥草原一個溫雅、嫻靜的禿發(fā)牧羊姑娘的故事。為了幫助這個苦命的姑娘,托諾依來到了故鄉(xiāng)的神山不兒汗哈勒敦,遠走柴達木和孫布爾山,問遍了頭人、長老(孛額)、安達、額吉,尋找長黑頭發(fā)的秘方。最后,托諾依的誠意感動了善良的牧羊姑娘,姑娘長出了黝黑的長發(fā),兩個有情人終于套鞭結(jié)緣,篝火拜天,結(jié)為伴侶。“然后,他們雙雙乘馬,趕著他們的畜群,沿著腦溫江(嫩江)向南走去。從此,腦溫江東畔的杜爾伯特草原上,托諾依夫婦生兒育女,飼養(yǎng)牛羊,過上了幸福的日子”[6]。
來到嫩江中下游左岸后,朵兒邊部已成為金國屬民,部落首領(lǐng)、薩滿巫師或有關(guān)幕僚有可能掌握一些金國文字,因為在金國統(tǒng)治下,政治、經(jīng)濟的社會交往,需要“筆貼士”,即文人。后來,蒙古族也有了自己的文字,但口述歷史,記憶文化的傳統(tǒng),一直流傳至今。
2 元代的蒙古字學與教育方式
蒙古文字創(chuàng)立于1204年。此事,記錄于《元史》:“塔塔統(tǒng)阿,畏兀兒人也,乃蠻太揚汗掌印官。太祖西征,乃蠻國亡,就擒。帝善之,命居左右,是后凡有制旨,始用印章,仍命掌之。帝曰:‘汝深知本國文字乎?’塔塔統(tǒng)阿悉以所蘊對,稱旨,遂命教太子諸王以畏兀字書國言”[7]。這里的“國言”系指蒙古語。“迄今發(fā)現(xiàn)的最早的畏兀兒蒙古文文獻是1225年的‘成吉思汗石’。其次是1246年貴由汗所使用的璽書,1257年的‘釋迦院碑記’”[8]。這些文獻說明,畏兀兒體蒙古文已經(jīng)在蒙古帝國中普遍使用。那時,東道諸王帖木哥·豁赤斤的勢力已發(fā)展到東北地區(qū),朵兒邊部在其及后裔諸王的控制中,朵兒邊人開始接觸蒙古文字。
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六年(1269年)下令創(chuàng)制新字,畏兀體蒙古文不再是元朝的官方文字,而代之以“八思巴”蒙古文字。忽必烈雷厲風行,詔頒行天下,大力推進新國字的教育工作,中央設(shè)蒙古國子監(jiān)學,地方普遍設(shè)蒙古官學。朝廷在至元六年“秋七月,置諸路蒙古官學。十二月,中書省定學制頒行之”。主要招收“諸路府官員子弟”及“民間子弟”,政府向他們提供相應(yīng)的條件,學成者,出任官員[9]。元廷還設(shè)置蒙古翰林院為諸路蒙古字學的最高管理機構(gòu),蒙古提舉學校官是蒙古字學的地方管理機構(gòu)。“遼陽行省當于這個時期,在浦峪路、肇州等10個萬戶府,烏裕爾、兀良哈、古州等3個千戶所,塔察爾城、乃顏城、明安倫城等地設(shè)置了蒙古文字學校”[10]。 “八思巴”蒙古新字成了國字,自然政府行文、驛站關(guān)押、官府印信乃至私人印章都用八思巴文字。“但是,畏兀體蒙古文并沒有完全被遺棄,有元一代,曾經(jīng)有不少用這種文字寫下的金石、手抄和木刻文獻。在民間更是一直只用畏兀體蒙古文”[11]。
元代,朵兒邊部確實使用過八思巴蒙古新字。2002年8月,杜爾伯特縣他拉哈鎮(zhèn)哈拉海村一位農(nóng)民在哈拉海古城遺址處拾到一枚古印章。印章為黃銅質(zhì),通高(紐殘)1.1厘米,重量8.28克,印面呈長方形,長2.7厘米,寬2厘米,厚0.2厘米,陽面鑄八思巴蒙古文,印背無款識,印紐呈梯形,頂部有一穿孔,長0.9厘米。此印章經(jīng)內(nèi)蒙古大學齊木德道爾吉教授、包祥教授、黑龍江省民研所波·少布研究員等考證,為元代地方小官員的收簽押印,印文用字為八思巴文,曰“涉勒”。所以,又稱“元押”或“涉勒押”。元代蒙古人一般不用姓氏,只用名字,估計“涉勒”是一個蒙古族底層小官員的名字。哈拉海古城址緊鄰嫩江左岸,根據(jù)出土文物和文獻記載,該城為遼代所建,金代肇州所轄,元代沿用,隸屬元朝遼陽行省,是嫩江中下游地區(qū)遼、金、元時期具有一定規(guī)模的城堡,也是南北交通的重要驛站之一。此印說明,至元代,哈拉海古城仍有官衙,一個叫涉勒的地方官員在這里負責收取稅賦,并用八思巴文“元押”。
“元押”的使用,反映了那一時期朵兒邊部的文字學習情況。地處東北邊遠之地的朵兒邊部底層小官員“涉勒”,收繳實物稅賦要用八思巴文印章,說明元朝政府推行國字八思巴文的力度很大,效率也很高。那時,可能朵兒邊部的封建領(lǐng)主、同姓貴族以及那些大小官員們都學會了八思巴蒙古字。底層小官員要面對普通牧民,也許此時富裕一些的牧民也都認識了八思巴蒙古字,普及程度還好。
“元代蒙古人的教育形式可歸納為三種:一是家庭教育,二是私塾教育,三是官學教育。”[12]根據(jù)史籍關(guān)于元代黑龍江地區(qū)教育情況的記載,可知朵兒邊部也許已經(jīng)設(shè)立了類似于“貴族子弟”的蒙古字學。黑龍江“蒙古字學招收學生的范圍包括路、府、州、千戶所官員子弟以及民間子弟。官員子弟每路2人,每府、州、千戶所各1人,民間子弟上路30人,下路25人,散府20人,上、中州15人,下州10人。元貞元年(1295年)后,給予學生優(yōu)厚待遇,學生入學后免一身雜役。”[13]學生享受半供給制,官方給予學生飯費,有利于學生讀書。地方學校路、府、州蒙古字學均設(shè)教授,路教授正八品,府、州教授從八品,大德四年(1300年)后添設(shè)學正1人。當時,諸學校使用的文字均是八思巴蒙古文。“至元六年(1269年)農(nóng)歷七月,朝廷下詔‘立諸路蒙古字學’以后,黑龍江地區(qū)10個萬戶府、3個千戶所、3個城,相繼都成立了蒙古字學。每府蒙古字學學生26人,每州、城蒙古字學學生11人。黑龍江地區(qū)10個萬戶府共有生員260人,6個所、城共有生員66人,總計326人。除此之外,萬戶府達魯花赤、萬戶、副萬戶的子弟讀完府學后可以到京都蒙古國子學深造。”[14]統(tǒng)一了中華大地的元帝國,以包容天下的胸懷教育蒙古族子弟。體現(xiàn)在具體辦學上,就是蒙古字學教學與漢字教學相結(jié)合,并把儒家學說納入教學領(lǐng)域。在黑龍江地區(qū),“一般情況下,大多數(shù)學生在二、三年內(nèi)讀完《三字經(jīng)》、《百家姓》、《千家詩》、《千字文》、《大學》、《論語》,學會應(yīng)用的字,得到一些儒學知識”[15]。根據(jù)這些朝廷規(guī)定和史料記載可知,那時的朵兒邊人的子弟應(yīng)該受到同樣的學校教育。
除了官學之外,私塾也是元代蒙古族教育的重要形式。“私塾教育,是指私人創(chuàng)辦的學校或眾人捐資興辦的義塾。它與家庭教育所不同之處是,家庭教師只教授一個家庭的子女,而私塾或義塾的教師要教授幾個家庭或十幾個家庭的子女,并且具有類似學校的專門教授場所,即學校。元代黑龍江地區(qū)在沒有建立官學之前,有的萬戶府的達魯花赤就曾組織建立過私塾,使本萬戶府所有官員的子弟入學讀書。元代并不禁止官學以外的其他辦學形式,1291年(至元二十八年)朝廷規(guī)定‘自愿招師,或自授家學于父兄者,亦從其便。’政府并不限制家庭教育與私塾教育”[16]。
根據(jù)以上元代黑龍江地區(qū)教育情況的記載,可知家庭教育、私塾教育、官學教育等三種教育形式,在朵兒邊部的教育中,一定會有具體的體現(xiàn)。朵兒邊部是元代黑龍江地區(qū)一個重要的蒙古部落,部落內(nèi)有一定文化素養(yǎng)的人,大多掌握八思巴蒙古文和畏兀兒體蒙古文,有些人還掌握漢文。
3 明代的學校教育與家庭“榜什”教學
忽必烈命國師西藏薩迦派喇嘛八思巴創(chuàng)制的元朝國字,本來缺少群眾基礎(chǔ),民間很少用。隨著元朝滅亡,“八思巴”蒙古字也消失了,畏兀體蒙古字又開始盛行。從明代史料得知,在明代的東北地區(qū),蒙古文字是官民通用文字,可見蒙古文教育受重視與普及情況,也是蒙古一統(tǒng)天下100多年的結(jié)果。
明初,明廷多次北伐,戰(zhàn)爭頻繁,草原罹難。明中前期,東西蒙古相互間連年征戰(zhàn),之后,蒙古本部各封建主割據(jù)一方,都想“挾天子以令諸侯”。這一時期,蒙古社會處在空前的動蕩與混亂之中,經(jīng)濟迅速萎縮,文化更是明顯衰退,元代時期的官學、蒙古字學也早已蕩然無存,但朵兒邊人的畏兀體蒙古字的家庭教育并未中斷。
朱元璋說:“兵變以來,人習戰(zhàn)爭,惟知干戈,莫視俎豆。朕惟治國以教化為先,教化以學校為本”。“洪武二年(1369年)詔天下府、州、縣皆立學”[17]。 “根據(jù)這一規(guī)定,我們可以得知黑龍江地區(qū)的奴兒干都司和福余、朵顏、泰寧、撒叉河等衛(wèi),也應(yīng)在洪武十七年,即1384年以后的時間里分別建立了都司儒學和衛(wèi)儒學,比南方的府、州、縣晚建學校15年。”[18]洪武十七年閏十月二十七日,“置遼東都指揮使司儒學,設(shè)教授一員,訓導四員。”[19]“我們從遺留下來的一些史跡中看到,明代社會對蒙古文的應(yīng)用面很廣,說明明代蒙古文教育還是很發(fā)達的,特別是在奴兒干都司境內(nèi),蒙古文一直是社會通用的文字。福余、朵顏、泰寧、撒叉河等衛(wèi)向朝廷呈送的文書以及朝廷下達的訓令,均用蒙古文書寫。就連女真人的衛(wèi)所,與朝廷的公文往來以及社會交際,也都通用蒙古文”[20]。隨著金國滅亡,在劇烈的社會變革中,“正統(tǒng)年間東北女真人已全部拋棄了舊有的女真字,改用蒙古字了”[21]。 “15世紀中葉女真字已失傳,而借用蒙古文字”[22]。正統(tǒng)九年(1444年)玄城衛(wèi)指揮撒升哈等向朝廷奏請:“臣等四十衛(wèi)無識女真字者,乞日后敕文之類,第用達達文字”[23]。所謂“達達文字”,即蒙古文字。我們從東北女真各衛(wèi)所通用蒙古文字的記載可知,明代的東北地區(qū),蒙古、女真的各衛(wèi)所一定都有蒙古文教育的學校。
明代的蒙古社會中,掌握文字的人,仍然是社會上層人物,即大小封建主及貴族階層。學校教育與家庭教學,主要是這些封建主及貴族家族子女的事情。當然,有一定勢力或有一些財產(chǎn)的中等家庭,有的雖然不是貴族,也十分重視子弟教育,或到學校或聘請家庭教師教授子女,因而,這些家族的子弟也都具有一定的文化修養(yǎng)。阿勒巴圖中的稍有能力的人家,即使聘不起家庭教師,也會想方設(shè)法把自家子弟送到貴族家庭伴讀。
家教老師稱“榜什”,他們也是部落諾顏官府的文字工作承擔者,很受人尊重。榜什即使不能躋身封建主之列,但也處在平民的上層。榜什“隨酋首往來,列于諸夷上一等。以故夷中最敬榜什,法有侮慢榜什者罰馬一匹以給之”[24]。可見明代蒙古社會對知識分子的尊敬,對教育的重視。“榜什,是寫番字書手;筆寫契,是寫漢字書手”[25]。 “榜什”,也記作巴克什,是教師之意;“筆寫契”,也記作筆帖什,是書記員之意。顧名思義,榜什是教育工作者,筆寫契是文書工作者。榜什和筆寫契在那個時代自然都擔當著翻譯工作,看來那時,為了政治、經(jīng)濟、文化交流需要,已經(jīng)有懂漢語漢文的人為部落諾顏服務(wù)了。榜什和筆寫契的出現(xiàn),反映了那時以翻譯為主的蒙古與漢文化交流現(xiàn)象。“1407年(永樂五年),明成祖于四夷館內(nèi)設(shè)蒙古、女真等八館,‘置譯字生、通事,通譯語言文字’。這些譯字生、通事中有很多是蒙古人,他們?yōu)闇贤蓾h兩個民族做了大量工作”[26]。這些政治、文化現(xiàn)象必然逐步影響到杜爾伯特地區(qū),也許,那時的學校教育與家教,已開始有少量的漢字教學。
明代,朵兒邊部的榜什的家教工作主要是教授蒙古文字,除貴族家庭為官府培養(yǎng)官吏人才(筆寫契)外,一般的普通人家的家教,不學漢文。據(jù)明代史料記載,畏兀體蒙古字教學是榜什家教的主課。最晚在明中期,蒙古地方已有了蒙古文的教科書,叫《忠經(jīng)》和“夷字《孝經(jīng)》”,[27]說明那時蒙古族子弟啟蒙教育已漸規(guī)范,也說明蒙古族啟蒙教學還是十分重視忠孝教育的,注重文字教學與思想品德教育相結(jié)合。榜什家教如同漢地私塾,學生不論歲數(shù)差別,三、五個或十來個聘一榜什成一私塾。王公子弟必須學習蒙古文字,貴族家庭的女孩子也可讀書。雖然蒙古社會中,女子地位也如中原那樣比男子低下,但不像內(nèi)地那樣“女子無才便是德”。游牧經(jīng)濟中,女人需要承擔很多繁雜的家內(nèi)外勞動,因而在家庭中有一定的地位,且受尊重。
那時,紙張匱乏,只能用粗糙的黃色薄紙,大多數(shù)人家都用羊皮或木板代替。書寫工具叫“烏朱格”,是用竹子或木板削制成的,多用竹子,把筆頭削平,成方狀,不成尖。早先,蒙古文都是用“烏朱格”書寫的,用毛筆是引進漢文化的結(jié)果,因此,那時書寫筆還是很容易解決的。
明代的蒙古部落諾顏家有最好的榜什家教,旁系貴族家庭也都可依據(jù)財力聘請榜什。然而,無能力聘請榜什的家庭,多有識字的父母居家教孩子即父傳子承或母傳子承。也許有手抄本的課本,也許沒有課本,但都要先教授《查干套魯蓋》。《查干套魯蓋》,也稱《阿爾本·浩伊日·套魯蓋》,可譯為“十二字頭”,也就是蒙古文字母的啟蒙識字課本。無論戰(zhàn)亂還是和平時期,無論富有人家還是貧窮人家,父傳子承的家庭教學,是蒙古社會最普及、最基礎(chǔ)的教育方式。因為它是最簡單、最容易,也是最有效的,且存在了相當長的時期。
教育古已有之,也無處不在。最初的教育活動與人類的生產(chǎn)活動與社會生活融為一體,人們主要是通過言傳身教,傳授知識和技能。朵兒邊人與其他蒙古人一樣,即使沒有條件讀書的家庭,也十分注意子孫教育。首要的是生存技藝教育與實踐。游牧與狩獵生產(chǎn)以及戰(zhàn)爭環(huán)境,需要蒙古男兒從小學會騎射,騎射是蒙古人最主要的本領(lǐng)。趙珙在《蒙韃備錄》中記載:蒙古人“騎射則孩時繩束以板絡(luò)之馬上,隨母出入。三歲以索維之鞍,俾手有所執(zhí),從眾馳騁。四五歲狹小馬短矢。及其長也,四時業(yè)田獵”[28]。還要諳熟畜牧業(yè)、狩獵業(yè)生產(chǎn)技術(shù),學會騎射、摔跤、廝殺、搏斗。道德教育更是必不可缺的教育。蒙古家庭特別注重對子女的道德教育,歷來有圣母“折箭訓子”的傳統(tǒng),成吉思汗的第11世祖母阿闌·豁阿、母親訶額侖這兩位圣母都有“折箭訓子”的故事流傳。蒙古族把尊長敬老、撫幼愛子當作社會美德,尤其是強調(diào)家族團結(jié),對朋友要忠誠信義,從貴族到普通人,都格外講究,若有違背,必遭重責,嚴重者還要懲罰。
[1][波斯]拉施特·艾丁.史集[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6(1):34.
[2][波斯]拉施特·艾丁.史集[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6(1):251-252.
[3]余大鈞譯注.蒙古秘史[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3-7.
[4]波·少布.黑龍江蒙古族民間故事[M].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2005:13.
[5]波·少布.黑龍江蒙古族民間故事[M].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2005:8.
[6]波·少布.黑龍江蒙古族民間故事[M].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2005:4.
[7]宋濂.元史:卷一百二十四[M].北京:中華書局,1976.
[8]孫竹.蒙古語族語言詞典[M].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61.
[9] 宋濂.元史:卷八十一[M].北京:中華書局,1976.
[10]波·少布.黑水蒙古論[M].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2004:123.
[11]義都合西格主編.蒙古民族通史[M].呼和浩特:內(nèi)蒙古大學出版社,2002(2): 350.
[12]波·少布,烏云達來.黑龍江蒙文教育史[M].哈爾濱:黑龍江朝鮮民族出版社,2004:31.
[13][明]宋濂.元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6(81):2028.
[14]波·少布,烏云達來.黑龍江蒙文教育史[M].哈爾濱:黑龍江朝鮮民族出版社,2004:33.
[15]黑龍江教育史研究課題組.黑龍江教育史: 征求意見稿上[M].2001: 67.
[16]波·少布,烏云達來.黑龍江蒙文教育史[M].哈爾濱:黑龍江朝鮮民族出版社,2004:32.
[17]張廷玉.明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275):17-203.
[18]波·少布,烏云達來.黑龍江蒙文教育史[M].哈爾濱:黑龍江朝鮮民族出版社,2004:44.
[19]明太祖實錄:卷一百六十七[Z]:2563.
[20]波·少布,烏云達來.黑龍江蒙文教育史[M].哈爾濱:黑龍江朝鮮民族出版社,2004:45.
[21]金光平,金啟孮.女真語言文字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31).
[22]季永海.試論滿文的劃制和改進[J].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1(3).
[23]明英宗實錄:卷一百一十三[Z].
[24]瞿九思.萬歷武功錄:卷十四·切盡黃臺吉傳[M].
[25]王士琦.三云籌俎考·夷語解說[M].臺北:臺北廣文書局出版,1963.
[26]義都合西格主編.蒙古民族通史:卷三[M].呼和浩特:內(nèi)蒙古大學出版社,2002:403.
[27]明英宗實錄:正統(tǒng)六年正月甲子[Z].
[28]王國維.蒙韃備錄箋證:遺書十三冊(16)[Z].
[責任編輯寶玉]
2017-07-25
包玉林(博彥賀喜格),1949-,男,蒙古族,黑龍江杜爾伯特人,黑龍江省民族研究會副理事長、黑龍江省蒙古學研究會理事長、杜爾伯特文化研究會理事長、《杜爾伯特文化》主編、黑龍江省民族研究所特聘研究員,蒙古族歷史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