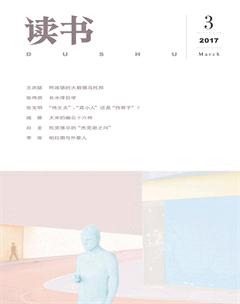學者的本分
胡成
學術研究的要旨,在于知識創新意義上的發現和發明。就其成敗得失來看,如果套用托爾斯泰的那句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那么似可以說成功的學者都很相似,不成功的學者各有各的煩惱和傷心。一般說來,學術上能夠成功之人,是在正確的時間里研究正確的問題,需要天賦、訓練、勤奮,當然還要有點運氣。這就注定只有極少數人能夠脫穎而出,成為學術研究的佼佼者。畢竟,在未知世界里的探索,前面充滿了太多不確定性,大多數人終生只是在黑暗中跌跌撞撞,雖廢寢忘食,夜以繼日,卻不見得能有收獲。一句自我解嘲和安慰的話,是耳熟能詳的:“只問耕耘,不問收獲。”當然,有幸做出點成績者大有人在。不過,倘若不能進入學術史意義上的“發凡起例”,或者說帶來科學革命意義上的“范式轉換”(paradigm shift),那點成績也只是為他人建造巍峨大廈增磚添瓦。這就像吾人進到北京故宮,首先映入眼簾而贊嘆不已的,是炫麗的房頂、威嚴的大殿、堂皇的拱門、挺拔的圓柱;不會有多少人注意修造這些建筑所用的一塊又一塊的青磚綠瓦。
好在,終生以學術為業之人,多多少少都有些病態的自戀情結。即使生不逢時、身處逆境,也沒有太多想到知難而退。這猶如古希臘神話里的美少年納喀索斯,對于自己在水里的倒影,愛慕不已、難以自拔;否則,如何能長年累月、不離不棄地堅持下來。就此吾人可以舉出太多經典事例。一個頗為生動形象的說法,是一九四九年發明避孕藥的美國化學家卡爾·杰拉西(Care Djerassi, 1923-2015)在其回憶錄所言:“扮演學術成員妻子的角色簡直糟糕透了,同一個每天工作長達十六個小時,每天晚上都把自己的‘情人帶回家去的科學家一起生活,絕對是難以忍受的。”(卡爾·杰拉西:《避孕藥的是是非非》)
由此說來,學術生涯確如馬克斯·韋伯所說是“一場瘋狂的冒險”,多數人注定一無所獲,失意而歸。這是韋伯在其人生最后一年,即一九一九年,為慕尼黑大學學生所做的《學術作為一種志業》講演中之所說。他語重心長地質問那些年輕學生:“你能夠年復一年看著平庸之輩一個接一個爬到你的前面,而既不怨懟也無創痛嗎?”那個時代的德國大學制度,對于投身于學術研究的年輕人,規定從除講課費之外而無薪水的編外講師做起。韋伯的家境相當優渥,不在意講課費。他最初在柏林大學開設商法和羅馬法課程,選修的學生數量太少,其中有一位還是走錯了教室。由于第一次上課,至少得有兩三位學生選修,韋伯請這位學生將名字留在選修名單上,并承諾退還十個芬尼的聽課費。逮至韋伯發表這個著名講演時,他在德國學術界還沒有得到普遍承認,也沒有多少學術影響力。所以,在他所謂學術生涯是“一場瘋狂的冒險”的講述里,很難說沒有自己心理不平衡和受挫感的投射。
就中國當下的語境來看,韋伯的這一質問怕還有實實在在物質生活上的羞澀和失落。畢竟,中國大陸目前的大學薪酬制度,采行的是“競賽制”,教授分為“基底工資”加“崗位津貼”的四個等級。雖沒有統計數字說這個基底工資是否為全球最低,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僅此而已,幾乎所有學者都無法過上體面的生活。作為補償,當政者設計了在基底工資之上幾倍于此的“崗位津貼”,評定標準是所謂數字化的“績效考核”。再有所謂“長江學者”“特聘”“資深”“學術帶頭人”等五花八門的評選,都與獲得者的實際收入聯系在一起。各種評比的結果無非是“水落石出”,同一專業教授之間的收入形成不少于幾倍的懸殊。作為參照,歐美、日本、新加坡,乃至中國香港和臺灣等地,學者薪水是“達標制”,除了少數講座教授,只要拿到“永久教職”,同僚們薪酬水平是相差不多的“水漲船高”。即使是諾貝爾獎獲得者,學校也不會額外給其任何經濟補貼。所以,當下大陸的“不成功”學者,最終如果能夠堅持下來而不至于魂不守舍,一定比當年的韋伯更能經受住各種“折騰”。
人生的坎坷和困蹇,本來就不只是單一負能量。尤其上天賜予學者的一小點睿智,是普通人對不幸多默默承受,而他們則能咀嚼、回味、反思,乃至言說自己的傷痛和苦惱。就像尼采把思想者稱為“有病的動物”,認為人的尊嚴只在感受巨大痛苦的精神之中—即痛苦使靈魂敏感,當靈魂不愿屈服之時,意志愈加激昂,思想也就愈發活躍。實際上,孟子在兩千多年前說的“天將降大任于斯人”,就已經表達了同樣的意象。古代學人作為自由職業者,運蹇時乖而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可將自己不為當下接受的創世之作,“藏諸名山,傳之其人”。然而,現代學者作為職業研究人員,參與的是一種集眾的工作。他的任何研究都需要經過同行仔細驗證,以及學術共同體的認真審查,故不太可能“朝聞道夕死可矣”。重要的是,“不成功”的學者置身底層和邊緣,較多發憤之作,難免沒有一點離經叛道,自然比成功的學者更期待一個能夠鼓勵自由表達意見,公開交換觀點的外在寬容環境。
除此之外,“不成功”學者還應比成功的學者,更注重學術共同體的內在環境。這也是因為現代意義上的學術研究,注重同僚之間的合作與競爭。誰也不會否認,與杰出之人作為同事相處,可能將永不停止地追求卓越;如果周圍都是些平庸之人,則會讓自己變得乏味而無生氣。這也可以理解當年的韋伯,盡管很長時間里辭職而離開大學,卻時刻關心學術共同體的堅持和恪守。一九○八年他在《法蘭克福報》刊發文章,尖銳批評普魯士教育部大學事務部門將曾在地方大學任教之人,擅自任命為柏林大學經濟學正教授。韋伯認為這一任命不合法,在于踐踏了十九世紀德國業已確立的大學教師聘任的自治傳統。因為讓當局反感的一位學者占據了教授職位,執事者會懲罰性地任命另一位迎合政府之人,在學者之間制造矛盾和爭斗。韋伯稱其為“懲罰教授”,并認為鑒于個體責任感和團體自尊感,是學術繁榮和大學正常運作及其發揮社會作用的前提和條件;當局不尊重大學里的自治傳統,也就是不尊重學者通過同行評議和審核而選擇同事的應有權利。韋伯擔心會在年輕學者中培養出一種投機取巧、見風使舵的市儈精神,誘使他們走向為權力效勞而謀求“出人頭地”的提升捷徑,致使大學充斥著一批喪失獨立人格,為謀取現實利益而蠅營狗茍的人—所謂的“生意人”或“工匠”(馬克斯·韋伯:《貝恩哈德事件》,見《韋伯論大學》)。
我不揣淺陋地講這些,是想讓那些“不成功”學者,或那些將要毅然步入這一“瘋狂的冒險”之年輕學人,能有稍微多一點的從容不迫和氣定神閑。面對那么無奈的現實世界,學者最重要的責任或許不是拯救這個世界,而是首先設法拯救自己。既然盡了自己的本分,肯定擁有一個自由的靈魂;縱使在職業生涯結束之時,吾人仍然無所建樹,壯志未酬,那又何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