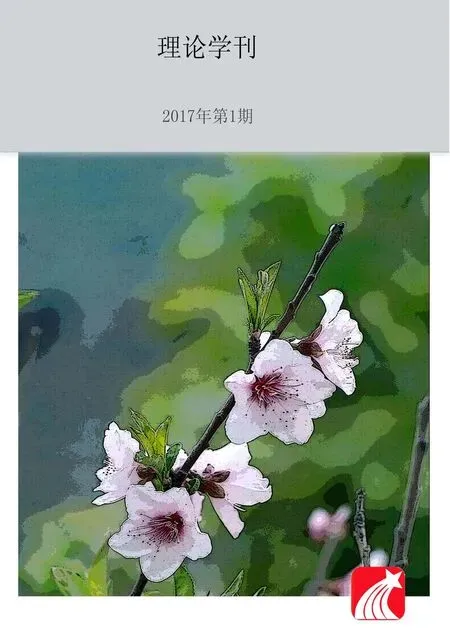“中國特色資本主義論”辨析
臧秀玲,王增劍
(山東大學當代社會主義研究所,山東 濟南 250100;山西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山西 臨汾 041000)
“中國特色資本主義論”辨析
臧秀玲,王增劍
(山東大學當代社會主義研究所,山東 濟南 250100;山西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山西 臨汾 041000)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種特殊形態的社會主義,是以市場經濟而非產品經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形態。從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來看,由于政策的扶持,非公有制經濟得到了長足發展,但在所有制結構中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發揮主導作用的格局沒有改變,國有經濟的實力、效率、影響力和控制力反而得到較大提升。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極大地增強了我國的國家實力,有利于實現社會主義的本質和目標。發展混合所有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有企業改革進一步深化的必然要求和有效路徑,也是實現社會主義公有制與市場經濟有機融合的重要途徑,不僅不會導致國有資產私有化,反而會進一步增強我國國有企業的主導地位和作用。更重要的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確保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正確方向的根本保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公有制為主體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又為不斷縮小貧富差距、防止兩極分化成為常態提供了制度保障。 〔關鍵詞〕中國特色;市場經濟體制;所有制結構;收入分配;混合所有制
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一直是各界人士關注的熱點,國內外有一部分人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性質始終持懷疑態度,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只是個旗號,其實蘊涵著資本主義的性質,與其稱之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還不如說是“中國特色資本主義”。例如美籍華人、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黃亞生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質是中國特色資本主義,其基本根據就是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改革和發展實踐中利用了資本主義的一些東西,比如市場經濟、私有經濟、股份制、外資企業等;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和人民的福利距離越來越遠,收入分配不均,基尼系數過高,中國社會貧富差距日益嚴重*Yasheng Huang,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tat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p.276.。在國內,這種觀點也有一定的市場。持這種觀點的人,其主要依據大致有四條:一是認為搞市場經濟就是搞資本主義;二是認為中國所有制結構中非公有制經濟成分已占半壁江山,實際上是資本主義經濟;三是認為中國貧富差距拉大,出現了兩極分化這種資本主義特有的現象;四是認為對國有企業實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實質上是搞私有化。對此,我們必須旗幟鮮明,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進行科學辨析,以便澄清是非,廓清認識,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一、辨析之一:搞市場經濟就是搞資本主義?
發展市場經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個偉大創舉,由此形成的市場經濟體制被稱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然而在現實中,總有一些人忽略“社會主義”,只提“市場經濟”或“市場經濟體制”,不認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他們看來,市場經濟只能屬于資本主義制度的范疇,將市場經濟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相結合是不可能的。還有一些外國學者認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其實是資本主義的一種形態,并將其稱之為“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階段”或“國家資本主義階段”*徐覺哉:《國外學者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08年第3期。。
說中國走了資本主義道路的人,往往把中國發展市場經濟作為論據,認為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的特有范疇,而沒有看到市場經濟只是發展生產的方法和調節經濟的手段,并不屬于基本制度的范疇,而屬于體制及運行機制范疇。是否實行市場經濟,并不說明一種社會制度的性質,因為社會性質是由社會基本制度決定的。只要這一市場經濟是服務于社會主義制度的,那么它就不屬于資本主義范疇。1992年初,鄧小平在南巡談話中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③ 《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369頁。鄧小平的上述論斷,對于統一黨內思想、推動我國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型起了重要的理論支撐作用,理論界的相關探討也主要以這些論斷為依據。當前,雖然人們仍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存在各種質疑,但已不再集中于計劃與市場的關系,而是重點關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資本問題。
市場經濟不僅代表著發達的商品交換,還代表著資本是這一經濟形態中社會化大生產的主要組織力量。由此有人指出,既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允許資本,那么就一定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對于這一質疑,單純圍繞計劃與市場關系以及市場經濟的手段性進行回應已遠遠不夠,應進一步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處的歷史方位來解釋為什么要發展市場經濟與資本的問題,否則就會掉入各種邏輯陷阱。比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是伴隨市場經濟與資本力量的擴張而發展起來的,所以不少人立足西方國情將中國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視作復辟資本主義。再如,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提出的代替資本主義的共產主義社會(包括第一階段和高級階段),是以市場經濟與資本的消亡為基本特征的,所以也有不少人認為搞社會主義就必須消滅市場經濟與資本。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當資本主義制度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并為共產主義所代替時,市場經濟將過渡到產品經濟,組織社會化大生產的力量也由資本轉變為自由人聯合體。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作為共產主義社會同義語的社會主義社會只與產品經濟相容,而與市場經濟、資本等范疇不相容。既然如此,為什么鄧小平反復強調“要把什么叫社會主義搞清楚,把怎么樣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搞清楚”呢③?實際上,他所說的“沒有搞清楚”并非指馬克思、恩格斯未弄清楚經典意義上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特征,而是指經濟文化落后的現實社會主義國家沒有搞清楚如何持續發展本國的社會主義問題。在此基礎上,鄧小平認為建設社會主義“根本一條就是發展生產力”,對于經濟文化落后的中國來說,任何有利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舉措都是有利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在當前資本有利于促進生產社會化、市場經濟有利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情況下,培育資本、發展市場經濟就成為經濟文化落后國家搞社會主義的應有之義和“不可逾越的階段”*《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參見中共中央文獻文獻研究室:《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476頁。。實際上,馬克思早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一文中,就立足商品交換關系的發展揭示了人類社會經濟形態與社會形態演進的一般規律:經濟形態將由商品交換關系處于從屬地位的自然經濟階段,發展到占主導地位的市場經濟階段,再到處于消亡狀態的產品經濟階段;而分別以自然經濟、市場經濟、產品經濟為基礎而形成的三大社會形態,也將隨著經濟形態的演進而依次更替。在商品交換關系的發達階段,勞動力商品化與資本雇傭勞動成為普遍現象,所以在馬克思所生活的時代,第二大社會形態特指資本主義社會,但二者并非等同,正如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項啟源所說,第二大社會形態是要揭示“發展到這種程度的交換關系的基本特征,而不是強調這樣的交換關系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更不是講什么‘資產階級社會的一般特征’”*項啟源:《馬克思恩格斯對社會形態演進的研究》,《當代思潮》2001年第2期。。而第三大社會形態則是指共產主義社會,包括它的“第一階段”與“高級階段”,盡管這兩個階段實行的分配方式不同,但均實行產品經濟。反觀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脫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自然經濟和半自然經濟占相當比重,若要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中間需要一個市場經濟的充分發展階段來為其創造前提,而不可能跨越市場經濟階段向產品經濟直接過渡。
總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本質上屬于經濟文化落后國家,特別是現實社會主義國家對經濟規律的探索。這一探索不僅是總結社會主義實踐經驗的結果,也受到經典社會發展理論的啟發。所以,搞市場經濟與發展資本不一定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它們同樣為經濟文化落后的現實社會主義國家(包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需,并服務于社會主義。從這一意義上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種特殊形態的社會主義,是一種以市場經濟而非產品經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形態。
二、辨析之二: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就是發展資本主義經濟?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非公有制經濟迅速發展,目前占GDP的比例已超過70%,稅收貢獻超過70%,對就業崗位的貢獻超過80%,占企業總數的比例超過80%。有人據此認為,現在中國的經濟制度已經是以私有制為主體了,發展了資本主義經濟,走了資本主義道路。國外一些學者也認為,中國目前的私有制已經超過公有制,而且是“不可逆的”,將導致“徹底的資本主義復辟和日益嚴重的外國經濟控制”*Martin Hart-Landsberg and Paul Burkett,China and Socialism: Market Reforms and ClassStruggle,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2005,pp.1~12.。對此,我們需要加以辨析,以澄清認識。
我國的公有制經濟包括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以及混合所有制經濟中的國有和集體資本。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通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調整優化經濟結構、形成創新驅動型經濟的相關政策措施,切實增強了國有經濟的影響力和控制力,不僅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處于優勢地位,更為關鍵的是國有經濟對國民經濟命脈的控制力增強。公有制經濟居于優勢地位、國有經濟發揮著主導作用,不僅是中國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的本質特征,也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不偏離社會主義方向的根本保障。目前,我國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國有經濟比重下降,但運行效率、經濟總量相對提高,對國家的貢獻率逐年增長。以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為例,“2015年末,國有資產總額119.2萬億元,凈資產40.1萬億元。2015年,全國國有企業實現營業收入45.5萬億元,實現利潤總額2.3萬億元,稅金3.9萬億元。國資委直接監管的106家中央企業資產總額47萬億元,凈資產15.9萬億元,職工人數1247.9萬人*《央企六成資產分布在五行業》,http://news.eastday.com/eastday/13news/auto/news/china/20160313/u7ai5403425.html。。從全國國有企業情況來看,據財政部統計,2014年1—12月,我國全國國有企業營業總收入達到4480636.4億元,同比增長4%;利潤總額24765.4億元,同比增長3.4%;應交稅金37860.8億元,同比增長5.7%*《2014年1—12月全國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經濟運行情況》,http://qys.mof.gov.cn/zhengwuxinxi/qiyeyunxingdongtai/201501/t20150121_1182847.html。。
第二,國有經濟數量明顯下降,但實力、影響力和競爭力不斷增強。尤其是黨的十六大確立新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以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和國有經濟布局的戰略性調整,國有經濟在國內外市場上的活力、控制力和影響力進一步增強。2015年,中國企業500強的59.5萬億元營業收入中,293家國有企業的營業收入為46.6萬億元,占中國企業500強的78.3%,納稅額占到88.7%*《2015中國企業500強發布》, http://news.xinhuanet.com/energy/2015-08/22/c_1116339452.htm。。一批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不僅是國內行業排頭兵,在國際市場上也有很強影響力,一批大型國有企業已成為與跨國公司競爭的主要力量。
第三,國有經濟分布范圍有所收縮,但牢牢掌控著涉及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目前,國有企業主要布點于事關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領域或者市場失靈的公共領域,如中央企業60%資產分布在電力、石油石化、建筑、軍工和通信五大行業,而只要“國有經濟在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占支配地位,支撐、引導和帶動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在實現國家宏觀調控目標中發揮重要作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8頁。,中國就能通過強有力的宏觀調控有效克服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實現社會公平與共同富裕,體現社會主義的性質及其優越性。
從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來看,由于政策的扶持,非公有制經濟也得到長足發展,但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發揮主導作用的格局沒有改變,國有經濟的實力、效率、影響力和控制力反而得到較大提升。中國的經濟改革沒有改變中國的社會主義方向,相反,國有經濟、集體經濟、民營經濟、外資經濟等各自發揮長處、共同發展,極大地增強了我國的國家實力,有利于實現社會主義的本質和目標。
三、辨析之三:貧富差距拉大就是搞資本主義?
黃亞生等人認為,當前中國嚴重的貧富差距是中國走向資本主義的重要例證。在辨析這一觀點之前,不妨先關注一個有趣的例子,即“奧巴馬的社會主義”。2008年,奧巴馬競選美國總統時提出的“財富均沾”綱領被美國人貼上“社會主義宣言”的標簽,“奧巴馬是社會主義者”的論調在美國廣為傳播*③ 榮筱箐:《如果奧巴馬開始社會主義》,《中國新聞周刊》2009年第14期。。那么,奧巴馬真的是社會主義者嗎?他真的是要“革”資本主義制度之“命”,進而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嗎?顯然不是,即便奧巴馬本人也對《紐約時報》記者聲明“自己是自由市場的忠實信奉者”③。
實際上,奧巴馬之所以被認作“社會主義者”,無非是因為他積極推動醫療改革、建立惠及全民的醫保體制,以及倡導對富人增稅、使其承擔更多社會責任。在醫保方面,美國是世界上中唯一不提供全民醫保的發達國家,新的醫療改革將促使3300萬人受益*孟亞波:《奧巴馬醫療改革法及其影響》,《國際資料信息》2012年第8期。,約占總人口的10.5%。在對富人增稅方面,所征資本利得稅已由2009年的15%上升到2013年的20%,奧巴馬還計劃將稅率進一步提高到28%*盛媛:《奧巴馬再提向富人征稅 助力2016年大選》,http://www.yicai.com/news/2015/01/4065119.html。。其實,28%的稅率并非奧巴馬的創造,而是20世紀90年代美國資本利得稅的稅率,奧巴馬只是將其恢復到了原來的水平而已。由此可知,無論從奧巴馬本人的主觀意愿,還是從改革新政的實效來看,上述舉措并非要撼動美國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制度,只是通過調整收入再分配政策縮小貧富差距、促進社會公平。而對于社會主義的判斷標準,很多人僅僅停留在價值觀念——社會公平的層面,并未考慮制度體系。受這一觀念的影響,不僅奧巴馬倡導社會公平被認為是“搞社會主義”,而且中國當前出現的嚴重貧富分化,也被部分人看作“搞資本主義”的結果。
資本主義在發展過程中出現過嚴重的貧富差距問題,我國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過程中,在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同時也產生了一定程度的貧富分化現象。兩種現象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從根本原因、發生機理和發展方向上存在明顯不同。導致我國現階段出現收入分配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是經濟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使然,又是我國市場經濟的個性特征使然,還是我國面臨的特殊情勢使然。其一,經濟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使然。19世紀以來,各國工業化的進程表明,每個國家在由傳統經濟向現代經濟飛躍過程中,都會經歷一個收入分配的分化與問題叢生的階段,其貧富差距攀升是普遍存在的現象,西蒙·庫茲涅茨對此有過深入研究,并提出了庫茲涅茨曲線理論。從我國實際情況看,20世紀80年代以來,伴隨國民經濟的持續增長,居民收入差距也呈現出不斷擴大的趨勢。截至目前,我國經濟增長與收入差距的這種相關性,與倒U曲線基本一致。其二,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不健全使然。如企業制度不完善、市場體系不健全、政府干預過多,法律、法規、政策不完善等。其三,我國面臨的特殊情勢使然。我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地理條件非常復雜,在經濟層面容易形成各種差距。如我國不同區域在自然稟賦、人文素養以及區位優勢方面存在巨大差異,這種差異導致各地對經濟資源的吸附力不同,自然引發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
毫無疑問,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本質的體現,消滅人與人之間的階級差別乃至勞動差別、實現人人平等,是社會主義的最終奮斗目標。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進程中,共同富裕一直居于特殊重要地位。鄧小平提出,公有制占主體與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②③ 《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364、111頁。,“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②。在傳統模式社會主義實踐的基礎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結出一條重要教訓,即共同富裕只有建立在生產力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上才是可能的,并且在不同發展階段,共同富裕的實現程度要與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相適應。
正是立足生產力發展在實現共同富裕中的基礎性作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開始變革了以往單一的公有制結構,鼓勵并支持各種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釋放其在發展社會生產力方面的活力與積極性;在資源配置方式方面,也拋棄了行政指令型計劃,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通過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與優化組合來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些改革舉措在刺激生產力發展的同時,也隱含著社會成員之間必然出現貧富差距的事實。從所有制結構看,公有制經濟內部存在企業高級管理者與基層員工的收入差距,非公有制經濟內部存在企業主、高級管理者與基層工人之間的收入差距;從市場參與者的角度看,生產經營者之間所掌握市場信息的差別、經營管理水平的差別,以及所掌握生產要素的質與量的差別,勞動者之間所提供的勞動質量與數量的差別,勞動成果在市場中被認可程度的差別等等,都決定了收入分配的多層次性甚至收入差距的擴大。所以,在非公有制經濟并未成為生產力發展桎梏、市場仍然是資源配置有效方式的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能實現的共同富裕還屬于低層次的,還是一種不均衡的、社會成員間仍存在較大收入差距的富裕。當前收入調節機制的不健全、不成熟,也對貧富分化的擴大起到了推動作用。鄧小平曾講到,“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③。在這里,鄧小平所講的“失敗”是指兩極分化成為一種社會常態;為避免這種常態以及中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鄧小平重點強調了兩大制度保障:一是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中國共產黨牢牢掌握社會主義政權。公有制經濟在制度設計上具有促進共同富裕的重要優勢。以國有經濟為例,近年來國家提高了國有企業上繳利潤比例,十八屆三中全會又決定到2020年將這一比例提高到30%,并主要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這種國民共享企業利潤的特質是非公有制經濟所不具備的,體現了國有經濟在促進共同富裕方面的比較優勢。而中國共產黨只有牢牢掌握政權,才能掌握改革的主動權,才能為不斷縮小貧富差距而引領和推動改革,特別是不斷健全和完善收入調節機制。十八大以來,官員非法收入在高壓反腐態勢下受到遏制,國有企業高管高薪機制得到規范;社會保障制度也不斷取得新進展與突破,城鄉居民醫保制度逐步并軌,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已全面啟動,在人民群眾共享發展成果的同時,也更加注重促進社會公平。最新數據表明,從2013—2016年,我國城鄉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數已呈現出微小下降的趨向。
總之,中國的特殊國情以及當前時代的局限性,決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中出現的貧富分化現象有其客觀必然性;同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公有制為主體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又為不斷縮小貧富差距、防止兩極分化成為常態提供了制度保障。所以,認為當下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擴大就是搞資本主義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
四、辨析之四:國有企業實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就是搞私有化?
黨的十五大第一次提出了“混合所有制”這一概念,十六大將“混合所有制”具體釋義為“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等參股”,《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將其界定為“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②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日報》2013年11月16日。。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再次強調,“鼓勵非公有制企業參與國有企業改革,鼓勵發展非公有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業”②。對此一些人產生了誤解或惡意曲解,將混合所有制改革等同于推行私有化,在此我們有必要加以澄清,弄清中國國有企業實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實質和目標。
混合所有制是社會基本經濟制度在企業層面的重要實現形式,“屬于中性的概念,并未表明某一社會所有制結構或某一企業經濟制度的基本屬性”*郭飛:《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與國有企業改革》,《光明日報》2014年4月2日。。事實上,基本經濟制度與其實現形式是兩個不完全等同的范疇,后者只是前者的實現形式,而并非基本經濟制度本身。將“混合所有制”作為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一是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并不是要從根本上改變我國基本經濟制度,而是對基本經濟制度借以實現的途徑進行方式方法上的變革;二是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方向和目的是更好地實現、維護基本經濟制度,進一步鞏固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促進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發揮主導作用,從而實現共同富裕的終極目標。
首先,發展混合所有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有企業改革進一步深化的必然要求和有效路徑,也是實現社會主義公有制與市場經濟有機融合的重要路徑。通過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夠使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協調發展,遵循市場經濟規律,通過市場化運作充分動員和利用勞動力、技術、資本、管理等各種資源,并最大限度地發揮其作用,從而不斷增強國有經濟的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和抗風險能力。其次,發展混合所有制是國有企業明晰產權、健全國有企業法人治理結構的必然要求。長期以來,我國國有企業產權模糊、股權單一的現狀導致國企生產效率低下,市場嗅覺遲鈍,決策盲目無序,國有資產嚴重流失,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實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就是要在明晰國有企業產權的基礎上,形成和健全國有股權與非國有股權相互制衡與監督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這是提升國有企業效率效益以及避免國有資產流失的有效方式,也是促進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更好發揮主導作用的有效途徑。再次,發展混合所有制是實現政府職能轉變、理順政府與國有企業關系的必然要求。一方面,混合所有制改革要求政府轉變對國有企業的管理理念和方式,由對企業的管理轉向對國資的管理,放手國有企業的經營管理權,更多著眼于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另一方面,要求政府對國有企業的股權設置進行頂層設計和整體把握,決定哪些領域必須國有控股,哪些領域國有資本可以參與也可以控股,哪些領域必須國有獨資等,從而確保國有企業的主導地位和控制力不會因與民營資本混合而削弱。通過改革,不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公有制性質不會發生根本變化,而且私人資本還會因企業員工持股的規模化而進一步被社會化,形成資本和勞動者利益共同體,促進生產資料的非私有化。
國有企業實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不僅不會導致國有資產私有化,反而會進一步增強我國國有企業的主導地位和作用。首先,在國有企業實行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夠促進國有資本的保值和增值。國有資本、民營資本和外資交叉持股,各種資本合理分工、優勢互補、相得益彰,通過合作發展逐步實現國有資本的保值增值,創造更大的經濟效益。其次,國有企業實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利于國有經濟競爭力的提高。通過各種資本的混合,打破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中的形式主義,形成更加完善、科學的治理結構和現代企業制度,從而提高國有企業效率和競爭力。據國家統計局歷年公布的統計數據,2013、2014、2015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分別為62831億、64715.3億、63554億元,其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實現利潤總額分別為15194.1億、14006.7億、10944億元,股份制企業實現利潤總額分別為37285.3億、42962.8億、42981.4億元。可見,混合所有制的競爭力將會大大高于單純國有企業的競爭力。國有經濟競爭力的提升不僅體現于國內,還外溢于國際市場當中。2015年中國大陸進入世界500強的企業數量達到了106家*《2015財富世界500強榜單:中國106家企業上榜》,http://news.163.com/15/0723/10/AV6VE6AO0001124J.html。,其中除了幾家國有獨資公司外,多數為混合所有制企業*黃速建:《中國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經濟管理》2014年第7期。。再次,國有企業實行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夠放大和拓展國有資本功能。事實上,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的控制力與影響力,并不僅僅表現在與非公經濟成分的比重上,而主要表現在國有資本的功能與影響力。混合所有制通過擴大國有資本的支配范圍來放大國有資本功能,吸收、調度、整合社會資本,充分發揮對民族經濟的影響力和推動力。在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國有資本通過產權轉讓、兼并重組、增資擴股等多種方式,引導非公資本以混合所有制形式參與國有企業經營,在極大地激活國有資產流動性和盈利能力的同時,也借助混合所有制這一平臺將國有資本的資源、品牌優勢與民營資本的靈活性、創造力等優勢有機結合起來,催生更高發展水平、更具世界影響力的民族企業集團,發揮對民族經濟的影響力和推動力,增強國有經濟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帶動作用。
更重要的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確保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正確方向的根本保障。2015年7月5日,中共中央審議通過的《關于在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中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的若干意見》強調指出:“把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要堅持黨的建設與國有企業改革同步謀劃、黨的組織及工作機構同步設置,實現體制對接、機制對接、制度對接、工作對接,確保黨的領導、黨的建設在國有企業改革中得到體現和加強。”強化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深入探索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將企業黨組織和現代企業制度有機結合的有效方法與途徑,不僅能夠使國有企業黨組織的政治優勢轉化為企業的核心競爭力,而且能夠保證國有企業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不會變質,這是確保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改旗易幟、不走私有化之路的根本前提。
五、基本結論
通過上述對“中國特色資本主義論”的理論辨析,使我們錘煉了思維、廓清了思路,進一步澄清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模糊認識,更加堅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總結全文,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結論:
第一,把握普遍與特殊的辯證關系,切實理清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性與民族特殊性、社會主義本質與表現形式之間的關系。社會主義本質是對社會主義原則要求的最高度凝練與概括,體現的是社會主義最充分發展的應然,由于其抽象性,可以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方向要求,但不能作為衡量實然的精準標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符合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又遵循中國國情,是理論邏輯與實踐邏輯、歷史邏輯與現實邏輯的統一,是合目的性與和規律性的統一。歷史已經雄辯地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發展中國、穩定中國的必由之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色是社會主義,根本不是其他什么主義,更不是國家資本主義和中國特色資本主義。“中國特色”指的是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具體實現形式,不是否定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是與社會主義本色一致的特色。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向前推進,特色與本色之間的色差會逐漸縮小。
第二,把握本質與現象的辯證關系,切實認清兩種制度在現代化大生產規律上的同質性與異質性之間的關系。社會主義與當代資本主義作為兩種社會制度,在本質上有著原則的區別,是根本對立的兩種社會制度。但二者在現象層次上卻會有共同點和相似性。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共處于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遵循著共同的市場經濟規律,因而在經濟社會的局部表現上存在著相同性與相通性,比如都遵守市場規則,都有積極探尋并運用現代的經濟運行機制、科學的經濟管理模式,都積極開發以信息化為根本特征的現代科技,在政治層面也相互借鑒,形成具有一定關聯度的民主政治與社會治理模式。但是,我們更應當看到,二者之間的局部表象類似并不能否定他們之間的整體本質差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由道路、理論體系、制度三位一體構成的,三者統一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如果借口我國同資本主義國家在具體管理方法、經濟運行層面上具有某些共同的東西,就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中國特色資本主義”,這就犯了只看現象不看本質的錯誤。
第三,把握對立與統一的辯證關系,切實認清兩種制度之間存在的“必然代替”和“必須利用”的關系,既充滿信心,又留足耐心。社會制度的演進與文明的更迭是連續性與繼承性、斷裂性與創新性的辯證統一,任何社會都是在某種形式繼承的結果。從社會主義的使命上看,是對資本主義的取代,但是從社會主義的產生上看,又是對資本主義的繼承。資本主義用不到一百年的時間創造了比以往任何時代都要多的生產力。生產力的大發展為無產階級的壯大奠定了基礎,無產階級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后必須充分借助已有生產力,大力借鑒資本主義的一切文明成果。繼承是為了超越,利用是為了壯大自身。社會主義只有學會利用資本主義,才能真正超越資本主義,才能更具生命力、感召力,才能必然代替資本主義。當然,我們學習、借鑒資本主義的文明成果決不是要照搬資本主義基本制度,而是取其所長,為我所用,以有益于改革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我們要借鑒的是資本主義文明中那些有益的、能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具體制度、方法手段、運行機制以及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而非那些維護資產階級政治統治和根本利益的東西。因此,“必須利用”與“必然代替”是有機統一的,“必然代替”是終極目標,“必須利用”是手段。社會主義作為新生事物,是一種新的、更高級的社會形態和生產方式。社會主義最終必將取代資本主義,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是歷史發展的大趨勢。
[責任編輯:趙麗娜]
A Doctrine of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 Analysis
Zang Xiuling & Wang Zengjian
(Research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Socialism of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School of Marxism of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Linfen Shanxi, 041000)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a special form of socialism based on market economy instead of product economy. As far a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is concerned, supported by the state policies, the non-public economy has made substantial development while in the ownership structure, the pattern that the public ownership is the main body and the state-owned economy plays a leading role has not changed. Instead, the strength, efficiency, influence and controlling force of the state-owned economy have got larger ascension. The communal development of a variety of ownership economies have greatly enhanced our national power and helped to realize the socialist essence and target as well.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ist marketing economy, to develop mixed ownerships is a necessary requirement and an effective path to deepen the reform of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an important way to realize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socialist public ownership and marketing economy. It cannot result in privatization of the state-owned assets. Instead, it can further promote the dominant position and role of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China. More importantly, adhering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an fundamentally guarantee the right direction that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can be reformed into the mixed ownership. The public ownership as the main body and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ve provided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narrowing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and preventing polarization from being normalized.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arket economy system; ownership structure; income distribution; mixed ownership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相關‘主義’之比較”(項目編號:09&ZD002)、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當代資本主義發展的階段性特征研究”(項目編號:2009jjD840011)、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俄羅斯政黨政治發展態勢及其趨向研究”(項目編號:15BGJ040)、山東省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國際金融危機后資本主義的變革及其趨向”(項目編號:11BKSJ02)的階段性成果。
臧秀玲,女,山東大學當代社會主義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王增劍,男,法學博士,山西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F121
A
1002-3909(2017)01-011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