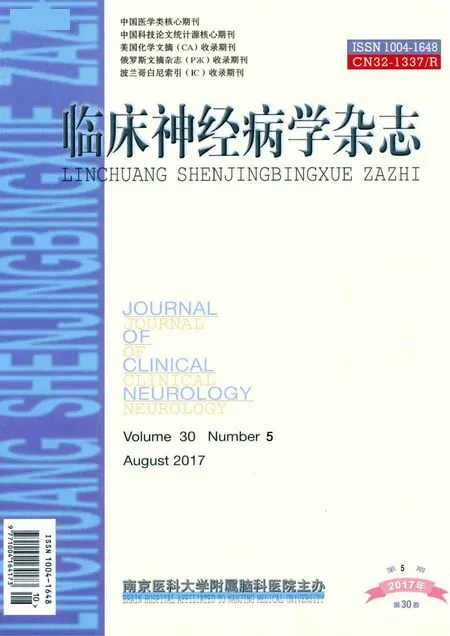極后區綜合征在視神經脊髓炎譜系疾病中的研究進展
邵冰,楚蘭,徐竹,賀電
·綜述·
極后區綜合征在視神經脊髓炎譜系疾病中的研究進展
邵冰,楚蘭,徐竹,賀電
極后區綜合征(APS)作為視神經脊髓炎譜系疾病(NMOSD)中一個重要的核心特征,臨床常表現為頑固性呃逆、惡心、嘔吐(IHN),可在NMOSD病程早期出現,易誤診為消化系統疾病且常被忽視而延誤診治。對于臨床醫師而言,重視并早期識別APS對NMOSD患者的早期診治,減少患者致殘率、提高患者生活質量尤為重要。本文對APS在NMOSD中的發生機制、臨床及影像學特征進行綜述,以提高臨床醫生對APS的重視。
1 NMOSD與APS
1.1 NMOSD 視神經脊髓炎(NMO)又稱Devic病,是一種自身免疫性星形膠質細胞病[1],臨床上以急性縱向延伸長節段橫貫性脊髓炎(LETM)及視神經炎為主要特點[2]。2004 年Lennon等[3]采用間接熒光免疫法在NMO患者血清中檢測到一種能與CNS星形膠質細胞足突上的水通道蛋白4 (AQP4)結合的特異性抗體,命名為抗AQP4-IgG抗體,也被稱作NMO-IgG[2]。該抗體的發現明確了NMO是不同于多發性硬化(MS)的獨立疾病,同時該抗體被作為一項支持標準納入Wingerchuk等[2]2006年修訂的NMO診斷標準中。然而,臨床中血清抗AQP4-IgG抗體陽性的部分患者并不完全滿足NMO的診斷標準,如復發性視神經炎、雙側視神經炎、LETM等,卻與NMO有著類似的致病機制及臨床病程,故有學者于2007年提出NMOSD的概念。NMOSD包含了血清抗AQP4-IgG抗體陽性的視神經炎或脊髓炎患者,但未包含CNS其他部位受累但血清抗AQP4-IgG抗體陽性的患者。2015年國際視神經脊髓炎診斷小組(IPND)最新提出的診斷標準[4]中,將NMO歸入NMOSD,根據血清學抗AQP4-IgG抗體狀態分為抗AQP4-IgG抗體陽性的NMOSD和抗AQP4-IgG抗體陰性的NMOSD,并提出NMOSD的6組核心臨床癥候:視神經炎、急性脊髓炎、APS、急性腦干綜合征、急性間腦綜合征、大腦綜合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