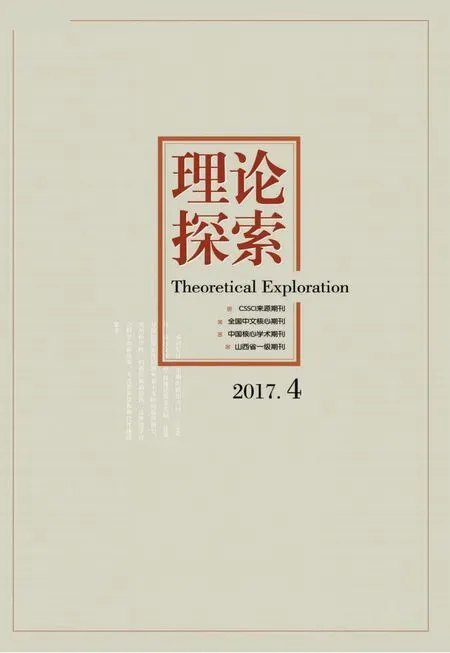俗訓與世范:南宋袁采治家與治世的“民法”規(guī)訓
劉盈辛沈瑋瑋
(1.山西大學,太原 030006;2.華南理工大學,廣州 510006)
俗訓與世范:南宋袁采治家與治世的“民法”規(guī)訓
劉盈辛1沈瑋瑋2
(1.山西大學,太原 030006;2.華南理工大學,廣州 510006)
南宋袁采基層為官的充分歷練經(jīng)驗和社會生活知識的豐富來源,在其以“訓俗”為目的的傳世代表作《世范》一書中得到了充分體現(xiàn)。該書從地方治理的主要議題入手,綜合運用理學義理、訟學知識和社會風俗來構(gòu)造南宋地方精英所普遍追求的倫理道德,重塑儒家禮作為民事法則的要旨,在保障庶民大眾的家庭和諧與財富穩(wěn)定的同時,也利于地方官員履行刑名與錢谷之責。
南宋,袁采,《世范》,倫理重塑,民法規(guī)訓
國內(nèi)學界通常認為,中國古代雖然存在民法,但并不發(fā)達。①然中國古代民法到底由何構(gòu)成,已有觀點頗受民國學者楊鴻烈、梅仲協(xié)、胡長清和潘維和等人的影響。〔1〕一種觀點認為古代民法主要來自含民間習慣成份的儒家學說、鄉(xiāng)規(guī)民約和家法族規(guī)。另一種觀點認為古代民法能夠在歷代法典中找到證據(jù)。本文試圖從來自于民間習慣的儒家思想和家法中尋找古代國家與社會對庶民大眾民事行為的規(guī)范,具體以受南宋朱熹理學思想影響的袁采及其撰寫的頗有家法之名的《世范》一書為例,結(jié)合唐宋思想轉(zhuǎn)型,勾勒一個基層縣官在治家與治世的諄諄告誡中,如何借用傳統(tǒng)禮俗,對治下百姓的諸多民事行為,包括民事糾紛解決進行倫理道德指引和律法規(guī)訓。
一、引論:南宋基層社會世風與袁采其人其書
(一)南宋基層社會的治家與治世之風
兩宋之際,曾經(jīng)有過的豪強大族已經(jīng)消失,替代的是地方性大戶。〔2〕147因經(jīng)濟發(fā)展所導致的世事無常、貧富易位的現(xiàn)象屢見不鮮,這不得不引起一些士大夫的重視。于家庭而言,家族如何在社會競爭中取勝,并保持經(jīng)久不衰,是必須面對的問題。因此,一些士宦家族積極地纂述家訓,以期通過對家庭成員的道德教化、行為規(guī)范等令其修身齊家,來維持家族的優(yōu)勢地位。于社會而言,南宋士大夫?qū)Τo力收復失地深感失望,只能退而求其次,關注社會基層,通過興辦學校(書院)普及知識,變革家族和村社,以使傳統(tǒng)文化精華不致因來犯之敵而遭毀滅。諸如歐陽修開風氣之先,指導如何編纂合乎體例的家譜,范仲淹首創(chuàng)族產(chǎn)之說,朱熹則最先提出設立祠堂,等等之舉均是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古典儒家哲學要求下的應激反應。在江浙,福廣等省份,家族已成為了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因此,南宋對家訓的看重就不足為奇。
經(jīng)濟發(fā)展和人口增多讓普通農(nóng)民意識到生活發(fā)生了重要變化,即使在最發(fā)達的地區(qū),鄉(xiāng)村生活似乎也遠非平安無事。地方官員頻頻報怨肅清土匪之難,衙門充斥著鄰里親友互相訴訟、爭奪田產(chǎn)的案件。例如江西萍鄉(xiāng)“地接湖湘,俗雜吳楚,壤沃而利厚,人繁而訟多……編戶之內(nèi),學訟成風,鄉(xiāng)校之中,校律為業(yè)。”據(jù)宋人周密稱“江西人好訟,是以有簪筆之譏,往往有開訟學以教人者,如金科之法,出甲乙對答及嘩訐之語,蓋專門於此,從之者常數(shù)百人。”〔3〕江南鄉(xiāng)村甚至還出現(xiàn)了專門訓練人如何應付詞訟的機構(gòu),訟學已擴散到了孩童的啟蒙教育:“江西州縣有舍席為教書夫子者,聚集兒童授予非圣之書,有如四言雜字,各類非一,方言俚鄙,皆詞訟語。”〔4〕時任江西宜豐縣令的應俊在編輯的《琴堂諭俗編》一書序言中有同樣的感受:“相欺、相凌、相斗、相奪、相戕殺、相詆訐,以唆教作生涯,以脅持立門戶。”如何防止爭訟當然成為家訓中的重要內(nèi)容。
(二)南宋縣令袁采其人與《世范》其書
袁采(約1140-1195),字君載,信安(今浙江常山)人,南宋隆興元年(1163)考取進士。乾道四年(1168),他的第一個官職是江南西路袁州萍鄉(xiāng)(今江西萍鄉(xiāng))縣主簿,應對江南興訟之俗了如指掌。淳熙年間(1178-1183)出任浙江東路溫州樂清(今浙江樂清)縣令,《世范》正是在該任上制定的。該書共3卷,分睦親、處己、治家三門。《睦親》60則,論及父子、兄弟、夫婦、妯娌、子侄等家庭關系的處理。《處己》55則,縱論立身、處世、言行、交游之道以及如何提升自我修養(yǎng)的規(guī)范要求。《治家》72則,論及處理奴仆、田產(chǎn)、賦稅、債務等竅門。此中包含有大量關于詞訟應對的精細之策,或許就來自于當時頗為流行的訟學。只不過袁采不可公然倡導訟學,只能將官方所打壓的民間訟學知識轉(zhuǎn)變?yōu)楣俜絼裾]之語,合理地利用訟學,使之成為一本民事法律行為指南。
然而,治世須從治家起,這與上述世風也相合。早在北宋之際,司馬光已作《家范》,故袁采的《世范》落腳點必在“治家”,《四庫全書提要》也稱其“固不失為《顏氏家訓》之亞也”,將之視作傳統(tǒng)家訓一類。當然,袁采的身份決定了此書的目的在于正風俗、化人倫,即“訓俗”,所以,該書初定名為《俗訓》,“使田夫野老、幽怨婦女皆曉然于心目間”,達致“庶幾息爭省刑,俗還醇厚”的效果。這是身為父母官的袁采理應具有教化全縣的使命使然。書成之后,袁采委托時任隆興府(今江西南昌)司法參軍的友人劉鎮(zhèn)作序。劉鎮(zhèn)讀罷之后給予極高的評價,建議將書名改為《世范》以廣為流傳,后世又稱《袁氏世范》。
二、家事與國事中的民法規(guī)訓
(一)《世范》對家庭關系的民法規(guī)訓
印刷術(shù)的普及使此前主要靠口頭傳頌的知識被訴諸筆端,有利于士大夫指出文字前后矛盾之處或無法核實的迷信內(nèi)容,從而否定這些傳統(tǒng)的權(quán)威。〔5〕111-113受此影響,袁采即在《世范》一反傳統(tǒng),倡導家庭成員間的平等之道,即便是長輩,也要以超乎其他人的修養(yǎng)來樹立權(quán)威,而非以尊卑壓人。相比朱熹,袁采并沒有無限制地強調(diào)父系原則。〔6〕9,238子女要保持各自的性格,沒必要屈從長輩。同居共財?shù)默F(xiàn)象在宋代頗為常見,然而袁采認為同居能共財固然很好,但不能勉強。為了避免財產(chǎn)繼承糾紛,他還建議多子的大家庭應做好生前遺囑,安頓好庶子、非婚生子及遺腹子的份額。“常預為遺囑之文”且“遺囑公平”。〔7〕55如對于家中的“不肖子孫”要有靈活的應對方法:“若父、祖緣其子孫內(nèi)有不肖之人,慮其侵害他房,不得已而均給者,止可逐時均給財谷,不可均給田產(chǎn)。”否則不肖子將田產(chǎn)變賣,又會“窺覷他房,從而婪取,必至興訟”,而且會“使賢子孫被其所擾害,同于破蕩。”〔7〕54對收養(yǎng)義子他也有精辟的見解:應堅持不收養(yǎng)異姓為原則,以防日后與族人爭產(chǎn)或同姓結(jié)婚的惡果,且義子名分要早定。此外,對被收養(yǎng)人的年齡要區(qū)分對待。貧者養(yǎng)他人之子當于幼時,易培養(yǎng)感情。富者養(yǎng)他人之子當于既長之時,易觀察性情,防止敗家。“蓋貧者無田宅可養(yǎng)暮年,惟望其子反哺,不可不自其幼時衣食撫養(yǎng)以結(jié)其心”,而“富人養(yǎng)他人之子,多以為諱故,欲及其無知之時撫養(yǎng),或養(yǎng)所出至微之人,長而不肖恐其破家,方議逐去,致有爭訟。”所以對富家養(yǎng)子“取于既長之時,其賢否可以粗見,茍能溫淳守己,必能事所養(yǎng)為所生,且不敢破家,亦不致興訟也。”〔7〕39婚配方面,袁采不提倡指腹為婚或童婚,“蓋富貴盛衰,更迭不常。男女之賢否,須年長乃可見。”否則,若有變故,進退兩難,只能興訟。媒妁之言不可輕信,表親婚可鼓勵,但不可因表親而禮數(shù)不周,以免引起紛爭:“故凡因親及親,最不可托熟閥其禮文,又不可忘其本意,極于責備,則兩家周致,無他患矣。”〔7〕50親戚之間互幫互助也時常有之,“人之姑、姨、姊、妹及親戚婦人,年老而子孫不肖,不能不供養(yǎng)者,不可不收養(yǎng)。”但為了防止爭端,“須于生前令白之于眾,質(zhì)之于官,稱身外無馀物,則免他患。”〔7〕53此外,親戚間的借貸不宜太頻,“雖米、鹽、酒、醋計錢不多,然朝夕頻頻,令人厭煩。如假借衣服、器用,既為損污,又因以質(zhì)錢”,反倒“因財成怨”。因此,對待親戚故舊,“不若念其貧,隨吾力之厚薄,舉以與之。則我無責償之念,彼亦無怨于我。”〔7〕34若借人錢谷過多,則會使借錢人“寧以所還之資為爭訟之費者多矣”,〔7〕63那么就難以維持和諧融洽的關系。
在仆人和奴婢管理方面,袁采給出了中肯的建議。納妾和奴婢需防備婢妾與人私通,尤其不宜在外地安置婢妾。漂亮的小妾不可以蓄養(yǎng),“切不可蓄姿貌黯慧過人者。”年老之人更不宜蓄養(yǎng)婢妾,“暮年尤非所宜。”婢妾身份來歷宜要問清,因為“恐有良人子女,為人所誘略”,觸犯刑律。奴婢最好是本地人,便于了解品行,也易處理突發(fā)狀況:“蓋或有患病,則可責其親屬為之扶持;或有非理自殘,既有親屬明其事因,公私又有質(zhì)證。或有婢妾無夫、子、兄、弟可依,仆隸無家可歸,念其有勞不可不養(yǎng)者,當令預經(jīng)鄰保,自言并陳于官。或預與之擇其配,婢使之嫁,仆使之娶,皆可絕他日之意外之患也。”且“雇婢仆須要牙保分明。”〔7〕145-146狡猾奸詐之徒尤不可用,否則極易引誘子弟為非作歹,敗家破財。對頑固不從的奴仆則可遣送回家,但不要毆打,一旦發(fā)現(xiàn)奴仆違法之事就送官究辦,且嚴防佃客引誘家內(nèi)婦幼私自放貸錢谷。
在理財方面,袁采頗重節(jié)約經(jīng)濟用度之理,“蓋百事節(jié)而無一事之費,則不至于匿乏;百事節(jié)而一事不節(jié),則一事之費與百事不節(jié)同也。”〔7〕103凡事應事先準備,科學理財。比如婚喪嫁娶方面,“今人有生一女而種杉萬根者,待女長,則鬻杉以為嫁資,此其女必不至失時也。有于少壯之年,置壽衣壽器壽瑩者,此其人必不至三日五日無衣無棺可斂,三年五年無地可葬也。”〔7〕104同時,還要注意防盜防騙,保持家財不損。他從犯罪心理上分析認為,為富不仁者最易成為打家劫舍的對象。比如富人貸錢取息,只要不是高利盤剝,天經(jīng)地義。但不可乘窮人破產(chǎn)之危,壓低田價,兼并土地。因此,富貴之家應多行善事,和睦鄰里,“居宅不可無鄰家,慮有火燭,無人救應。”“須平時撫恤鄰里有恩義”,〔7〕128如此才能聯(lián)防互助。各家庭院要勤修防護垣墻,以免盜賊侵擾和奴婢及不肖子孫在夜間奔竄;山野僻靜處居住應建立莊園,讓佃戶同住,有所照應。為防止群盜入戶搶劫,則要隨時準備器械,并在重要路口安排防御人手,同時不忘設置緊急出口。尤其是夜間,勿要防衛(wèi)過當,并注意防范火災。為避免騙取財物,盡量不要讓尼姑、道婆、媒婆、牙婆等進入家中。兒童不可佩戴貴重物品,不可獨游于鬧市,防止被人拐騙,也不可單獨在危險之地,如河邊井邊等玩耍逗留。鄰里要注意避免一些無意的過失,防患未然:“人有小兒須常戒約,莫令與鄰里損折果木之屬。”“養(yǎng)牛羊須常看守,莫令與鄰里踏踐山地六種之屬。人養(yǎng)雞鴨須常照管,莫令與鄰里損啄菜茹六種之屬。”除此之外,還需采取一些保護措施防止瓜田李下:“墳塋山林,欲聚叢長茂蔭映,須高其圍墻,令人不得逾越。園圃種植菜茹六種及有時果去處,嚴其籬圍,不通人往來,則亦不至臨時責怪他人也。”〔7〕154-155
(二)家的規(guī)訓經(jīng)驗之于治世的意義
以上量大面廣的民事行為規(guī)范,應是袁氏家族幾代人積累之結(jié)果。〔8〕袁采生于官宦之家,其父袁國賢曾任泉州知府,從小他便受到良好的家教并有機會親自思索并處理大家族中的各種龐雜事物。但是,能寫出以上細微具體的防范經(jīng)營之訣竅,則無不體現(xiàn)他處處留心生活,善于總結(jié)反思的難能可貴。例如他建議“凡夜犬吠,盜未必至亦是盜來探試,不可以為他而不警。夜間遇物有聲,亦不可以為鼠而不警。”〔7〕119又如,他對農(nóng)家起火原因的分析亦十分精到:“火之所起,多從廚灶。蓋廚屋多時不掃,則埃墨易得引火。或灶中有留火,而灶前有積薪接連,亦引火之端也。”“烘焙物色過夜,多致遺火。”〔7〕124-125再如,他對商業(yè)經(jīng)營中摻雜摻假的伎倆也十分了解:“如販米而加以水,賣鹽而雜以灰,賣漆而和以油,賣藥而易以他物。”〔7〕65這些經(jīng)驗全部成為《世范》的材料來源。
袁采的以上勸告看似在處理家長里短之事,但始終是在預防爭訟和刑案發(fā)生,志在安民。這些內(nèi)容完全可以看作是袁采初次主政一方所詳細發(fā)布的安民告示,他試圖通過革新傳統(tǒng)之禮來規(guī)訓百姓的日常民事行為,保全地方家族財產(chǎn)和維持家內(nèi)秩序,最終確保賦稅征收和任內(nèi)治安。在此意義上,家事與國事在袁采這一基層縣令身上得到了統(tǒng)一,更是“家國同構(gòu)—移孝于忠”的當然要求。
三、理學與訟學交織的民法規(guī)訓
(一)理學的道德教化對《世范》民法規(guī)訓的影響
十年的萍鄉(xiāng)主薄生涯讓袁采基本掌握了一縣治理難易之關鍵,即家庭不睦、爭訟財產(chǎn)、為富不仁等。他所編撰的《世范》正是從這些基層治理難點入手,“先天下之憂而憂”,踐行宋代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抱負。②主薄的經(jīng)歷,讓他發(fā)現(xiàn)地方財政虧空的原因在于“作縣之人不自檢己,吃者、著者、日用者,般絜往來,送遺給托,置造器用,儲蓄囊筐,及其他百色之須,取給于手分、鄉(xiāng)司。為手分、鄉(xiāng)司者,豈有將己財奉縣官,不過就簿歷之中,恣為欺弊。或攬人戶稅物而不納;或?qū)⒌綆熘X而他用;或偽作過軍、過客券,旁及修葺廨舍,而公求支破;或陽為解發(fā)而中途截撥……弊百端,不可悉舉。”于是他告誡到:“大凡居官在事,不可不仔細,猾吏奸民尤當深察。若輕信吏人,則彼受鄉(xiāng)民遺賂,百端撰造,以曲為直,從而斷決,豈不枉哉!”除此之外,官吏以權(quán)壓人,恃強凌弱的例子也不勝枚舉:如“貪暴之官必有所恃,或以其有親黨在要路,或以其為州郡所深喜,故常難動搖。”“吏以官庫之錢而行賂,毀去簿歷,改易案牘。”“冒占官產(chǎn),不肯輸租;欺凌善弱,強欲斷治”等等,〔7〕115-116袁采只能將改善這一狀況寄希望于天怒人怨:“假以歲月,縱免人禍,必自為天所誅也。”〔7〕112總之,“存天理,滅人欲”的樸素報應觀成為袁采教化百姓的不二選擇。如他認為商人不得摻雜摻假,否則天理難容:“凡物貨必真,又須敬惜。如欲以此奉神明,又須不敢貪求厚利,任天理如何,雖目下所得之薄,必無后患。”〔7〕169又如面對因分家析產(chǎn)而訴爭頗多的現(xiàn)實,他認為即便分到更多的財產(chǎn),但遇到浪蕩子弟,也無法逃脫貧困的境地,而這就是所謂的天理難勝:“有以分析不平,屢經(jīng)官求再分,而分到財產(chǎn)隨即破壞,反不若被論之人昌盛如故者。世人若知智術(shù)不勝天理,必不起爭訟之心。”〔7〕25
“存天理,滅人欲”的觀念還表現(xiàn)在袁采欲通過“禮義”而節(jié)制欲望:“飲食,人之所欲,而不可無也,非理求之,則為臀為饞;男女,人之所欲,而不可無也,非理押之,則為奸為淫;財物,人之所欲,而不可無也,非理得之,則為盜為賊。人惟縱欲,則爭端起而獄訟興。圣王慮其如此,故制為禮,以節(jié)人之飲食、男女;制為義,以限人之取與。”〔7〕96雖然南宋之初理學仍處邊緣地位,〔9〕219但如此好學上進,審時度勢,能迅速捕捉到社會形勢的袁采想必也對理學思想細致追蹤過,因為《世范》中有關女性的文字竟約占1/5,大部分均體現(xiàn)了對不同女性的理解和關懷,這是宋代理學以及整個社會對女性態(tài)度轉(zhuǎn)變的寫照。
(二)訟學的技術(shù)防范對《世范》民法規(guī)訓的影響
刑名乃第一大要務,袁采極力降低訴訟可能。他認為爭訟乃不得已而為之。在處事過程中只要“彼稍服其不然則已之”,“不必費用財物,交接青吏,求以快意,窮治其仇。”即便吃了小虧也無妨,強大的內(nèi)心可化解戾氣,避免與惡人相較,更不要“至于毆打論訟”。因為“忠信二事小人不守者多……而憐小人之無知,及其間有不得己。”〔7〕35這可能與袁采兼有百家思想有關,《世范》在清代以前也一直被歸為雜家。他更是從訴訟成本上來勸導不必興訟:“仇者不伏更相訴訟,所費財物,十數(shù)倍于其所直。”從訴訟心理上講,“大抵人之所訟互有短長,各言其長而掩其短,”如果再考慮到官吏貪墨的可能,“胥吏得以受賕而弄法,蔽者之所以破家也。”這樣打官司就成了意氣之爭。即便是勝了官司,也丟了陰德:“至于爭訟財產(chǎn),本無理而強求得理,官吏貪謬,或可如志,寧不有愧于神明!”〔7〕111
錢谷也是基層治理之核心,為完成賦稅征收任務,確保不違農(nóng)時,更要從積極方面預防爭產(chǎn)興訟。田產(chǎn)“異居分析之初,置產(chǎn)、典買之際,尤不可不仔細。人之爭訟多由此始。”因為借此機會,“有欲便順并兩丘為一丘者”,“有以屋基山地為田,又有以田為屋基園地者。”為此,因田產(chǎn)四至不清而導致的爭訟完全可以通過界至分明來避免:“人之田畝有在上丘者,若常修田畔,莫令傾倒。人之屋基園地若及時筑疊垣墻,才損即修。人之山林若分明挑掘溝塹,才損即修,有何爭訟!”〔7〕155分家析產(chǎn)要早立鬮書,送官驗證,勿要因懼怕官府勒索而因小失大。同時,要具有契約意識:“不可憑恃人情契密不為之防……如交易取錢未盡,及贖產(chǎn)不曾取契之類。”〔7〕62在田產(chǎn)交易程序上,因“官中條令,惟交易一事最為詳備,蓋欲以杜爭端也。”但若“人戶不悉”,就會“違法交易,及不印契、不離業(yè)、不割稅,以至重疊交易,詞訟連年不決。”因此,袁采給出了甚為詳細的指引:“當先憑牙家索取閹書砧基,指出丘段圍號,就問見佃人,有無界至交加,典賣重疊。次問其所親,有無應分人出外未回,及在卑幼未經(jīng)分析。或系棄產(chǎn),必問其初應與不應受棄。或寡婦卑子執(zhí)憑交易,必問其初曾與不曾勘會。如系轉(zhuǎn)典賣,則必問其元契已未投印,有無諸般違礙,”之后“方可立契”。即使是在簽字畫押之時,“如有寡婦幼子應押契人,必令人親見其押字”等,〔7〕160以確保交易真實有效。法律之外的一些小常識在袁采看來更需遵循,例如鄰近田產(chǎn)宜增價買,“凡鄰近利害欲得之產(chǎn),宜稍增其價,不可恃其有親有鄰及以典至買及無人敢買而扼損其價。萬一他人買之則悔且無信,而爭訟由之以興也。”違法田產(chǎn)更是不可買,“凡田產(chǎn)有交關違條者,雖其廉價,不可與之易。”“他時事發(fā)到官,則所廢或十倍。”〔7〕161同時,寄產(chǎn)于官戶或普通地主之家以逃避賦役都是愚昧之舉,易引起日后爭訟,所以應秉持“君子之財取之有道”之原則,早備賦稅,及時繳納。“凡有家產(chǎn)必有稅賦,須是先截留輸納之資,卻將羸余分給日用,歲入或薄,只得省用,不可侵支輸納之資。”〔7〕64
袁采所關注的以上問題在宋代被稱民事“細故”。實際上對庶民大眾而言,這些被稱為“細故”的瑣碎之事,相比官府所看重的“殺人越貨”之重情更為常見和重要,〔10〕也是日常倫理可望又可及的領域。因此,《世范》不僅依托已經(jīng)成熟的理學價值觀來對貪墨奸猾之徒進行倫理道德上的譴責,而且將“細故”之事同刑名訴訟和錢糧賦稅結(jié)合起來,既有息訟和諧的消極預防,又有憑證交易的積極預防,讓“細故”之事同政事緊密聯(lián)系起來,從倫理性的理學之道德教化和技術(shù)性的訟學(訴訟發(fā)生學)之維權(quán)止損來共同重塑社會的倫理道德,進而到達對庶民百姓進行民法規(guī)訓的目的。
四、斯文的轉(zhuǎn)變與《世范》的民法偏好
(一)袁采《世范》與《顏氏家訓》的區(qū)別
《四庫全書提要》稱《世范》“固不失為《顏氏家訓》之亞也。”不過,《顏世家訓》比較側(cè)重于學術(shù)的傳承,頗多對經(jīng)史文章的考證,尤其詳述了顏之推在書法、繪畫、射箭、算術(shù)、醫(yī)學、彈琴等方面的見解,有很濃的書生學究氣。強調(diào)躬耕實踐,格物致知的袁采則主張現(xiàn)實主義和實用主義,《世范》便側(cè)重世俗經(jīng)驗的傳授而非理論的空洞說教。因為以袁采為代表的南宋普通知識分子,正逐漸拋棄了以往的“文學—歷史”的視角,而代之“倫理—哲學”的視角,這是唐宋變革之際所致。隨著科考人數(shù)的增加,北宋以降通過科舉考試的可能性下降了。到11世紀末,通過兩種傳統(tǒng)的標準——門第與職官——來維持士的身份已不可能,只能靠讀書為學才能獲得士的身份認同。為學的目的變成了完善個人道德修養(yǎng),學以至圣人。〔11〕這正是理學所強調(diào)的,每個人只要能充分發(fā)揮天性,就可以成圣成賢,不一定要出仕為官。道德而不是官位才是理學家真正看重的權(quán)威身份。〔12〕于是,南宋士大夫就從官僚性格變成地方精英的性格,〔13〕這就是唐宋思想轉(zhuǎn)型的社會基礎。如此就不難理解,袁采心目中理想的士是一個倫理的人,而不是顏之推所看重的一個有文化的人。因為,顏之推面對的是一個世家大族正拋棄他們的文化以便仕進的時代,袁采面臨的則是一個地方精英正拋棄他們的倫理標準,以便增強他們占有地方財富和權(quán)力的時代。〔14〕14-15
就此而言,袁采理想的“士”雖等同于“富貴之家”“高資之家”和“貴顯之家”,但顯貴之家又是通過地方精英所重建的倫理道德來維持的。所有這些為維持財富和權(quán)力而重建的倫理道德,則是由禮義、律法、習俗以及理學相互融合而成的。如果說《顏氏家訓》所代表的是世家大族繼承儒雅的文化傳統(tǒng)來出仕,以保持榮譽的“斯文”說教的話,那么《世范》則是代表家族如何通過新的道德倫理,保持良性經(jīng)營的長遠利益之方案。如何保持這種家族地位?唯有通過保持鄰里和睦,與人保持良好而端莊的關系,仔細打理家族財產(chǎn)等來實現(xiàn),而這些恰恰是南宋庶民百姓所關乎的主題。因此,袁采或更偏愛于涉及民法所關注的物質(zhì)財富,但這在顏之推看來完全是“有辱斯文”。〔14〕9-11袁采甚至認為士大夫之子弟,即便是科舉失敗,也可以通過選擇其他職業(yè)來追求民事財產(chǎn),以維持家族地位:“茍無世祿可守,無常產(chǎn)可依,而欲為仰事俯育之計,莫如為儒。其才質(zhì)之美能習進士業(yè)者,上可以取科第、致富貴,次可以開門教授,以受束修之俸。其不能習進士業(yè)者,上可以事筆札、代箋簡之役,次可以習點讀,為童蒙之師。如不能為儒,則巫醫(yī)、僧道、農(nóng)圃、商賈、技術(shù),凡可以養(yǎng)生而不至于辱先者,皆可為也。”并且認為“子弟有愚繆貪污者,自不可使之仕宦。”因為“今其愚繆,必以獄訟事,悉委胥輩,改易事情,庇惡陷善”,“今其貪污,必與胥輩同謀,貨鬻公事,以曲為直,人受其冤,無所告訴。”〔7〕11
(二)類似于《世范》的南宋作品
或許只有同時代的《琴堂諭俗編》能與《世范》的影響力相當。《琴堂諭俗編》原由應俊編輯成書,再經(jīng)元人左祥補編后分上下卷。上卷注重家內(nèi)禮制,包括孝父母、友兄弟、教子孫、睦宗族、恤鄉(xiāng)里、重婚姻、正喪服、保墳墓、重本業(yè);下卷注重社交品行,包括崇忠信、尚儉素、戒忿爭、謹田戶、積陰德、擇朋友。“其書大抵采摭經(jīng)史故事關于倫常日用者,旁證曲喻,以示勸戒,故曰《諭俗》。”就此來看,該書同樣是以重建日常民事倫理道義為中心,與袁采不謀而合。可以說,袁采旨在通過重塑一種新型的社會倫理,〔15〕為的是方便在尚訟的江南之地更能舉重若輕地執(zhí)政。〔16〕
此種集家庭倫理和社會倫理于一體的新型倫理之所以可能,是在印刷普及使得知識易得的前提下,因地方經(jīng)濟發(fā)展促使民眾增強了通過律法進行自我防衛(wèi)的意識,再加上地方精英力促而成。當然,重視新型倫理的價值是在南宋社會內(nèi)在轉(zhuǎn)向的大背景下完成的。當南宋無法解決包括法制繁雜在內(nèi)的多種社會問題時,思想界的領袖人物便反而求諸己,期望以增強道德的方式來解救蒼生。〔17〕30-43這種保守主義思想終被樹立為國家正統(tǒng),成為影響后世中國近千年之久的理學。〔18〕3總之,通過引入理學禮俗以及律法規(guī)范,使庶民大眾的民事行為得以遵照治國平天下的主旨來踐行,就是袁采及其《世范》的民法偏好所在。
五、余論:民法規(guī)訓的古今之別
總體看來,作為規(guī)范民事行為的《世范》完全是一整套為人處世的社會生活小百科,包含著各種民事行為和處分之道,細致入微,可以說是袁采對人生、社會和生活感悟的肺腑之言。〔19〕268-269而且該書從庶民自身利益來實現(xiàn)移風易俗,普及契約常識等基本律法的功業(yè),很容易成就袁采平易近人的父母官形象。該書完全可以視作風俗紀要,以禮義秩序、律法規(guī)范和民風世俗為主題構(gòu)筑了南宋江西的民事規(guī)范的重點和難點,既可助廟堂之人關懷民情,也可襄江湖之人安然處事,雅俗共賞,代表了當時地方士大夫精英所追求的民事行為標準,后人亦稱贊道:“所言婦子居室之事,準乎人情,協(xié)乎天理,沒身處世,即病即藥,幾乎纖細,悉不遺矣。”〔20〕127
袁采及其《世范》一書,無不對古代民法部分來自于禮義道德與家法俗訓的觀點有佐證和補強的意義。最新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第十條也規(guī)定,處理民事糾紛,應當依照法律;法律沒有規(guī)定的,可以適用習慣,但是不得違背公序良俗。該條所指的習慣以及善良風俗,實際上完全等同于蘊藏在傳統(tǒng)家法俗訓中的禮義規(guī)則,只不過是民法規(guī)訓的載體不同罷了。因為在古人看來,制定過多的法律如同人為地制造干預自然的準則。〔21〕法律并不是傳統(tǒng)社會治理的唯一手段,這正是古人將日常生活實踐中常見的民事規(guī)則完全融入于“禮”這一富有道德教化的形式之初衷。
注 釋:
①參見張晉藩:《論中國古代民法研究中的幾個問題》,《政法論壇》1985年第5期;趙曉耕:《試述宋代的民事法律規(guī)范》,《法學研究》1986年第3期;懷效鋒:《中國古代民法未能法典化的原因》,《現(xiàn)代法學》1995年第1期。
②余英時認為,“以天下為己任”可以視為宋代“士”的一種集體意識,參見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三聯(lián)書店,2004年,第219頁。
〔1〕俞 江.關于“古代中國有無民法”問題的再思考〔J〕.現(xiàn)代法學,2001(6).
〔2〕許倬云.說中國——一個不斷變化的復雜共同體〔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
〔3〕《癸辛雜識·續(xù)集·訟學業(yè)觜社》.
〔4〕《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之一五十》.
〔6〕伊佩霞.內(nèi)闈:宋代的婚姻和婦女生活〔M〕.胡志宏,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
〔7〕袁 采.袁氏世范〔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
〔8〕蔣黎茉.袁采與《袁氏世范》研究〔D〕.長春:東北師范大學,2012.
〔9〕葛兆光.中國思想史〔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
〔10〕趙曉耕.兩宋法律中的田宅細故〔J〕.法學研究,2001 (2).
〔11〕周 晉.唐宋學術(shù)轉(zhuǎn)折與道學文化的興起——略述包弼德教授的程頤研究〔J〕.中州學刊,1997(1).
〔12〕張冠梓.探尋歷史與現(xiàn)實之間的脈絡——專訪哈佛大學包弼德教授〔N〕.中國社會科學報,2009-09-03.
〔13〕周 武.唐宋轉(zhuǎn)型中的“文”與“道”——包弼德教授訪談錄〔J〕.社會科學,2003(7).
① 以上例句來自北京大學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創(chuàng)建的現(xiàn)代漢語語料庫(CCL corpus)、《漢語功能語義分析》和其他語料。為適用于分析,有些句子稍做調(diào)整.
〔14〕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轉(zhuǎn)型〔M〕.劉寧,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
〔15〕劉 欣,呂亞軍.興訟乎?息訟乎?——對《袁氏世范》中有關訴訟內(nèi)容的分析〔J〕.邢臺學院學報,2009(3).
〔16〕龔汝富.江西古代“尚訟”習俗淺析〔J〕.南昌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2).
〔17〕黃仁宇.現(xiàn)代中國的歷程〔M〕.上海:中華書局,2011.
〔18〕劉子健.中國轉(zhuǎn)向內(nèi)在:兩宋之際的文化內(nèi)向〔M〕.趙冬梅,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
〔19〕黃錦君.宋袁采及他的《袁氏世范》〔A〕.舒大剛.宋代文化研究(第十八輯).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10.
〔20〕陳弘謀.五種遺規(guī)〔A〕.《續(xù)修四庫全書》編委會.續(xù)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21〕沈瑋瑋.傳統(tǒng)觀念與民法結(jié)構(gòu):再論中國古代民法的價值〔J〕.廣東社會科學,2016(1).
責任編輯 楊在平
D929
A
1004-4175(2017)04-0123-06
2017-05-07
2016年度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共建項目“廣東瑤族糾紛解決機制研究”(N4160670),負責人沈瑋瑋。
劉盈辛(1994-),女,山西運城人,山西大學法學院。
沈瑋瑋(1986-),男,湖北襄陽人,華南理工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法制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