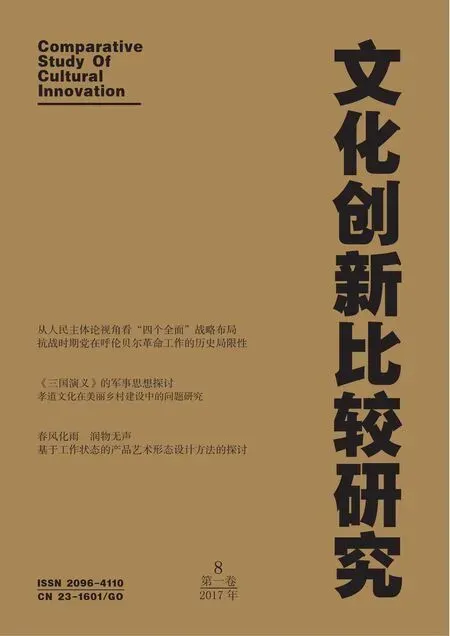解讀《黃色墻紙》中的女性意識
鄒德芳
(廣西中醫藥大學外語部,廣西南寧 530001)
解讀《黃色墻紙》中的女性意識
鄒德芳
(廣西中醫藥大學外語部,廣西南寧 530001)
著名短篇小說《黃色墻紙》是美國優秀的女性主義文學作品之一,其作者夏洛特·珀爾金斯·吉爾曼在小說里刻畫了一位敏感的知識女性在父權制婚姻家庭的“囚籠”里備受壓抑的經歷,揭示了父權制思想對女性身心兩方面的摧殘。本文從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視角出發,通過分析故事中女主人公的經歷和作品中所采用的象征來揭示作品中強烈的女性自我意識,并表明女性要活得真正的獨立和自由還需要擺脫父權制社會對女性的壓迫和束縛。
女性主義;黃色墻紙;象征手法
美國女作家夏洛蒂·珀金斯·吉爾曼(1860-1935)的《黃色墻紙》是女性批評家重新發掘的著名女性主義文本,它反映了19世紀末美國社會男女關系的現狀,作者在作品中揭露了父權制社會對女性帶來的困擾和束縛,倡導女性要有自己的自由權利和價值觀,并對男權社會和權威提出了強烈的抗議。該作品取材于作者的真實生活,因此可以說是一部半自傳體小說。
吉爾曼于1860年出生在美國康涅狄格州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從小有藝術天賦的她24歲時就嫁給了一個藝術家。在她產下第一個孩子后患上了憂郁癥,神經極度衰弱,這與她不幸福的婚姻有關。此后她接受了當時美國一位著名的醫生所謂的“休息療法”,該療法要求她不讀書,不寫作,不思考,不參加任何社交活動,甚至不做家務,不能與自己的孩子過于親近。她就像嬰兒一樣被禁錮在自己的房間里,長期吃藥,臥床休養。吉爾曼在堅持了一個月后,精神接近崩潰的邊緣,這使她在極度痛苦中重新審視了她的丈夫和家庭,思考父權制度下的女性和家庭、社會的關系。離婚后的吉爾曼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寫下了 《黃色墻紙》這一短篇小說,并投身于當時的女權運動中,進行了積極、大量的文學創作。
1 女性主義文學批評
女性主義文學批評(Feminist Criticism/Feminism)來源于西方60年代初爭取男女平等的婦女解放運動,伴隨而來的是對文學作品的研究,并帶動了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繁榮和一大批理論著作的出現。女性文學批評理論為提高婦女社會地位提供了理論武器,最具代表性的流派主要有三種:自由的女性主義、激進的女性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女性主義。
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提倡理性,向權威的傳統質疑。激進的女性主義認為父權制是女性受壓迫的根源,由譴責男性的生理特征,轉而贊美女性的生理特征。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認為女性受壓迫的根源來自父權社會的意識形態和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兩個領域,認為要為婦女爭取特別的保護性立法。
2 《黃色墻紙》中的女主人公——“我”
小說中的女主人公沒有名字,是以第一人稱的敘事手法講述了一個女知識分子走向精神崩潰的悲劇命運。“我”在產后患上了抑郁癥,當醫生的丈夫約翰把“我”帶到一座鄉間別墅進行治療。鑒于“我”的神經衰弱,約翰采用了“休息療法”,把“我”安排住在樓上的育兒室,禁止“我”的一切活動,包括思考、寫作、做家務、接觸外界,甚至自己的孩子。育兒室每個方向都有窗戶,窗上都裝有柵欄,墻壁上糊著黃色的墻紙,這讓“我”倍感壓抑,丈夫卻說這樣的房間對“我”有好處,因為陽光充沛,空氣好。“我”多次提出搬到樓下住、更換墻紙、堅持工作等要求,均遭到丈夫的反對,而且“我”與丈夫的溝通越來越難,最后到了“失語”的境地。丈夫由于經常要在病院加班,就委托他的妹妹來照顧監管“我”。在她的監督下,“我”被剝奪了唯一舒緩精神壓力的方式—寫作。在無所事事,極度沮喪的情況下,“我”只得把注意力轉向了黃色的墻紙。逐漸地,從原來毫無意義,令人壓抑的枯燥乏味的墻紙后“我”看到了一道道柵欄,柵欄的后面是一個,有時是多個女人在彎腰爬行。這些女人竭力要從墻紙中逃離出來,擺脫囚禁,可是卻被緊緊地禁錮,無法脫身。慢慢被逼向瘋癲狀態的“我”從墻紙里爬行的女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于是開始撕扯黃色的墻紙,在地板上爬行。丈夫看到此情景,驚愕得暈了過去,“我”只好從他身上爬過去。
小說中的“我”是被丈夫控制、壓迫,失去自由和生存價值的家庭女性。瘋癲的狀態表明了“我”的女性意識的覺醒,然而代價卻是高昂、殘酷和悲壯的。一個具有現代意識的女性被淹沒在父權制度當中,被扼殺在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模式當中。
小說是從兩個階段來分析描述“我”這個角色的,即意識清醒和意識模糊兩種情況。“我”意識清醒時,代表著父權制下女性的特點:沉默與服從。當醫生的丈夫執意要“我”住到樓上的育兒室,雖然“我”提出過抗議,并試著與丈夫溝通和交流,但只要丈夫表現出不耐煩和反感,“我”就停止了努力。“我”在面對強大的父權制家庭時,感到力不從心。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在家庭中女性的地位是依附于丈夫的,丈夫有說話權和決定權,女性只是一種附屬品。雖然有幾次“我”與丈夫進行了交流,但當“我”面對丈夫嚴厲苛刻的眼神時,就哭了起來,說不下去了。這表明女性把爭取平等地位的希望寄托在男性身上是行不通的,甚至更可怕的是女性把弱勢群體、附屬地位的思想內化了,用男性的眼光來看待自己的渴求。“我”在小說的結尾處處于意識模糊的階段,雖然有些評論家認為這是父權制取得勝利的象征,但是鑒于當時女性在社會中的地位以及女權運動的起步階段,“我”的瘋癲更象是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思想上獲得的自由。這是對男性中心社會的反抗,是擺脫附屬地位,實現自我的手段。
3 《黃色墻紙》中的象征寫作手法
短篇小說《黃色墻紙》里吉爾曼運用了大量的象征來表達她的女權主義的觀點和意識,這些看似普通的事物在小說中表達了深層的涵義。小說的女主人公生活在一個充滿象征意味的環境中,她所居住的別墅、嬰兒室、黃色墻紙是小說中采用的重要象征。它們反映了女主人公對所處環境的內心感受、其女性意識發展的不同階段以及對父權制社會的控訴和反抗。
3.1 鄉間別墅
為了治好女主人公的病,丈夫選擇了一所鄉間別墅作為療養的靜地。這幢房子是殖民時期的一座世襲產業,這就代表了男人對女人有控制權的傳統。這幢房子是他們的家,但是卻沒有家的溫馨和親切,看起來幽靜別致的別墅實則是禁閉女主人公的場所。別墅遠離公路,周圍三英里內沒有村落,房子顯得孤僻冷清,這暗示著女主人公被丈夫人為地與社會隔絕開來。女主人公毫無自我意愿可言,只能聽從丈夫的安排,猶如困在牢籠里的小鳥。在這里,家和房子不是人們休憩、享受天倫之樂的港灣,而是實施男權社會里男女不平等、女性遭到男性壓迫和束縛的場所。隔絕、孤立、壓抑是這所房子的代名詞。女主人公向丈夫表達了住在這種房子里害怕、心緒不寧、孤獨的感受,可是得不到作為一家之主的丈夫的理解,失去了話語權和自由。
3.2 嬰兒室
樓上的嬰兒室是女主人公的臥室,也是她的活動場所。這間房子的窗戶都釘上了鐵柵欄,原來是為了防止孩子掉出窗外,現在卻成為了禁錮女主人公的囚籠。從這里可以看出在丈夫眼里,女主人公不過是個孩子,是個需要照顧,處于被動、附屬地位的人。女性就猶如男性的私有財產,任由他們處置和安排,而且要一直扮演著長不大的角色,受男性的支配和控制。
固定在地板上的大床則象征著女主人公和丈夫一成不變的生活方式,無法改變的兩性關系。女主人公渴望與外界進行交流和接觸,哪怕只是到樓下,但是都遭到了丈夫的反對。這些柵欄象征著男性要阻斷女性與社會的接觸和交流,好讓她們安心在家里扮演著妻子和母親的角色。女主人公希望通過寫作來宣泄自己的情感,可是也遭到了反對,丈夫不在家的時候,甚至要他的妹妹到家中看護女主人公,以防她有任何表達自己的自由的機會。在這樣的父權制社會里,女性是沒有獨立的生活空間的,甚至被剝奪了獨立思考的權利,女性只能屬于丈夫和家庭,失去了自己的個性和自由。
3.3 黃色墻紙
黃色墻紙是貫穿整篇小說的象征,在推動故事情節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對黃色墻紙的不同階段的認識和理解則表明了女主人公從傳統女性到有自我意識的女性的轉變過程。
故事的一開始,女主人公認為這種顏色的墻紙丑陋不堪,圖案混亂,甚是厭惡。此時她的意識是清醒的,還在為自己神經衰弱而不能照顧好家庭和孩子感到內疚,這表明了這個階段的女主人公是具有傳統思想的女性,努力做一個好妻子和好母親,這符合父權制社會對女性的要求。當女主人公被禁錮在嬰兒室里,終日無所事事時,她開始研究黃色的墻紙,對墻紙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墻紙不再顯得那么讓人厭惡,因為她看到了墻紙里的人影,看到了爬行的女人,她們要擺脫鐵柵欄而在地上爬行。此時的女主人公身體狀況雖然好轉,精神狀態卻日益惡化,意識逐漸模糊。爬行的女人是吉爾曼時代女性地位的真實寫照,她們沒有獨立完整的人格,不能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思想,卑微地依附于丈夫和家庭,成為父權制社會的附屬品。黃色墻紙中的女人爬啊爬啊,怎么也爬不出柵欄和囚籠,這表明了女性無法掙脫傳統思想的束縛,無法擺脫社會對她們的禁錮和壓迫。
小說的結尾女主人公撕破墻紙后瘋了,這是一個充滿了寓意的結局。女主人公的瘋癲既表現了女性對自身地位和處境的意識和不滿,也是對父權制度的一種控訴,是一種極端的尋求解放的出路。從這里不難看出作者對并未找到女性解放真正途徑的矛盾心理和困惑心情。
《黃色墻紙》是一部充滿了女性意識和女權思想的文學作品,作者吉爾曼可稱為“第一代”女性作家。小說通過女主人公的遭遇呼吁廣大女性要通過自身的努力,正確認識自己,擺脫父權制度的社會對女性的束縛和壓迫,獲得真正的獨立和自由,享有與男性平等的地位。
[1]Gilman.Charlotte Perkins.The Yellow Wallpaper[M].New York:The Feminist Press,1973.
[2]陳曉蘭.女性主義批評與文學詮釋[M].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1999.
[3]楊莉馨.西方女性主義文論研究[M].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2.
I712
A
2096-4110(2017)03(b)-0028-03
[課題項目]廣西優秀中青年骨干教師培養工程項目(項目編號:gxqg022014025)。
鄒德芳(1975-),女,浙江杭州人,天津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碩士,廣西中醫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外國文學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