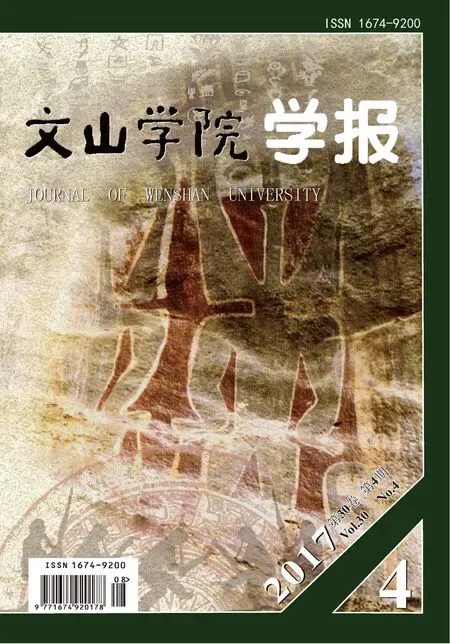主糧結構的優化:當代生態建設的又一關鍵環節
楊庭碩,耿中耀
(吉首大學 歷史與文化學院,湖南 吉首 41600)
主糧結構的優化:當代生態建設的又一關鍵環節
楊庭碩,耿中耀
(吉首大學 歷史與文化學院,湖南 吉首 41600)
農業生產是人類與所處自然與生態系統制衡運行的紐帶,優化“主糧”結構直接關系到人類與生態系統和諧程度的提升。在時下的生態建設中,社會各界總是習慣性地聚焦于憑借工程技術手段,或創立和擴大自然保護區去推動生態恢復。這樣的努力當然無可厚非,但卻遠遠不夠。原因在于,“主糧”結構不合理對生態系統構成的沖擊和損害,更其直接和影響深遠。在生態建設中忽視“主糧”結構優化能夠發揮的關鍵作用,顯然是一種建設思路上的失誤和偏頗。這樣的思路若不及時調整,勢必還會造成更大的損失和災難。
“主糧”結構;生態建設;關鍵環節
一、“主糧”結構的內涵
一提到“主糧”結構,習慣性的看法總是將其內涵鎖定在禾本科作物內。但這是一種十足的偏見。綜觀古今中外的“主糧”物種構成,除了禾本科作物外,往往還包括眾多科屬的糧食作物,如豆科、藜科、莧科、旋花科、唇形花科等等。此外,很多非禾本科糧食作物,在世界上不同民族和國家中都充當過“主糧”,有的還一直沿用到今天。比如,屬于豆科的扁豆,仍然在土耳其充當“主糧”;屬于棕櫚科的桄榔木,在東南亞和南太平洋群島的十幾個國家中也依然充當“主糧”;芭蕉科的芭蕉籽實,在中美洲和幾內亞灣沿岸各國民族中,至今還將其作為“主糧”種植。
因此,僅僅把“主糧”鎖定在禾本科作物中,不僅無法滿足人類生活的多樣化需求,還會在無意中導致相關生態系統遭受損害。生態學的研究告訴我們,多一種“主糧”作物,就會在該作物規模種植的基礎上,形成一個龐大的食物鏈,也就能夠支撐起更多生物物種的延續,從而能夠在不經意中發揮了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功能。此外,同一物種不同品種的“主糧”并行種植,也能發揮同樣的功效,同時還能起到防治病蟲害和防災減災的功能。從這個意義上說,理想的“主糧”結構所涉及到的生物物種越豐富越好,同一物種的不同品種和地方栽培品種越豐富越好。
“主糧”結構的定型,涉及到三大要素的綜合作用:一是自然與生態結構,二是與此相關的民族文化,三是農業生產的歷史演化過程。因而,評估“主糧”結構的優劣,顯然需要兼顧到上述三大要素的實情和發展趨勢,才能做到在確保全國人民基本生活得到充分滿足的同時,也能為當下的生態建設發揮作用。
眾所周知,任何意義上的“主糧”生產,都必須與所處地區的自然與生態系統相適應。如果適應水平較高,那么相關民族的“主糧”生產,不但成本投入低,成效大,而且還對當地生物多樣性保護、病蟲害的防治等發揮重大作用。我國幅員遼闊,生態類型豐富而多樣,如果“主糧”產品的物種構成過于單一,就會對相關生態系統構成重大的壓力;若“主糧”生產不能與當地的自然與生態系統相適應,就會直接干擾到該區域生態建設的成效,甚至還可能抵消已經取得的成績。從這個意義上說,“主糧”結構的物種構成越豐富,其生態維護價值就越大。
我國民族構成復雜多樣,民族文化多樣性極為復雜。因而,我國“主糧”種植的農耕體制,以及生態管護體制,也會表現得互有區別。這樣的區別,又會導致生產成本和生產效益的迥異。由此而產出的“主糧”產品,即使是同一農作物物種,其產品都會表現得千姿百態。
在這些多樣化的傳統農產品中,必然包含著眾多名特優農林牧精品。這不僅對自然資源的合理使用和管護,可以發揮多方面的積極作用;對豐富我國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我國生物物種基因多樣化,也會具有重要價值。
在歷史上,我國不僅是一個農業大國,同時還是世界上“農業文化遺產”擁有量最多的國度之一。由于這些“農業文化遺產”,都是定型于工業文明之前,因而它們本身就具有生態維護的稟賦。當下,發掘利用好這樣的“農業文化遺產”,不僅可以為“主糧”結構的優化提供有益的參考和借鑒,還能支持我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同時又具有提供生態食品,確保糧食安全的功效。就這一意義上說,對我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進行傳承保護和創新利用,也是當下從事生態建設必須加以有效利用的手段與方法。
“主糧”結構的定型是我國各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歷史演化的產物。這樣的歷史過程,又必然是特定時代、特定地區和特定技術水平,相互制衡和協同演化的過程,而且還與不同時代的國內外形勢直接關聯。以至于由此而形成并定型延續下來的“主糧”結構,無不打上了時代和地域的烙印。這對于當前中國的生態建設來說,所表現出的作用必然會優劣參半,其間的精華,必須發揚光大;其間的偏頗和失當,也需要及時加以消除。只有做到這一點,才能滿足當前中國生態建設的需要。
立足于上述,若評估現行“主糧”結構的優劣,顯然得取準于當前我國農業生產和生態建設的具體要求,去具體分析、論證兩者之間的契合程度,以及能否及時消除和化解歷史留下的不利因素,并在這一過程中放大和提升有利因素。
二、“主糧”結構的評估
我國當下的“主糧”結構,僅重點關注稻米、小麥和玉米三種。近年來,我國農業部才致力于推動馬鈴薯的“主糧”化。而大豆在我國民眾的實際生活中,本身就具有“主糧”屬性,在國家規劃的“主糧”種植中,甚至沒有把大豆列為糧食作物。還有一些作物,在歷史上曾經是國家法定的“主糧”,但在當代卻被歸為“雜糧”,根本不納入國家管理的框架之內。如藏族所種植的青稞,蒙古族培養的糜子和沙米。這只能理解為,時下我國的“主糧”結構嚴重缺乏包容性,不但物種構成較為單一,而且在大力推廣種植這些“主糧”作物后,還會在無意中損害我國的生物物種多樣性水平。
隨著雜交稻的推廣,我國歷史上各民族培養成功的數以千計的水稻品種,其種植規模和利用范圍都遭受了嚴重的沖擊,很多名特優產品也隨之銷聲匿跡。正如朱有勇所指出的,隨著品種的銳減,水稻的病蟲害日趨猖獗,進而由此還會引發農藥的濫用,其生態受損所付出的代價,比雜交水稻種植所增加的產量還要大。[1]這同樣是“主糧”結構不合理而釀成的悲劇。
此外,另一個帶有國際意義的重大生態問題還需要高度關注。時下,西方發達國家的“主糧”結構,同樣也極為單一,僅包括小麥、水稻、玉米和馬鈴薯等有限幾個物種。世界上最大的四家糧食跨國公司,均是按這樣的模式去主導了國際“主糧”貿易。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后,美國鑒于中國大豆消費量巨大,才致力于在該國擴大轉基因大豆的種植,產品專門銷往中國。其后,又將轉基因大豆的專利轉讓給巴西,在巴西種植后向中國傾銷。結果,中國和巴西的生態結構都因此而引發了重大的損失。中國的傳統大豆品種,也由此遭受了嚴重的打擊。
這一事件最值得注意之處還在于,如果我國的“主糧”結構依然單一,國際糧食貿易就會輕而易舉地左右中國的糧食市場。如此一來,不僅中國的經濟會遭受嚴重的沖擊,生態結構也會因此而蒙受難以預測的損失。但如果“主糧”構成盡可能多樣化,那么國際糧食貿易對中國的沖擊,以及中國的生態損害都可以降到最低。同時,中國大量的非轉基因糧食,在國際糧食貿易中,還會因其符合“生態食品”的標準而獲取巨額報償。時至今日,歐洲各國依然抵制轉基因農產品,在這種背景下強化我國傳統農產品的生產和消費,本身就是一個明智的做法。今后中國“主糧”結構的優化,看來需要更多地向歐洲各國學習,才能擺脫美國糧食壟斷以及對我國的糧食安全和生態安全造成的雙重壓力。
除了物種品種構成外,“主糧”作物對生態環境的適應,也是評估“主糧”結構是否合理的必備內涵。我們必須牢記,每一種糧食作物,其生物屬性都具有極高的穩定性,在不合適的生態背景下種植特定的糧食作物,不僅生產成本高、產量低,而且還會威脅到生態的安全。我國是一個山地環境構成比例極大的國度,在山區坡面推廣種植玉米,不僅會釀成嚴重的林糧爭地的尖銳矛盾,還會引發水土流失和山體滑坡等嚴重的自然災害。[2]我國烏蒙山區之所以會成為水土流失的重災區,即是歷史上無原則地大面積推廣玉米種植釀下的生態隱患。但時下烏蒙山區的各族民眾,依然大面積種植玉米作牲畜飼料。這樣的經營范式純屬多此一舉,在“主糧”結構調整優化中,對這種做法也必須高度關注,盡可能消除其負作用。事實上,烏蒙山區各族民眾,根本不需要大費周折地種植玉米作飼料,因為當地本來就具有眾多的優質牧草。這其間僅是一個觀念的轉變問題。而如今要處理這樣的問題,難度不大,但生態治理成效顯著。因而在今后的“主糧”結構評估指標設計中,必須把這樣的問題包容在內。
在我國,水稻最佳的種植范圍極為有限,但時下的水稻種植區域,不僅推廣到東北,還推廣到內蒙古的阿拉善腹地,甚至有研究者還致力于將水稻推廣至雅魯藏布江河谷。這樣做的結果,水稻的總產量雖然可以提高,但由此而引發的生態問題,同樣會抵消其生態效益,還會誘發無窮的生態后患。
有鑒于此,“主糧”結構的優化,不僅需要體現為提高物種和品種構成的多樣化,還必須針對我國的生態結構特點,嚴格控制各種作物的種植比例和產量比例。以此確保不同的“主糧”,都能夠種植到它最理想的生態環境之中。而不能憑借習慣或者主觀的判斷,去追求“主糧”產品的短期市場價值,更不應當把心目中的“主糧”,推廣到它不適宜種植的生態系統之中,而最終在無意中制造生態災變。因此,今后制定“主糧”結構優化的指標時,必須將“主糧”物種和品種的最佳適應范圍、最佳種植背景納入其中;也需要劃定“生態保護紅線”,不適宜種植的地帶明令禁止種植。時下,沒有將這一問題納入評估指標,本身就是一種失誤,應當及時啟動新的評估辦法,對此前的失誤加以匡正,并以此推動我國“主糧”種植的全國性協調。
生產“主糧”作物的農耕體制對生態建設而言,也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同一物種,甚至是同一個品種的糧食作物,在完全相同的生態背景下種植,由于耕作體制不同,其產量和質量也完全不同,其生態影響更會各不相同,有的對生態建設極為有利,有的則會帶來始料未及的生態負效應。因而,“主糧”結構的優化,還必須關注耕作體制的科學性和合理性。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早就明確指出,西方的集約農業耕作體制,主要是針對溫帶草原建構起來的合理制度,這樣的制度并不適應于其他的生態系統,也不值得其他地區的國家和民族去抄襲和模仿。[3]時下,美國正在大力推廣“免耕法”,而我國的糧食種植,卻在致力于推廣機械化操作和大規模集約經營,其間的走向恰好相反。而值得反省的教訓又非止一端。
在歷史上,沙米曾是我國內陸干旱地帶的“主糧”作物。這種作物可以在半流動山丘上規模性種植,產出的沙米價值極高,其桿蒿還是牲畜的飼料。更具價值的是,這種作物還能防風固沙,極具治理草地退化和土地沙化的生態功效。唐代河西四郡的稅賦糧種,就包含有沙米在內,[4]并被其后的各個王朝沿用。清代康熙皇帝御駕親征討伐葛爾丹時,漠南蒙古各部提供的軍糧,主要就包括沙米。[5]近年來,環保部門鑒于沙米具有防風固沙的生態效益,并為此投入了巨資,耗費了多年的精力,希望推廣沙米的種植,以便收到治理土地沙化災變的成效。但研究的取向和采用的種植體制,卻抄襲自禾本科糧食的種植辦法。結果,沙米的萌發率和成活率極低,根本無法達到生態治理的目標。而我國蒙古族和其他好幾個游牧民族,使用他們種植沙米的傳統農耕體制,則可以輕而易舉地大面積種活沙米。這應當是一個慘痛的教訓,其失誤僅僅是來自對農耕體制的誤用,而沒有做到因地制宜。因而其失敗,是從研究起步時就種下的禍根。如果仿效這些少數民族的傳統農業遺產,將其發揚光大,或者設計同等功效的耕作體制,那么不僅沙米可以升格為“主糧”,沙地災變的治理,也可以步入一個新的臺階。
“架田”是我國南方利用固定水域實施農業耕作的“農業文化遺產”。類似的農耕體制,在墨西哥的阿茲特克人中目前還在使用。[6]但中國自宋代以后,各朝政府為了行政的需要,明令禁止這種農耕體制的實施。隨著時代的演進,當下中國水資源的維護,水體質量的保障,正在成為可持續發展的瓶頸。而架田種植在這方面的功效,至今沒有找到替代的辦法。我國大型水庫修建的數量日趨增多,相關部門又把這些水庫的水面租賃給企業或個人,供作網箱養魚之用,并因此釀成水體的嚴重污染和水資源的無效蒸發。但如果重新啟用“架田”種植,不僅可以維護我國的耕地紅線,還能坐收水環境優化的成效。當前沒有將這樣的農耕體制,納入“主糧”結構的評估框架,同樣是一種無意中犯下的失誤。同樣的事例不勝枚舉。
我國沅江流域的各族鄉民,長期執行“林糧兼作”體制,“主糧”種植不會干擾到對森林生態系統的維護。我國嶺南地區的各民族,在歷史上早就擁有一整套在森林環境中種植糧食作物的成熟農耕體制,比如在森林中配種木本糧食作物,如桄榔木、木薯等;還在林下種植天藍星科的芋屬作物等。這樣的農耕體制,不但不會引發林糧爭地的矛盾,還可以做到“主糧”種植與森林維護的和諧兼容。我國涼山地區的彝族,利用牧場的間隙配種圓根和燕麥,也是能夠兼顧到“主糧”種植和生態維護的農耕體制。
為此,評估“主糧”結構的優劣,必須將農耕體制納入其中。但凡農耕體制與種植的糧種相互適應,又能兼顧到所利用的生態系統,就應當視為“主糧”結構優良。反之,就應當視為“主糧”結構的不合理。有了這樣的評估指標,才能推動糧食安全和生態安全建設的兩全其美。然而,“主糧”結構的優化,由于涉及到歷史的積淀和生態的適應等一系列問題。以至于要完成這樣的使命,必然要耗費較大的投資,需要經歷相對漫長的歷史歲月。為此,“主糧”結構的優化,還必須兼顧到“主糧”生產的當代創新空間這一棘手問題。
就總而論,我國確實是“重要農業文化遺產”最為豐富的國度。但這些遺產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因各式各樣的社會原因而失傳,即令能夠活態傳承至今,其生產規模也無法達到優化“主糧”結構調整的預期目標。可是出于我國生態建設的考慮,只要這些傳統的“農業文化遺產”能夠為我國當前生態建設所需要,都具有發掘和創新利用的必要;只要在當前的條件下能夠實現創新,就有必要納入“主糧”規劃當中去組織推廣和發展。
小米本來是遠古華夏居民的“主糧”。在其后漫長的歷史歲月中,僅僅是因為中央政權的政治和經濟中心逐步向南、向東遷徙,原來的小米主產區逐步被邊緣化,其“主糧”地位也就隨之而喪失。但這種作物非常適應于在干旱的疏樹草地生態系統中大面積推廣種植,并都能對這樣的生態空間發揮生態維護的效能,其潛在的空間又幾乎可以覆蓋我國四分之一的國土面積。因而,發掘創新利用小米,其生態價值極大。據文獻記載,我國漢代推行的“代田法”,就是專為這種作物而設計。[7]“代田法”的技術操作,只需創新設計農業機械化的設備,完全可以實施機械化操作,只要能夠做到這一步,將小米一類的作物確立為“主糧”,完全可以實現。
我國歷史上的某些“主糧”作物,特別是塊根類,如桄榔木那樣難以加工和保鮮的糧食作物對我國異質性較大的生態背景具有較高的適應能力,尤其是對喀斯特山區、水土流失地區和石漠化災變區等特殊的生態環境維護而言,幾乎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歷史上卻受運輸條件、加工條件和國家行政管理條件的限制,而不能成為國家“主糧”。當下的運輸、保鮮和加工基本不成問題,而耕作體制的現代化,卻又成了亟待解決的創新領域。鑒于當代農業機械主要是針對禾本科糧食作物而設計,要創新利用塊根類的糧食作物,確實存在著諸多技術和科研問題。但這樣的問題,并非不能改變,而是此前的研究取向沒有關注到這一緊迫需要而已,只要科研取向做出有效的調整,這些糧食作物的機械化生產同樣可以做到。
舉例說,我國涼山地區的彝族,是采用“糞種法”種植圓根和馬鈴薯,其單位面積產量并不比高產的雜交水稻低。[8]但“糞種法”卻要受到牲畜擁有量的限制,否則就難以提供足夠的脫水廄肥。實施這一耕作體制的核心技術原理,僅僅是為了規避地溫偏低的自然缺環。在當代技術和材料裝備的基礎上,要規避這樣的自然缺環,其實并不存在問題,只需要脫離地表,建構懸空的高標準耕地,也能收到同樣的生態適應實效。而且所產生的經濟效益,完全可以抵消較高的成本投入。作出這樣的創新應對,完全可以使我國此前無法實行農耕的高海拔地帶,也能擁有穩定的耕地。
從創新的視角去規劃我國的“主糧”結構,就可以使很多歷史上失傳或者瀕危的“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得以發揚光大,并兼收生態維護的成效。為此,對傳統的農業遺產全面分析和應對其創新空間的大小,也應當納入“主糧”結構優化的評估框架內去評估考量,才有助于“主糧”結構的優化,也才能夠在生態建設中發揮其關鍵性的作用。
三、亟待應對的幾大挑戰
當前我國按照慣例運行的“主糧”結構,主要是顧及到行政管理的方便和考慮到糧食安全的維護。但這種做法,卻與我國長期糧食生產的實情相左。查閱清代的地方典籍就不難發現,在國家規定的“主糧”框架內,當時的各府州縣,還包括當時所稱的“蕃部”,無一不擁有琳瑯滿目的“主糧”作物。當時朝廷雖明文規定有稅收“主糧”糧種,但同時也極大地寬容,甚至是支持適合地方的糧食作物種植。這些糧種,也始終占據著當地的“主糧”消費地位。這顯然是一種既關系到糧食安全,又兼顧到生態維護的“主糧”結構優化。
然而一段時間以來,我們僅僅將稻米、小麥和玉米確立為“主糧”。近年來,國家才將馬鈴薯作為“主糧”作物去加以規劃和種植。這當然是一個好的開頭,但顯然還遠遠不夠。為了兼顧到生態建設的需要,“主糧”的物種構成還需要進一步多樣化。原則上,在二十世紀初,曾經處于“主糧”地位的作物,都理應納入“主糧”結構去加以發展和穩定種植。如此一來,就可以做到在確保糧食安全的基礎上,同時收到生態維護的實效。
正因為時下我國的“主糧”結構過度單一化,其結果導致了糧食作物的壓庫,生產能力的懸置,農業生產成本居高不下,盈利空間越來越小。而市場緊缺的糧種,特別是那些名特優糧食產品卻供不應求,形成了市場供給的“短板”。這樣的現實都一再警示我們,“主糧”結構的物種構成和品種構成亟待優化。而阻礙這一優化的關鍵制約因素,不在于生態環境,也不在于技術條件,而在于觀念上抱殘守缺。
當前,我國生態建設的任務極其艱巨,我國政府先后提出了“退耕還林”“退耕還草”和“退耕還湖”的正確決策,也收到了一定的實效。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也暴露出了一些新問題。事實上,在我國的“重要農業文化遺產”中,就有很多糧食作物的生產,不僅不會與還林、還湖、還草等措施相互沖突,反而還具有提高生態建設成效的積極作用。
桄榔木、木薯,還有芋屬塊根糧食作物,都可以在“還林”后的森林中正常種植。歷史上作“主糧”用過的葛根、山藥、版腳薯等,不僅可以與森林相互兼容,還可以作為“還林”的先鋒作物去加以利用,對提高“還林”的成效具有重要作用。沙米和粟類作物,完全可以在“退耕還草”后實施規模種植。這些作物不僅與當地的草原能夠相互兼容,還能與當地各族鄉民從事的畜牧業相合拍,從而更有利于當地受損草原生態系統的快速恢復。實施“架田”種植也與“退耕還湖”不相矛盾,不但能夠凈化水質,防治水污染,在干旱地區還能抑制水資源的無效蒸發。
就這個意義上說,從事生態建設就不一定單靠行政和工程技術手段去完成,創新利用“重要傳統農業文化遺產”,推動“主糧”結構的優化,反而可以降低生態建設成本,提高建設的實效。應該做到,在我國的國土范圍內,只要糧食作物的最佳適應面積超過一萬平方公里,就有必要納入“主糧”結構中去加以規劃種植,以期穩定其用地面積和產量。這樣去優化“主糧”結構,才能確保我國當前的生態建設,既能夠得到高效的利用,又能得到較好的維護,生態建設也就能降低成本,提高成效。
為了確保“主糧”結構的優化能兼顧到生態建設的需要,其間必然存在著諸多亟待深入研究的科學問題。而當前我國對“主糧”作物的研究,卻一直按社會習慣去加以規劃,主要是對有限的幾種糧食作物展開深入研究,對歷史上曾經有過的“主糧”作物,以及相關的“農業文化遺產”和耕作體制,卻長期處于科學研究的閑置狀況。相關的科學研究,根本沒有將這些內容納入科研范疇,即令有零星的涉及,也需要亟待深入和完善。而這已經成了我國“主糧”結構優化的關鍵制約因素,若不調整這樣的科研取向,“主糧”結構的優化同樣會寸步難行。
就終極意義上說,任何科研活動,都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社會活動。以至于具體的農業科研活動,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都會受到傳統“主糧”觀念的規約和左右,從而導致研究取向和研究思路的偏頗。比如,西漢晚期推行的“代田法”,不管是農業史專家,還是歷史學家,都會做出充分的肯定,這在當時確實是一項先進的發明。但受到當代“主糧”結構的習慣性干擾后,對此展開的科學研究都很少關注到,“代田法”對我國西北干旱地帶的疏樹草地生態系統具有極高的適應能力,對規模化的農事耕作也不缺乏其科學性和合理性。在當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水平上,發揚光大這樣的傳統農業遺產,本來不該成為問題,但卻因為受到習慣性的思維干擾,導致相應的科學研究長期缺位。同樣,對我國南部山區的農業研究,也會在無意中出現了研究取向上的偏頗。研究者總是過分地關注農業機械的小型化,以及拆裝搬運的便利化,而從不考慮另建適合山區作物種植的機耕體制,更不考慮換種能夠與特殊山區環境相適應的作物,并創新利用與此相關的傳統耕作體制。這更是一個嚴重的失誤。
舉例說,在我國西南嚴重石漠化的喀斯特山區,在歷史上當地各民族是通過農林牧副的復合經營,憑借“免耕法”去種植特種“主糧”,如桄榔木、葛藤等等。其后,僅僅是因為不能與國家賦稅制度相接軌,這份農業遺產才在無意中被窒息。時下的研究卻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反而是大動干戈去規劃設計超小型的農業器具,卻不會考慮創新利用傳統的“免耕法”。而近年來美國農業部門正在大力推廣的“免耕法”,正與我國西部山區的“免耕法”具有內在的同質性。
事實上,中國的南部和西南部山區,強行推廣禾本科糧食作物種植不是辦不到,而是會引發諸多的生態問題。但如果改種歷史悠久的傳統糧食作物,如上文提及的桄榔木、葛根、芋頭、木薯,卻可以收到生態建設的實效。而改種這樣的糧食作物,并確立為“主糧”去加以規模性發展,那么以禾本科糧食作物為對象而設計的農業機械就失去了用武之地。但如果改用索道運輸,情況則會大不一樣。因為這些適合于山區發展的糧食作物,通常都不需要全面翻地,也不需要頻繁地除蟲、施肥和除草,基本上都是實行“半野化”種植,為此付出的主要勞力投入,都集中在收割環節。而就收割環節而言,山區采用索道運輸,可以做到投資少,操作便利,而且對生態環境的沖擊還可以降到最低限度。因而,要優化我國的“主糧”結構,確實需要作出科學研究取向的調整。但這樣的調整,必然要受到現存“主糧”結構造成的干擾,兩者之間互為因果,相互牽制。最終會使得,沒有觀念上的更新,就不會有科學研究取向的調整,沒有科學研究的新進展,也無法支撐“主糧”結構的優化。這反倒成了亟待解決的關鍵性難題,如果不及時加以化解,相關制約因素將難以排除。
“主糧”結構的定型,既是歷史發展的產物,同時又會制約其后的歷史發展。其中,消費習慣的調整和與時俱進就不容忽視。現有的“主糧”結構均習慣于將小麥、稻米和玉米以外的糧食作物,不加區別地視為“雜糧”,甚而加以貶低。但隨著中國的崛起和人民生活的日趨富裕,三大“主糧”的人均消費水平,特別是城市人口所表現出來的消費水平,比之于改革開放前,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遷。“主糧”消費在食物中所占的比例,已經降到不足四分之一的水平。[9]與此同時,對所謂“雜糧”的需求,卻出現了難以置信的反彈。而國家的糧食管理,卻依然在不計成本地大規模儲糧避荒,儲集的糧食依然定位于“三大主糧”和大豆,由此而耗費了大量的糧食保管支出。這不僅是經濟上的不合理,也與生態建設的實際需要背道而馳。此外,還會進一步誘導人們消費心理的變態,富裕起來的人們不再看中中國土產的“主糧”,而是更看中進口的糧食產品。如此一來,勢必加劇中國生態建設的難度,還會增加生態安全的風險。在“主糧”結構優化的目標下,主動消費中國產出的琳瑯滿目的“雜糧”,特別是那些與生態環境直接關聯的“雜糧”,本身就為中國的生態建設做貢獻。上文提及的沙米、桄榔木、葛藤等,都可以體現這一客觀價值。
由此看來,“主糧”結構的優化,不僅要對付科研問題、技術問題、生態問題,還得對付消費心態和社會價值觀所帶來的習慣性障礙。相關的決策應責無旁貸地發揮關鍵作用,引導我國民眾樹立理性消費多物種糧食的正確觀念。中國民眾在糧食消費中,必須做到需要為中國的生態建設承擔,而且很容易承擔起的責任來。
上述幾個必須應對的挑戰,若作出有效地應對,我國“主糧”結構的優化,以及與此相關的對策,才能一并落到實處。理由全在于,“主糧”結構的優化,不是單純的農業問題,而是與生態建設休戚相關的關鍵問題,只有將“主糧”結構的優化與生態建設捆綁起來,協調推進,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和生態建設才能相得益彰,互為補充,互為支持,和諧共榮。
四、結論與討論
長期以來的慣例,我們都是將“主糧”結構與生態建設,作為相互獨立的問題去對待,而沒有注意到這兩者之間的內在關聯性。以至于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主糧”結構的調整與生態建設總是難以相互兼容,甚至還會出現針鋒相對的矛盾和摩擦。盡管這是歷史和習慣延伸的結果,但對生態建設極為不利。
需要指出的是,我們這里要強調的農業是廣義上的大農業,理應包括農、林、牧、副、漁,以及狩獵采集在內的人類經濟生活方式。這里受篇幅所限,僅就其關鍵性和典型性,對“主糧”結構的優化展開探討。以便讓社會各界注意到,農業生產并不僅僅是一個確保生存的基礎產業,而應該是生態建設中必須加以兼顧和創新利用的關鍵環節。“主糧”結構的優化,不僅對農業本身至關重要,對生態建設也同樣至關重要。“主糧”結構得以優化,不僅可以坐收生態建設的實效,而且可以支持生態建設項目的順利推行,及建設成效的提升;“主糧”結構不合理,不僅會給農業本身造成損害,同時還可能壓低,甚至抵消生態建設的實效。兩者之間的辯證統一,本身就應該成為生態建設的有機構成部分,而決不允許農業生產部門和生態建設部門各自為陣,甚至相互摩擦和對立。
不過,要真正做到這一點,需要面對的困難卻非止一端。思想觀念的轉型,基礎裝備的完善,科研取向的調整,一項也不容疏忽。原因在于,“主糧”機構的優化,本身就是一項社會性的系統工程,需要改變的不是一個單方面的技術問題,或者是政策調整問題,而是需要全社會相互配合,協同推進,才能收到成效。因而,社會各界能夠注意到“主糧”結構優化與生態建設的內在關聯性,本身就是一項重大的突破。這足以表明,符合時代的價值觀得到了應有的關注和認同。接下來,雖然還會有諸多的困難,但只要社會各界齊心協力,那么歷史積淀下來的各種障礙因素,具體創新利用的科學探討,科學研究取向的調整和具體技術的完善,是可以次第落實的。
[1]朱有勇.利用水稻品種多樣性控制稻瘟病研究[J].中國農業科學,2003(5):521-527.
[2]張振興.論清代在西南山區推廣玉米種植的生態后果[J].原生態民族文化學刊,2010(3):40-47.
[3][美]西奧多·W·舒爾茨.改造傳統農業[M].梁小民.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
[4]唐耕耦,陸宏基.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第一輯)[M].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1990:2.
[5]《清高宗實錄》卷14[Z].雍正十三年.
[6]伍磊,吳合顯.漂浮農業在當今中國的實用價值初探[J].原生態民族文化學刊,2012(3):8-13.
[7]邵侃.“代田法”新解——漢族農業遺產的個案研究[J].原生態民族文化學刊,2010(2):9-15.
[8]楊庭碩,等.彝族文化對高寒山區生態系統的適應——四川省鹽源縣羊圈村彝族生計方式的個案分析[J].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1):27-33.
[9]汪希成,吳昊.我國糧食供求結構新變化與改革方向[J].社會科學研究,2016(4):130-135.
(責任編輯 王光斌 )
Optimization of Staple Crop Structure: Another Key Link for Modern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YANG Tingshuo, GENG Zhongyao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Hunan 416000, China)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s a connection link for balancing operation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al ecological systems. Optimization of staple crop structure is closely concerned with the promotion in harmonious degree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al ecological systems. During modern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people are mostly used to relying and focusing on engineering techniques, or establish and expand natural conservation areas to drive the ecological rehabilitation. Such endeavor is originally undisputable but far from enough. If the staple crop structure is not reasonable, it will bring more direct and far-reaching impact and damage for ecological structure. Therefore, it is a mistake and bias in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thinking without paying high attention to the optimization of staple crop structure, which needs promptl adjust to avoid suffering great losses and disasters.
staple crop structure;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key link
S181
A
1674-9200(2017)04-0001-07
2017-06-08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西南少數民族傳統生態文化的文獻采輯、研究與利用”(16ZDA157)階段性研究成果。
楊庭碩,男,貴州貴陽人,吉首大學終身教授,主要從事生態人類學研究;耿中耀,男,貴州威寧人,吉首大學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生態人類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