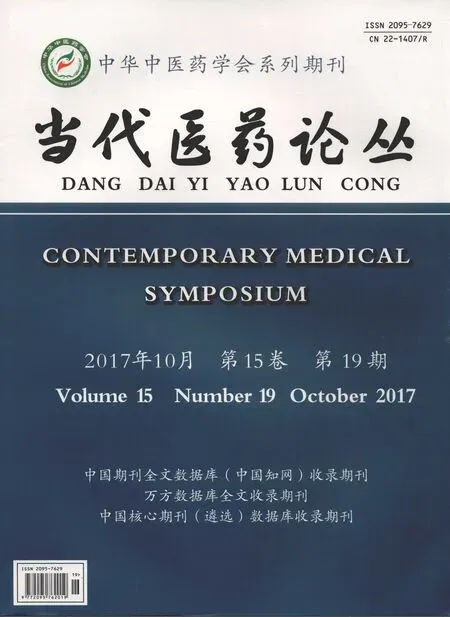皮膚組織工程在修復創傷皮膚中的臨床應用
曾紅菊
(武漢大學醫院外科,湖北 武漢 430072)
皮膚組織工程在修復創傷皮膚中的臨床應用
曾紅菊
(武漢大學醫院外科,湖北 武漢 430072)
皮膚是人體最大的器官。皮膚在受到創傷后愈合的過程中往往會導致創面收縮及瘢痕形成,進而可引起一系列局部功能、外觀和心理方面的并發癥。目前,臨床上在修復皮膚創傷時尚缺乏有效的手段。皮膚組織工程作為組織工程的一個分支,具有全面修復受損皮膚結構和功能等作用。近年來,皮膚生物學、生物材料科學和工程技術都得到了迅速的發展,皮膚組織工程技術也取得了一定的突破。本文主要探討皮膚組織工程在修復創傷皮膚過程中的臨床應用效果。
創傷修復;皮膚組織;工程
皮膚是人體最大的器官,覆蓋人體的表面并占人總體重的8%左右。皮膚由表皮、真皮、皮下組織和皮膚附屬器官等構成,具有防護、吸收、感覺、體溫調節、代謝、分泌和排泄等功能。它與外界環境直接接觸,能夠不斷接收外界的物質信號并適應其動態變化。人的皮膚在受到損傷后常會引起一系列功能、外觀和心理方面的并發癥。目前,臨床上在修復皮膚創傷方面尚缺乏有效的手段。皮膚組織工程作為組織工程的一個分支,具有促進多能干細胞、生物活性分子等對受損的皮膚進行修復、全面修復受損皮膚的結構和功能等作用。近年來,皮膚生物學、生物材料科學和工程技術都得到了迅速的發展,皮膚組織工程技術也取得了一定的突破。本文主要探討皮膚組織工程在修復創傷皮膚中的臨床應用效果。
1 皮膚創傷的原因及現狀
人的皮膚常會直接暴露于存在有害微生物、熱力、機械性或化學性因素的環境中,因此易受到損傷。人體在罹患疾病、發生急性創傷或接受手術干預時都可能導致皮膚創傷。皮膚在發生創傷后愈合的過程中往往會引起創面收縮及瘢痕形成,進而可導致一系列功能、外觀和心理方面的并發癥[1]。在所有的皮膚創傷中,皮膚燒傷最具有破壞性。皮膚燒傷不僅可使患者發生生理上的創傷和殘疾,還可使其出現情感及心理障礙[2]。發生嚴重的皮膚燒傷和慢性不愈合的皮膚創傷可使患者出現不可逆的功能障礙,并可使其因接受長期的治療和護理而承受沉重的經濟負擔。
2 皮膚創傷的修復
人的皮膚因受到創傷而導致部分細胞和組織喪失后,會自發地對缺損的細胞和組織進行修復。參與修復皮膚創傷的主要成分包括細胞外基質(ECM)和各種細胞。皮膚創傷的修復可概括為以下兩種不同的形式:1)皮膚的再生。皮膚的再生是指由受損皮膚周圍的同種細胞對其進行修復,使其不同程度地恢復原有的結構與功能。皮膚的完全再生是指,皮膚在再生的過程中完全恢復原有的結構與功能。2)皮膚的纖維性修復。皮膚的纖維性修復是指由受損皮膚中的纖維結締組織對其進行修復。受損的皮膚在發生纖維性修復后會形成瘢痕,故纖維性修復也被稱為瘢痕性修復。多數情況下,皮膚創傷的兩種修復形式會同時存在。受損皮膚的正常修復涉及4個相互重疊又明顯不同的階段:第一階段,受損的皮膚可發生與許多免疫細胞、細胞因子、趨化因子和生長因子有關的止血和炎癥反應;第二階段,受損的皮膚可發生細胞增殖、遷移及角質細胞的重上皮化;第三階段,受損的皮膚可發生受VEGF(血管內皮生長因子)調控的血管生成;第四階段,受損的皮膚可發生由各種miRNAs、生長因子及連接蛋白參與的重塑[3]。
3 組織工程皮膚產生的背景
皮膚創傷,特別是皮膚全層燒傷的修復一直是困擾臨床醫生的棘手問題[4]。燒傷后皮膚的再生和功能修復是進行燒傷學研究的焦點。較淺的燒傷創面或小面積的皮膚全層缺損,主要通過殘存皮膚附件的干細胞再生或臨近皮膚的上皮細胞遷移而逐漸愈合。在發生大面積燒傷或廣泛深度的皮膚創傷造成的皮膚全層缺損后,受損皮膚固有的表皮干細胞壁龕被破壞,其創傷愈合是通過傷口邊緣細胞的遷移和收縮來完成的,這可導致重大的攣縮形成,使病人發生嚴重的功能障礙,承受較大的痛苦[5]。皮膚移植是覆蓋大面積皮膚燒傷或皮膚缺損創面的重要手段。目前,自體皮膚移植手術是治療此類皮膚創面的首選療法。但是,大面積皮膚燒傷或皮膚缺損患者的自體皮源往往嚴重不足,在接受自體皮膚移植手術時其皮膚上會出現新的創面,其創面若未能及時得到有效的覆蓋會發生生命危險。為了解決這一問題,能替代人體自身皮膚治療大面積皮膚燒傷或皮膚缺損的組織工程皮膚便應運而生。
4 組織工程皮膚的三要素
皮膚組織工程作為組織工程(Tissue engineering,TE)的一個分支,是一門新興的邊緣學科。組織工程皮膚是最早被開發和目前最接近成功的組織學產品,也是世界上第一種獲得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批準,被應用于臨床上的組織工程產品。種子細胞、生物支架材料和生長信息作為組織工程的三要素,對皮膚組織工程同樣適用。
4.1 種子細胞
組織工程皮膚的種子細胞是指能夠發育成皮膚組織或其細胞成分的培養細胞。根據來源的不同,種子細胞可分為以下兩類[6]:1)來源于皮膚細胞的種子細胞,包括角質形成細胞(keratinocytes,KC)、皮膚成纖維細胞(fibroblast cells,FC)、 表 皮 干 細 胞(epidermal stell cells,ESCs)、黑素細胞(melanocytes,MC)。2)來源于非皮膚細胞的種子細胞,包括胚胎干細胞(embryonic stem cells,ESCs)、誘導多能干細胞(Inducible pluripotent stem cells,iPSCs)、間充質干細胞(包括骨髓間充質干細胞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BMSCs和脂肪間充質干細胞adipose-derived stem cells,ADSCs)、血管內皮細胞(endothelial cells, EC)、羊膜細胞(human amniotic membrane,AM)等。目前,組織工程皮膚中種子細胞的主要來源是患者的自體細胞、異體細胞和異種細胞。來源于患者自身的種子細胞具有最低的免疫原性和疾病傳播率,而且具有再生為新的皮膚組織的能力,用其修復皮膚創傷的效果最為理想[7]。種子細胞中的干細胞在受損皮膚愈合過程中發揮的作用包括以下幾種:1)在上皮的再生中可起到多種作用;2)其中具有多分化潛能的祖細胞,可從間充質細胞向上皮細胞表型轉化;③可作為血管再生時內皮細胞的前體細胞;④可表達成纖維細胞特異性膠原蛋白基因,促進創面重塑;⑤可促進色素再生;⑥可促進毛囊再生[8]。
4.2 生物支架材料
組織工程皮膚的生物支架材料是指用于支撐細胞生長為一個完整組織的框架材料。根據來源的不同,組織工程皮膚的生物支架材料可分為三大類:1)天然聚合物。⑴天然多糖聚合物,包括細菌纖維素、殼聚糖、透明質酸等;⑵天然蛋白質,包括絲素蛋白、纖維蛋白凝膠、膠原蛋白等。2)細胞外基質,包括脫細胞真皮基質、脫細胞羊膜及小腸黏膜下層。3)復合生物材料,包括天然聚合物+天然聚合物、天然聚合物+細胞外基質、天然聚合物+合成聚合物。使用生物支架材料進行皮膚創傷修復可能導致異物反應,包括炎癥反應、感染、血栓形成及栓塞。理想的生物支架材料應具備以下條件:1)具有一定尺寸的三維多孔結構;2)具有生物可降解性且速率可控;3)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4)不會引起炎癥反應;5)具有可塑性和一定的機械強度。此外,生物支架材料在濕態時也應具有可操作的力學性能及一定的柔韌性,能夠與機體緊密貼合,且不會對機體造成機械損傷。理想的生物支架材料應該類似于機體的細胞外基質,能夠支持細胞的粘附、增殖和成熟,促進創傷的愈合、肉芽組織的形成、纖維化、血管化和上皮再生[9]。
4.3 生長信息
哺乳動物的上皮組織器官在受到創傷后,修復的過程很復雜,可受到眾多分泌因子(包括細胞因子、生長因子和趨化因子等)的影響[10]。目前,許多研究證明,很多細胞因子、生長因子、趨化因子、轉化因子及新鑒定的生物活性分子都可以提高受損皮膚的愈合質量,組織中生長因子和細胞因子的減少則可明顯延遲皮膚創傷的愈合且促進瘢痕形成[11]。
5 組織工程皮膚的臨床應用及挑戰
目前,治療皮膚創傷仍是臨床上面臨的一個挑戰。有關信號控制創傷細胞和分子行為的新知識,促進了多能干細胞、生物活性分子在治療皮膚損傷中的應用,減少了皮膚再生中疤痕的形成[12]。最近,皮膚生物學的發展強調了細胞與細胞間的相互作用在表皮形態發生過程中的重要性[13]。這導致了高度復雜和創新的3D皮膚替代物的產生。3D皮膚替代物可模擬人體皮膚的結構和功能且含有毛囊、毛細血管網絡、感覺神經、脂肪組織和皮膚色素[14]。通過模擬局部解剖部位皮膚生長的環境,不同的種子細胞和ECs可通過相互作用促進血管生成及組織工程皮膚的血管化[15]。
臨床證據表明,組織工程皮膚(Tissue-engineering skin,TES)中包含的大多數細胞經移植后存活的時間不到1個月[16]。目前,大部分的TES在受損皮膚愈合的過程中只能作為一種臨時替代物。缺乏直接的血液供應和發生免疫排斥反應是阻礙同種異體TES永久存活的兩個主要問題。隨著創傷愈合機制的闡明,多種細胞的恰當組合及其相互作用在永久性TES的構建及皮膚創傷的初始治療中可能會發揮重要的作用。我們相信,隨著皮膚生物學、生物材料科學和工程技術的發展,TES療法在治療皮膚創傷方面終將達到與自體皮膚移植術等同的臨床效果。
[1]Jean, J., et al., Effects of serum-free culture at the air-liqu id interface in a human tissue-engineered skin substitute. Ti ssue Eng Part A, 2011. 17(7-8): 877-88.
[2]Pless, B., Injury prevention: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BMJ,1998. 317(7173): 1665A.
[3]Peng, L.H., et al., Genetically-manipulated adult stem cells as therapeutic agents and gene delivery vehicle for wound rep air and regeneration. J Control Release, 2012. 157(3): 321-30.
[4]Pellegrini, G., et al., The control of epidermal stem cells (ho loclones) in the treatment of massive full-thickness burns wit h autologous keratinocytes cultured on fibrin. Transplantation,1999. 68(6): 868-79.
[5]Eldardiri, M., et al., Wound contraction is significantly reduce d by the use of microcarriers to deliver keratinocytes and fi broblasts in an in vivo pig model of wound repair and regener ation. Tissue Eng Part A, 2012. 18(5-6): 587-97.
[6]Bi, H. and Y. Jin, Current progress of skin tissue engineering:Seed cells, bioscaffolds, and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Burns Tr auma, 2013. 1(2): 63-72.
[7]Anjum, F., et al., Biocomposite nanofiber matrices to support ECM remodeling by human dermal progenitors and enhanced wo und closure. Sci Rep, 2017. 7(1): 10291.
[8]Shi, Y., et al., Mesenchymal stem cells: a new strategy for immunosup pression and tissue repair. Cell Res, 2010. 20(5): 510-8.
[9]Bi, H. and Y. Jin, Current progress of skin tissue engineering:Seed cells, bioscaffolds, and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Burns Trauma, 2013. 1(2): 63-72.
[10]Stappenbeck, T.S. and H. Miyoshi, The role of stromal stem ce lls in tissue regeneration and wound repair. Science, 2009. 32 4(5935): 1666-9.
[11]Giannoudis, P.V., C.C. Tzioupis and E. Tsiridis, Gene therapy in orthopaedics. Injury, 2006. 37 Suppl 1: S30-40.
[12]Peng, L.H., et al., Genetically-manipulated adult stem cells as therapeutic agents and gene delivery vehicle for wound rep air and regeneration. J Control Release, 2012. 157(3): 321-30.
[13]Bi, H. and Y. Jin, Current progress of skin tissue engineering:Seed cells, bioscaffolds, and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Burns Tr auma, 2013. 1(2): 63-72.
[14]Liu, Y., et al., Reconstruction of a tissue-engineered skin con taining melanocytes. Cell Biol Int, 2007. 31(9): 985-90.
[15]Hudon, V., et al., A tissue-engineered endothelialized dermis to study the modulation of angiogenic and angiostatic mole cules on capillary-like tube formation in vitro. Br J Dermat ol, 2003. 148(6): 1094-104.
[16]Griffiths, M., et al., Survival of Apligraf in acute human woun ds. Tissue Eng, 2004. 10(7-8): 1180-95.
R722.14+2
A
2095-7629-(2017)19-0017-03
曾紅菊,女,1986年12月出生,籍貫為湖北,碩士,住院醫師,初級職稱,研究方向:真皮替代物的體內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