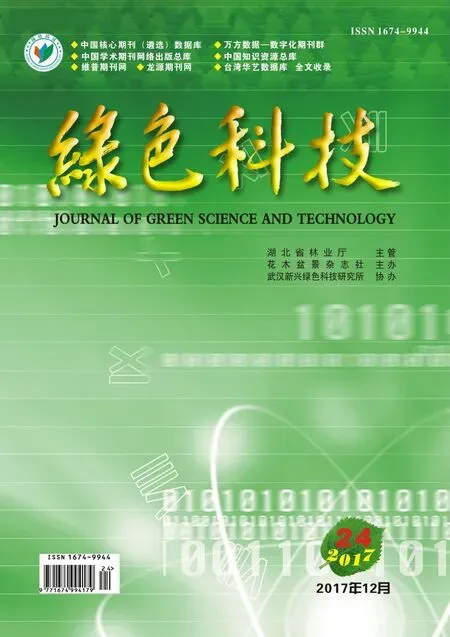民勤不同荒漠植物深色有隔內生真菌分離頻率及其與土壤因子的相關性分析
張琳琳, 賀學禮, 郭亞楠,葛佳麗,王姣姣,李欣枚
(河北大學 生命科學學院, 河北 保定 071002)
1 引言
甘肅民勤地處溫帶大陸性干旱氣候區,東西北三面被騰格里和巴丹吉林兩大沙漠包圍,氣候環境十分惡劣[1]。該地區冬冷夏熱、降水稀少、光照充足、晝夜溫差大,年均降水量110mm,蒸發量高達 2644 mm。由于民勤地區自然條件惡劣,特別是受到水資源條件的限制,許多旱生灌木對該環境有很強的適應性。膜果麻黃(Ephedraprzewalskii)、紅砂(Reaumuriasongarica)、合頭草(Sympegmaregelii)、泡泡刺(Nitrariasphaerocarpa)、珍珠豬毛菜(Salsolapasserine)等植物群落是我國西北極旱荒漠環境中的典型地帶性植被,這些植物屬于超旱生小半灌木或半灌木,具有抗旱性強、耐貧瘠及防風固沙等特征,生活基質多為強度石質化灰棕土或石質荒漠土[2]。在極旱荒漠環境,它們不僅形態結構和生態適應性發生了較大變化,如植株低矮、根系伸長、肉質化等,與其根系共生真菌的分布和活動也會發生改變[3]。植物自身的適應性變化及共生真菌的作用使其成為極旱、極寒、鹽堿、重金屬礦區等惡劣環境中的先鋒植物,在維持生態系統植被穩定性及生產力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樣地及植物群落概況見表1。
深色有隔內生真菌(dark septate endophytes, DSE)是定居在植物根組織細胞內或細胞間隙的一群分類混雜的產分生孢子或無性繁殖的真菌,大多屬于子囊菌門或擔子菌門[4]。DSE真菌具有廣泛宿主范圍和生態分布特性,在干旱、極地、高山等極端環境植物根系有較高定殖率[5]。由于荒漠生態系統在涵養水源、保持水土、物質生產及營養元素循環等方面有重要生態學意義[16],眾多學者進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但對于能與荒漠植物形成共生關系的DSE真菌在宿主植物適應荒漠環境中的作用機制尚缺乏足夠認識。
本研究選擇甘肅民勤荒漠區進行野外考察和系統采樣,比較分析不同土壤因子與DSE真菌分離頻率的相關性,為進一步明確DSE的分布規律及生態功能,特別是在荒漠植被恢復中的作用提供依據。

表1 民勤樣地植物群落概況
2 材料與方法
2.1 樣品采集
2016年7月在甘肅民勤極干旱荒漠選取膜果麻黃、紅砂、合頭草、泡泡刺和珍珠豬毛菜等5種典型植物群落,分別從每個群落選取5株相隔200 m左右,長勢相近的植株;去除枯枝落葉層采集0~30 cm土層土樣和根樣帶回實驗室,土樣陰干后過2 mm篩,土樣用于土壤理化性質測定;根樣用于DSE真菌的分離培養。
2.2 土壤因子測定及DSE分離
土壤溫度(Temp)、濕度(Hum)用土壤溫濕度傳感器測定,有機質(SOC)用重鉻酸鉀氧化法測定,土壤pH值用電位法測定,速效磷(AP)用碳酸氫鈉-鉬銻抗比色法測定,全氮(TN)、全磷(TP)用自動化學分析儀(Smart Chem 200)測定。根據Tarafdar 和 Marschner方法測定土壤酸性磷酸酶(ACP)和堿性磷酸酶(ALP),Hoffmann 和 Teicher方法測定土壤脲酶(U),活性以每克土樣培養1h催化尿素分解產生NH4+-N的微克數(μg)表示。
用無菌水洗去根樣表面塵土,放入75 %乙醇消毒4 min,無菌水沖洗2次,再放入10 %次氯酸鈉消毒2 min,無菌水清洗3次,用濾紙吸去根樣表面水分。將根段剪成1cm左右小段,放入加有抗生素(含50 mg/L氨芐青霉素和50 mg/L硫酸鏈霉素)的 PDA 培養基,每個培養皿放3~5個根段[6]。于27 ℃黑暗條件下分離培養并純化,根據如下公式計算分離頻率:
分離率(IR%)= 分離DSE菌株數/分離根段總數×100%
(1)
分離頻率(IF%)或相對頻率(RF%)=(某種真菌菌株數/分離所得總菌株數)×100%
(2)
2.3 數據處理與分析
用Excel 2007進行數據處理,采用SPSS 19.0 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及spearman相關性分析,采用CANOCO 4.5軟件對土壤因子進行主成分分析(PCA)。
3 結果與討論
3.1 土壤因子主成分分析
對土壤因子各項指標進行PCA排序(圖1),兩個排序軸對物種變量的解釋量達91.3%, 可將其作為主成分軸。其中,第1主成分(PC1)可以解釋變量方差的76.4%,酸性磷酸酶、全氮和全磷對PC1貢獻最大;第2主成分(PC2)可以解釋變量方差的14.9%,pH、堿性磷酸酶和速效磷對PC2起主要作用。綜合來看,磷酸酶、pH和全氮是民勤樣地的主要土壤因子,能綜合反映土壤肥力狀況。

圖1 民勤樣地不同植物群落土壤因子PCA排序
3.2 土壤因子之間及其與DSE分離率的相關性分析
DSE真菌分離頻率與土壤因子相關性分析如表2所示,脲酶與速效磷,土壤有機質與酸性磷酸酶和土壤濕度呈極顯著正相關,全氮與酸性磷酸酶,土壤有機質和速效磷呈極顯著負相關。此外,DSE分離頻率與酸性磷酸酶、土壤有機質、土壤濕度和全磷呈極顯著正相關,與全氮呈極顯著負相關。由此可見,各土壤因子之間及土壤因子與DSE之間具有明顯的相關性,能夠顯著影響DSE真菌的空間分布。

表2 DSE分離率與土壤因子相關性分析
注:*代表顯著性水平為P<0.05;**代表顯著性水平為P<0.01
3.3 討論
DSE真菌廣泛存在于荒漠生態系統,在不同科屬植物中均有定殖。這類真菌不僅能協助宿主植物抵御干旱、嚴寒、鹽堿等逆境脅迫,促進植物對水分及營養物質吸收,還能增強宿主植物對其他生物或非生物脅迫的耐受性[7]。膜果麻黃、紅砂、合頭草、泡泡刺和豬毛菜這5種超旱生灌木在民勤極旱荒漠生境長勢良好并能與DSE形成菌根聯合體,說明DSE可能是荒漠植物適應極旱環境的對策之一。土壤酶是土壤物質循環和能量流動的重要參與者,是土壤生態系統中最活躍的組分之一[8]。土壤磷酸酶、脲酶、蔗糖酶等水解酶活性能夠表征土壤碳氮磷等營養物質的循環狀況。磷酸酶活性是評價土壤磷素生物轉化方向與強度的指標,能將有機磷酸形式水解成無機形式為植物所吸收利用。結合DSE真菌與土壤因子的相關性,建立和完善荒漠土壤環境評價體系,對促進荒漠植被恢復和生態重建具有重要意義。此外,研究極旱荒漠環境中DSE真菌分布規律及種類組成[9],有助于充分理解DSE真菌在荒漠生態系統中的功能和意義。
[1]王曉武,羅 寧,單華佳,等. 民勤4種沙生灌木的干旱脅迫響應特征研究[J]. 干旱區地理,2016,39(5):1025~1035.
[2]劉茂軍,張興濤,趙之偉.深色有隔內生真菌(DSE)研究進展[J].菌物學報,2009,28(6):888~894.
[3]Knapp D G, Kovács G M, Zajta E, et al. Dark septate endophytic pleosporalean genera from semiarid areas[J]. Persoonia: Molecular Phylogeny and Evolution of Fungi, 2015(35):87.
[4]Mandyam K, Loughin T, Jumpponen A. Isolation and morphological and metabolic characterization of common endophytes in annually burned tallgrass prairie[J]. Mycologia, 2010,102(4):813~821.
[5]Rodriguez R J, Redman R S, Henson J M. The role of fungal symbioses in the adaptation of plants to high stress environments[J].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strategies for global change, 2004,9(3):261~272.
[6]Li B K, He X L, He C, et al. Spatial dynamics of dark septate endophytes and soil factors in the rhizosphere of Ammopiptanthus mongolicus in Inner Mongolia, China[J]. Symbiosis, 2015, 65(2):575-84.
[7]An H, Liu Y, Zhao X, et al. Characterization of cadmium-resistant endophytic fungi from Salix variegata Franch. in Three Gorges Reservoir Region, China[J]. Microbiological research, 2015(176):29~37.
[8]劉恩科,趙秉強,李秀英.長期施肥對土壤微生物量及土壤酶活性的影響[J].植物生態學報,2008,32(1):176~182.
[9]Samaga P V, Rai V R. Diversity and bioactive potential of endophytic fungi from Nothapodytes foetida, Hypericum mysorense and Hypericum japonicum collected from Western Ghats of India[J]. Annals of microbiology, 2016, 66(1):229~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