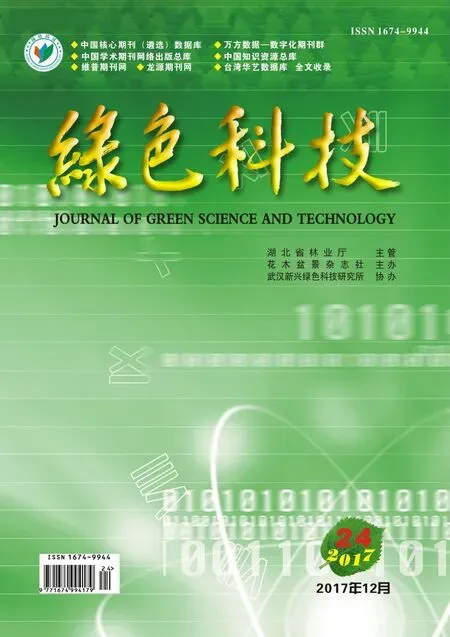武漢市土地利用變化對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影響
艾 雪,杜雪蓮
(貴州財經大學 經濟學院,貴州 貴陽 550025)
1 引言
一直以來,由于各國的國情不同,國際上沒有一個統一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核算理論和方法。20世紀80年代以來,包括美國、加拿大、法國、德國等超過45個國家在內的政府和國際組織或研究機構,先后開展了自然資源核算理論和方法及實施方案的研究和探索。1992年,加拿大生態經濟學家Wiliam.R 最早提出了生態足跡模型,并在1996年被Wackenagel[1]完善成為衡量人類對自然資源的利用程度以及自然界為人類提供生命支持服務功能的方法。其中最有影響的當屬于1997年,Costanza[2]等人發表的《世界生態系統服務與自然資本的價值》,對全球生態系統的服務功能分17種進行賦值計算,這一研究首次對全球生態資本的經濟價值進行確認和評估,雖然計算結果高得令人難以置信,但它讓人們認識到了生態資本有著巨大的經濟價值;同時,Westman提出了“自然的服務”的概念及其價值評估問題,以及Daily 主編的《自然的服務——社會對自然生態系統的依賴》的出版,這些研究為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的研究打開了新的局面。
生態系統服務的概念、價值理論、評估方法等引入中國后,歐陽志云等[3]生態學家對中國陸地生態系統的6種服務功能進行了初步評估,謝高地等[4]對中國青藏高原生態系統服務價值深入研究,制定出了中國的陸地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當量因子表;李淵等[5]用替代成本法對建設用地的氣體調節、水源涵養和廢物處理進行估算,對蕪湖市的特點做出修正。
就武漢而言,目前武漢土地利用變化對生態服務系統價值的影響的研究較少,基本停留在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期作為中部重點城市,如吳后建等[6]研究中,分析了1996~2001年武漢市快速城市化區域土地利用以及土地覆蓋變化,計算出由此導致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變化。但是,21世紀后,武漢經濟發展迅速,尤其是2010年左右,湖北著力打造“大武漢”國際化建設,土地利用結構變化顯著,但對武漢市土地利用變化對生態系統價值影響的研究大多局限于某個區域或者領域,如對濕地、湖泊等研究,沒有從整體進行數據整理分析。
本文則以武漢市2001年和2015年整體土地利用狀況相關數據為立足點,著重研究該區域土地利用變化對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影響,論證該區域內各生態系統的重要性,并在此基礎上計算出調整生態價值系數后各生態系統敏感性指數,可以預測個生態系統未來的發展動向,力圖為該區域以土地利用結構優化調整為重點的生態文明建設提供科學的決策依據。
2 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2.1 數據來源
本文以武漢市2001年和2015年國土資源統計年報和《武漢市統計年鑒》中的數據為基礎。將武漢市的土地利用類型劃分為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和建設用地。
2.2 研究方法
2.2.1 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評估模型
根據Costanza 、謝高地等的研究理論,并結合研究區的生態環境特征,確定武漢市土地利用類型相對應的生態系統類型及生態價值系數(表1)。生態系統服務價值估算公式為:
(1)
公式(1)中,ESV為研究區生態系統服務總價值;VCi為第i類土地利用類型單位面積的生態功能總服務價值系數;Ai為研究區內第i類土地利用類型面積,n為土地利用類型數目。由于建設用地生態服務價值功能為0[4],本研究僅針對武漢市耕地、林地、草地、水域進行生態服務價值功能的估算。

表1 不同土地生態系統單位面積生態服務價值 元/hm2·年
數據來自:謝高地等[4]制定的中國陸地生態系統單位面積生態服務價值
2.2.2 敏感性指數
生態系統價值敏感性指數(以下簡稱CS),CS 是指VC 變動1%引起ESV 的變化情況。如果CS >1,表明ESV 對VC 是富有彈性的,CS 越大,表明VC 的準確性越關鍵;如果CS <1,則表明ESV 對VC 缺乏彈性。本文擬將各土地利用類型的生態價值系數分別上下調整50%來衡量ESV 的變化情況。
敏感性指數( CS )的計算公式為:
(2)
公式(2)中,ESVj為調整后的生態系統服務總價值;ESVi為調整前的生態系統服務總價值;VCjk為第k種用地類型調整后的價值系數;VCik為第k種用地類型調整前的價值系數。
3 結果與分析
3.1 土地利用變化情況
根據表2可知,武漢市2001年和2015年的耕地面積占土地總面積的比例均超過35%,是土地利用結構的主體,其次是建設用地和水域;土地利用主要表現在建設用地的急劇增長,而耕地和草地日趨減少。具體來說,建設用地由2001年的120800 hm2增加到2015年的185045 hm2,增加了53.2%;林地面積由2001年的68100 hm2增加到2015年的96009 hm2,增加了41.0%;水域面積由2001年的219657 hm2增加到2015年的247529 hm2,增加了12.7%;草地面積由2001年的6900減少到2015年的3395 hm2,減少了50.8%;耕地面積由2001年的395000 hm2減少到2015年的301170 hm2,減少了23.8%。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3個方面:第一,湖北省省委、政府高度重視“退耕還林”國策的推進,武漢作為省會城市,率先垂范,武漢市林業局多次下發《武漢市關于加強建立退耕還林管理長效機制的工作方案》,積極落實中央及省委的要求,極大地促進了耕地面積的減少、林地面積的增加;第二,武漢市作為中部重點城市,經濟發展一直名列前茅,更是提出建造“大武漢”國際化都市的目標,交通方面,武漢連續建造并開通了5條地鐵線,在建地鐵線達14線(段),高架建設也是如火如荼,如雄楚大道高架。在房地產開發上,武漢陸續建立了多個經濟開發區,如東西湖高新技術開發區,再者武漢時高校和人口的聚集地,為滿足其需求,大量的房屋的建設等必不可少,這些都直接導致了建設用地的急劇增加。第三,湖北自古有“千湖之省”之美譽,而武漢的湖泊水域居湖北之首,如南湖、東湖、湯遜湖等,武漢在早期的發展中由于過度追求經濟建設,大肆圍湖造地,造成了湖泊水域面積的大幅減少,但在現實的教訓面前,武漢市已開始著力保護湖泊等水域面積,拆除大量的圍湖占湖建筑,是武漢市水域面積得以增加的主要助推力。

表2 2001~2015年武漢市土地利用變化情況
3.2 土地利用變化對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影響
根據估算公式(1),可計算得出武漢市2001年和2015年生態系統服務總價值量(表3)。由表3可知,2001~2015年武漢市生態系統服務總價值穩中有升,2001年武漢市生態系統服務總價值為127.10億元,2015年為137.88億元,15年間增加了10.77億元,變化率為8.47%。可知,武漢市土地利用結構中耕地、林地和水域的的變化對武漢市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影響尤為顯著。具體而言,15年間,耕地面積減少93830 hm2,致使生態系統服務總價值損失5.73億元;草地面積減少3505 hm2,導致生態系統服務總價值損失0.22億元。但林地面積增加27909 hm2,促使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增加5.39億元;水域面積增加27872 hm2,促使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增加11.33億元。總體分析,武漢市2001~2015年生態系統服務總價值增加,是由于武漢市具有極高生態價值的退耕還林面積大幅增長,從而填補了其減少的生態價值較小的耕地和草地所引起的生態系統服務總價值的下降。因此,在今后土地利用中,武漢市應加強對耕地和林地生態系統的重視,維護退耕還林的成效,采取有助于林地和土地可持續利用的手段促進生態環境協調發展。

表3 2001~2015年武漢市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價值變化
3.3 敏感性分析
根據敏感性分析計算公式(2),將耕地、林地、草地、水域的生態價值系數均上下調整50%,對研究區2001 年和2015 年的生態系統總服務價值進行估算,具體結果見表4。
武漢市生態系統服務總價值對生態價值系數的敏感性指數均小于1,其中當水域的生態價值系數增加1%時,生態系統服務總價值將增加0.730%,這主要是由于水域的面積和單位面積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較大。當草地生態價值系數增加1%時,生態系統服務總價值只增加0.002%,對武漢市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影響甚微。表明生態系統服務總價值對于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系數缺乏彈性,也論證了本研究所采用的謝高地參考標準而估算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是合理的。
將武漢市2001年敏感性指數與2015年相比較發現,林地和水域的敏感性指數呈上升趨勢,其中林地敏感性指數由2001年的0.104上升到2015年的0.135,水域敏感性指數由2001年的0.703上升到2015年的0.730,表明林地和水域生態價值系數的改變對總價值產生放大作用。耕地的敏感性指數由2001年的0.190降低到2015年的0.134,草地的敏感性指數由2001年的0.003下降到2015年的0.002,二者對生態系統服務總價值的影響逐年減小。

表4 調整生態價值系數后生態系統服務總價值的變化情況及敏感性指數
4 結論
(1)武漢市在2001~2015年間,耕地面積急劇下降,草地面積有一定程度的減少,而建設用地面積顯著增大,水域面積和林地面積小幅度增加。這種土地利用結構的變化與武漢經濟的高速發展、城市化進程的加快等因素緊密相關。
(2)土地利用結構變化使武漢市的生態系統服務總價值在2001~2015 年間的變化率為8.47%,整體波動較小。但林地系統在武漢市總生態服務價值中日益發揮主導作用,表明若林地覆蓋面積下降會導致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顯著減小,因此在今后土地利用中應側重林地的規劃建設。
(3)本文對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結果進行了科學的敏感性評估,排開建設用地,其它各項用地敏感性指數均小于1,表明本文所采用的價值系數是較為合理的。
[1]Wackernagel M, Onisto L, Bello P, et al. National natural capital accounting with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concept[J]. Ecological Economic,1999,29(3):375~390.
[2] Costanza R,Arge R,G-root R,et al.The value of the world’s ecosystem services and natural capital[J].Nature 1997(386):253~260.
[3]歐陽志云,王效科,苗 鴻. 中國陸地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及其生態經濟價值的初步研究[J]. 生態學報,1999(5):19~25.
[4]謝高地,魯春霞,冷允法,等. 青藏高原生態資產的價值評估[J]. 自然資源學報,2003(2):189~196.
[5]李 淵,魯成樹,王 娟. 基于土地利用變化的生態服務價值研究[J]. 中國農學通報,2007(6):576~580.
[6]吳后建,王學雷,寧龍梅,等. 土地利用變化對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影響——以武漢市為例[J]. 長江流域資源與環境,2006(2):185~190.
[7]王秀麗,吳克寧,呂巧靈,等. 鄭州市郊區生態服務功能價值變化研究[J]. 中國農學通報,2007(3):398~401.
[8]王佼佼,胡業翠,呂小龍,等. 基于土地利用變化的北京市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研究[J]. 中國農學通報, 2012(32):235~242.
[9]李 正,王 軍,白中科,等. 貴州省土地利用及其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與灰色預測[J]. 地理科學進展, 2012(5):43~49.
[10]王宗明,張 柏,張樹清.吉林省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變化研究[J],自然資源學報,2004,19(1):55~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