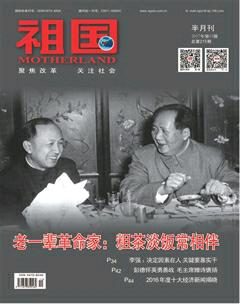論張潔小說的后現代主義傾向
后現代主義思潮的源起、發展、嬗變、撒播,是一個極其復雜以至于言人人殊的問題。大致上說,后現代主義思潮是對現代性問題的一種全盤反省和基本價值的消解。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期,后現代話語開始全球性的傳播并逐漸波及第三世界國家。張立群在《中國后現代文學現象研究》中曾把中國80年代中期以后至90年代初期的帶有后現代傾向的創作稱之為“類后現代”,原因之一是“80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國后現代文學創作更多的是以借鑒、超越的姿態完成自身的實踐的,這種在當時并不完全知道何謂‘后現代就展開的創作實踐,更多出自于文學創新和理論創新的需要。”然而女性主義研究者荒林曾在張潔的訪談錄《存在與性別·寫作與超越》中明確提出張潔的一些短篇小說具有后現代主義所追求的“魔幻文體”,張潔本人也承認“我最近看了一些后現代主義小說,我覺得我那個時候寫的就是,可是沒人理解。”“后現代文學是對傳統文學的一種延伸,我在20年前已經這樣做了。”當然,張潔小說的后現代特征并不與西方意義上的后現代完全相同,張立群學者把含有許多“非后現代因子”并體現中國后現代文學初始狀態的寫作表征,將其稱之為“類后現代性”。而張潔創作于80年代的小說在藝術特征上的荒誕意識、變形與虛構、破碎與拼貼、戲仿與反諷則具有張立群學者所謂的“類后現代性”。
一、荒誕意識
荒誕在字典中的解釋為“極言虛妄,不足為信”,但在后現代主義的層面上荒誕則表現著一種普遍的生活境遇,也表現著對理性的批判和對傳統認識論框架的一種否定,其本質體現著后現代思想拒絕總體主義、拒絕邏各斯中心主義、拒絕形而上學的立場和傾向。《謀殺》這篇小說我們可以簡單的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父母各自用自己的中西醫藥理論來醫治自己不斷萎縮的胃;第二部分則是父母在家無休止的爭吵;第三部分是父親去郵政局給自己多年之前的情人寄信,卻與工作人員發生爭執,過多的郵寄規則讓父親放棄了寄信。小說的內容雖然很荒誕,但它描述了一個普遍生活狀態世界的存在。仔細推敲,“謀殺”應該有兩層含義:一是父母都在用各自的理論知識來強加在兒子身上,扼殺了本該屬于孩子的人生,“把雙親那份愛子的天性或需要,全折在了他一個人的頭上。”二是社會過多的規則消磨了人的意志,“無論多么朝氣蓬勃、伶俐機智的人,一進這個大門,立刻變得呆傻,就像進入那些灰色的水泥建筑物里一樣。”后現代思想給我們的一個最大的啟示就是讓我們重新去省視人與人、人與現實、人與世界之間的關系。
二、變形與虛構
魔幻作為現實生活中無法解釋,從科學角度看根本不存在的現象,大部分是通過變形、虛構等方法得以實現的。張潔的小說《魚餌》中則運用了變形與虛構的方法,“常言道,誰干缺德事,誰養的孩子沒屁眼兒。BA的兒子倒是有屁眼兒,可上午他的兒媳卻生了一個沒屁眼兒的孫子。這也許叫隔代效應。”這段與馬爾克斯《百年孤獨》中說生了一個豬尾巴的孫子的效果是一樣的。文章多次寫到許多看似是魚但是又不能稱作為魚的東西開口說話,死湖不禁竊笑等等。這些都為本來荒誕的情節增加了神秘感。
三、破碎與拼貼
從理論上說,“破碎”與“拼貼”就是哈桑在歸納后現代主義特征時指出的“零亂化”、“種類混雜”。其效果就是詹明信所說的從“蒙太奇”到“東拼西湊的大雜燴”的過渡。《他有什么病?》則是個名副其實的“大雜燴”。第一部分醫生胡立川的飛機不能按時起飛,他在去問工作人員原因回來的路上,把錢包扔進了痰盂,把煙頭裝進了褲兜。第二部分丁小麗在醫院里檢查她的處女膜;丁大爺在無奈之下燒光了自己的棉花只因不愿意給過稱的工作人員送禮。第三部分玉峰忍受不了同住一屋的小木匠,分房不成功,就萌生了火燒宿舍的想法。第四部分胡立川在醫院救活了經常在醫院門前補鞋的黃老頭的孫子;一個看太平間的老頭與瘋女人繁衍后代的故事。第五部分則是每個開頭都運用了18個“某年某月某日”,來把胡立川在醫院里發生的不同事情連接在一起。第六部分,先是有了5大段的關于社會弊病的議論與憤慨,然后又直插入了醫院陳主任的女兒陳幺妹的班主任李老師的家訪。第七部分重新回歸侯玉峰與小木匠,結果被小木匠揍了一頓。整部作品給人的感覺就是“東一榔頭西一棒子”,無連續性、非確定性,正體現了后現代主義碎片化、拼貼式的風格手法。
四、戲仿與反諷
戲仿,希臘文原意是“模仿的歌者”。后世學者把古代的戲仿定義為:“追隨一種獨創性的風格歌唱,但又帶著某種差別。”[4]這種寫作手法后來被移用到文學上。琳達 哈琴把后現代主義文本中的戲仿定義為“帶著一種批判的反諷距離的模仿”。[5]張潔的作品《橫過馬路》的副標題就明顯標明“仿某某朝文體”。文本中的主人公是一個愛幻想的精神病者,想象著自己是一個國王,身邊美姬環繞,卻被老婆一棒子打醒;原本喜歡寫作,稿子卻被老婆當做了衛生巾來用;閑著沒事,打匿名電話,竟惹得做了壞事的人不安。來到大街上,傾訴自己喜愛做公交車的怪癖,為了“為什么紅燈停、綠燈行”的問題絞盡腦汁。在一番無果后,紅綠燈都亮了,他徑直走了過去,沒想到自己的絕活卻丟在了馬路上。這篇小說從他惡作劇的那個層面來說,是對黨政工作人員的諷刺,而那有關過馬路則是對傳統思維方式的質疑。開放式的格式、多元化的思維,宣告了“某某朝文體”在當代社會的徹底結束。
張立群曾指出,中國后現代文學整體流脈是從先鋒小說開始的,但在先鋒小說之前,張潔的創作已經具有了后現代主義的傾向,并且在不知何謂“后現代”的前提下就展開了文學創作,我們不得不說,張潔有著常人不可超越的文學感悟與天賦,她的創作是一種文學形式的創新,是在中國當代的大環境下的一次超越的嘗試。用超前的藝術特征來表達自己對于社會的關注與不滿,用文字表達自己建構自己的文學世界。
參考文獻:
[1]張立群.中國后現代文學現象研究[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社,2012.
[2]荒林,張潔.存在與性別·寫作與超越——張潔訪談錄[J].文藝爭鳴·評論,2005,(05).
[3]張潔.魚餌[M].北京:人民文學文出版社,2012.
[4]M.A.羅斯.戲仿:古代、現代和后現代[M].倫敦:劍橋大學出版社,1993.
[5]羅鋼.后現代主義文學作品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6]張潔.中短篇小說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
(作者簡介:許小燕,遼寧大學,專業: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