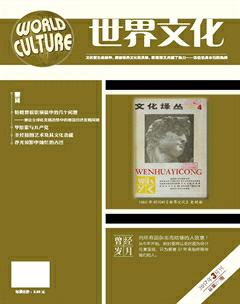浮光掠影中燦爛的古巴(一)
趙玫
美麗的哈瓦那
凌晨,從巴西利亞起飛,途經巴拿馬城。在浩瀚的晴空下,前往夢寐以求的古巴。飛行中,《美麗的哈瓦那》的旋律始終回環在腦海中。舷窗外,蔚藍色的大洋,好像昭示著某種神秘的密碼。飛機在降落時輕輕晃動,一團團清澈的濃霧,風一般地襲來。緊接著,你便看到了云團下青綠的莊稼,壯麗的海灣,眼前,就是我們兒時夢寐以求的美麗國家么?
是的,這就是古巴,這就是哈瓦那;這就是我們曾經歌唱過的那片豐饒的土地。記得那時,我們對這個夢一般的國家懷了很深的感情,但又對這個遙遠的國度其實并不真的了解。
記憶中,記住的,只有紅白藍三色相間的國旗,卻從不曾看到那戰旗是怎樣在大西洋海岸獵獵飄揚的。當然我們也記住了那位勇敢而英俊的卡斯特羅。盡管那時我們只能在報紙和畫報上領略他的風采,但我們還是深深愛上了這位古巴英雄。
于是,我們很快就學會了那首《美麗的哈瓦那》。幾十年過去,竟然依舊不曾忘卻優美的歌詞和旋律。那歌聲,伴隨著我們的向往,承載著我們的夢。但這夢,又是那么虛無縹緲。直到,幾十年后夢想成真。
回望1962年
小時候,我是在天津人民藝術劇院的舞臺前,慢慢長大的。因父母從事話劇事業,我得天獨厚地、幾乎看遍了劇院上演的所有劇目。無論是歷史劇,現代劇,還是外國戲劇,我都會乖乖地坐在排演場下,悄然無聲地看著叔叔阿姨們在舞臺上表演。
記得那年,我剛剛上小學。放學后,我總是首先來到排演場。在那里,我能一邊看排演,一邊做作業。那時我始終迷戀于表演,想象著某一天,自己也能站在戲劇的舞臺上。
不記得,那時的劇院在排演什么劇目,卻記得正在排演的那出戲,突然被叫停。后來知道,劇院將舉全力,將一位古巴劇作家的作品《甘蔗田》搬上中國的戲劇舞臺。那時我盡管懵懂,卻還是感受到了劇場的氣氛,在莫名的緊張中,感受著某種炮火硝煙的氣息。
是的,《甘蔗田》,為什么是《甘蔗田》?

還記得,當年的那位古巴劇作家,是的,阿爾豐索。他每天都會坐在排演場前,與翻譯、導演、演員不停地交流著。他看上去很糾結也很憤然的樣子,和他一道前來的是他美麗的妻子。他的妻子,是古巴最著名的女演員瑪利亞·歐菲莉亞·狄亞斯。她所以和劇作家一道從北京趕來,是因為瑪利亞曾經在古巴的舞臺表演過《甘蔗田》。于是她來到天津,對中國演員的表演給予指導。而這部不朽的杰作《甘蔗田》,據說也是他們愛情的見證。
緊接著,天津人藝開始緊鑼密鼓地排演《甘蔗田》。布景背后,已然是一片旖旎的加勒比海的風光。壯麗的大西洋,妖嬈的甘蔗田,舞臺上的風情,戲劇中的故事,很快就吸引了我們這些坐在舞臺下的孩子們。還記得,排演中,很多群眾演員的臉上和身上都涂抹上黑色的油彩,扮演當地的土著。演員們學著古巴那種有節奏的舞蹈。他們不停地敲擊著鼓點,跳著非洲黑人的舞步。而我們這些孩子,也伴隨非洲的鼓點旋轉了起來,不約而同地融入了叔叔、阿姨那靈動的舞姿中。
后來聽說,上海戲劇學院的師生,在學習了黨的八屆十中全會的公報后,便立刻掀起了反對美帝國主義侵略的熱潮,且當下就終止了獨幕劇的表演計劃,趕排《甘蔗田》,以無比高漲的政治熱情,支援古巴人民的革命行動。
緊接著,聲援古巴打倒美帝國主義的浪潮,在華夏大地風起云涌。而蕭三,則以他的文字,回顧了他和古巴詩人的交往。他深切地同情古巴人民在革命前的厄運,他激情飛躍地宣稱,他的心,已經飛向了那遙遠的加勒比海岸了。
是的,古巴,這個加勒比海上的一個輕柔蕩漾的島國,她被人稱之為“加勒比海的珍珠”,抑或“安第列斯群島的珍寶”。1492年,偉大的哥倫布航海至此,緊接著,這里就淪為了西班牙的殖民地。在這片豐饒的土地上,年輕的古巴共和國的歷史并不長,卻在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斗爭中,取得了獨特的勝利。于是哈瓦那,卡斯特羅,都成了我們的向往。
從機場出來,濕熱的氣候,看街上喧喧攘攘的人群,竟驀地有了種亦真亦幻的感覺,仿佛真的又回到了《甘蔗田》。
那一刻,不知是遙遠的童話,還是恒久的夢……
年深日久的呼喚
濕熱的大街上,蒸騰著夏日的炎熱。哈瓦那街頭的人們卻顯得很歡快。據說這里的幸福指數始終居高不下,因為對古巴人來說,金錢,確乎不是他們生存中的唯一。
大街上,一座座古老的房舍,昭示著城市的滄桑。驀地置身于美麗的哈瓦那,竟仿佛回到了我自己的城市。之所以會有這種回家的感覺,是因為哈瓦那街道兩旁的老房子,竟和我生活的環境大同小異。
于是慢慢思忖,恍然意識到,我所以如此熟悉哈瓦那,是因為我的城市和哈瓦那一樣,都曾淪為他國的殖民地。只不過西班牙人更早地就占領了當地土著人的家園,而我的家鄉,則是在1860年至1900年的40年間,才先后設置了九國租界。于是,我生活的城市變得很豐富、也很斑駁,歲月間,至今雜糅著多國文化的積淀。這再一次旁證,一個殖民的城市,自然會有殖民地的風情。
是的,眼前的這些幾百年前的老房子,始終佇立在大西洋沿岸。于是你便會想到當年的那些淘金者,是怎樣依照故鄉的模式,營建起他們不朽的家園。完全可以想象出,他們遠涉重洋,顛沛流離,既懷著悲涼的鄉愁,亦充滿征服者的傲慢。眼看著那些殖民地時期的老房子,怎樣慢慢地衰朽破敗,在熾熱的風中,追尋那曾經的絢爛。

沿著哈瓦那大街向前,你仿佛能聽到路兩旁的悲歌。那滿眼皆是的衰敗建筑中,盡是斑斑駁駁的斷墻。無論是地中海的風情,還是哥特式的陰森,都曾是隨風而逝的傷痛。總之這類古老的建筑,在哈瓦那幾乎觸目皆是。于是你無論走到哪兒,都能看到那寂寥的衰敗,哪怕透過車窗,也依舊能望到那些憂戚的房舍,挽歌一般地,在做著歲月的憑吊。
明媚街道的不遠處,我竟然看到了,正在如火如荼進行翻修的一些老房子,這讓我心頭一亮。工人們穿著工裝,在炎熱的驕陽下,一絲不茍地完成著他們的使命。慢慢地,那一座座輝煌的院落,似乎已開始修葺一新。讓曾經壯麗的那些房舍,再現昔日輝煌。
是的,這就是為什么,我總是會那么在意那些古往今來的老房子,因為我一直覺得,那年深日久的呼喚,不單單是在還原它曾經的繁盛,也在支撐著她的當下與未來。
幽深的小巷,仿佛昨日……
小街里的妖嬈,讓我驀地想到了戴望舒。是因為在悠長的小巷中,走來熱烈而又奔放的古巴姑娘。她們銅色的肌膚,妖嬈的身姿,歡快地行走在繁華的老街上。在這里,沒有蒙蒙細雨中的惆悵,只有燦爛驕陽……
是的,那迷人的午后。

這一刻,我們終于走進了老街。只是匆忙間,難以追尋老街迷人的歷史。只覺得,在老街中慢慢行走的那種感覺,是安逸而又恬淡的。行進中,就仿佛你真的回到了哥倫布的時代,迷人的小巷,停泊的漁船……
如今老街兩旁,到處是年久失修的房子,已不見當年風采。斑駁的石階,盡管已凋零惆悵,卻依舊濃郁著古巴人的風情萬種,那唯有古巴人才能感知的,那濃濃的詩意。
16世紀,無疑是西班牙人最為鼎盛的時期。他們很快就占領了原本屬于土著人的浩瀚疆域。從此他們在土著人的土地上進行開發,從草原,到海港,伴隨著哥倫布到此,這里就更是成了西班牙人的領地。他們瘋狂地掠奪原住民,將別人的土地變成自己的樂園。
早在1519年,哈瓦那就被確立為永久性的城址,從此土著人永失家園。
殖民者的到來,無疑改變了當地人生存的方式。那些驕傲的西班牙人,自踏上新大陸,就開始在老街中建造他們的家園。那些宏偉的建筑,壯麗的房舍,無疑拷貝了歐洲不同時期的藍本。于是,我們才得以在老街中看到那些古老房舍,如議事廳、教堂,城堡。如今這些匯集在老街上的建筑,大多雖已衰微破敗,卻始終傲然挺立,陪伴著老街昔日的不朽。
走在熙熙攘攘的街上,放眼看去,不同膚色的人種,構圖成奇異的景觀。在古巴,白人占大半,小半人為黑人或混血。混血,讓原本不同膚色的人種,伴隨著歲月滄桑,慢慢地親和了起來。膚色,在這個國度,在某種意義上,已幾乎不再帶世俗偏見的符號。(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