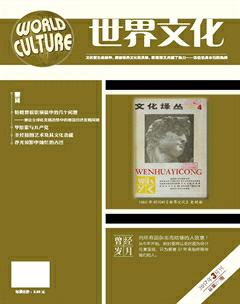圣經插圖藝術及其文化功能
任東升+馬月蘭

文字與圖像相生相成,歷史悠久。《周易·系辭上》有言“河出圖,洛出書”,足見“文不足以圖補之,圖不足以文敘之”的搭配與和諧。經書在信仰者心目中是超自然存在的精神容器,文字和書籍自然非常神圣。為表達崇拜和敬仰之情,經書插圖者不惜工本,甚至不惜金、銀,著力裝飾插圖,例如在中國最早出現的是佛經里的“變相”插圖,圣經古亞述文手抄本中黃金葉制作的耶穌及其他圣經人物圖像,《古蘭經》搭配細密畫配的經字畫。人類對神圣文本的膜拜是圖畫與書籍相結合的根源,而插圖精致、圖文并茂、裝幀考究的經書,一直是人類書籍中的珍品。不同時代、不同作者的圣經插圖,種類豐富、風格多樣,堪稱文字與圖像相結合的藝術長廊。
抄本插畫:基于原始藝術的“新型”藝術
現存最古老的圣經可以追溯到《新約》諸篇成書后的公元101年至200年之間。基督教得到羅馬帝國承認后擴展迅速。在地處偏遠、未被戰火波及的愛爾蘭基督教傳播尤為成功。追求清心寡欲的愛爾蘭修士到西歐各地建立起修道院,并大量抄寫經書以供傳教所用。為彰顯神圣,美化經書,畫在羊皮紙手寫書稿上的手抄本插畫應運而生。因當時人們識字水平低下,手插畫便順應時代需求,成為輔助人們理解、激發閱讀興趣的新型藝術,廣受歡迎。

手抄本插畫是“蠻族”原始文化藝術與當地傳統文化藝術融合后而形成的新型藝術。“蠻族”原始藝術中有描繪野獸的習慣,如在各種裝飾中所用的獸形圖案或由獸形變形而組成的花紋,被裝飾在基督教的十字架上或手抄本的插圖裝飾中,制作于7世紀晚期的《林迪斯芳福音書》(Lindisfarne Gospels,現藏于大英圖書館)是杰出的代表。該拉丁文手抄本由諾森伯里亞島上的林迪斯芳修道院主教埃德弗里斯設計并制作,共有259頁羊皮紙,匯集了四福音書,每一篇福音前都有三幅插圖:福音作者圖像、地毯頁(carpet page)和首字母頁。其中,地毯頁的裝飾設計極具動感,交纏的造型、伸縮收展的意境彰顯著動能與變化,彎彎曲曲的植物花紋圖案貫穿成十字架的造型,色彩豐富和諧,彰顯著整體美。首字母頁的圖案復雜有序,極具裝飾性,精致程度令人嘆為觀止。這些插畫為愛爾蘭-撒克遜風格,體現出愛爾蘭、古典主義和拜占庭三種元素的融合。如今,《林迪斯芳福音書》成為英國保存最好的千年古書(該書的手寫副本于1104年圣庫斯伯特墓開啟時被發現)。
12世紀下半葉至13世紀中葉,抄本繪畫在英、法兩國廣為流傳。著名抄本繪畫遺例見于英國的《溫徹斯特圣經》(1170—1175)、《溫徹斯特大修道院詩篇》(12世紀末)等。《溫徹斯特圣經》(The Winchester Bible)羅馬式泥金裝飾,58.3cm x 39.6cm開本,抄錄了整部《武加大譯本》,包括《新約》《舊約》兩個版本的詩篇以及經外書,書中的裝飾圖案,因真金和來自阿富汗的天青石而閃耀奪目,魅力大增。這版圣經并非溫徹斯特本地的風格,而是來自整個歐洲大陸的風格。其風格莊重,恰好與教堂神圣風格相匹配,所用羊皮紙質地精致,排版設計講究,這些可以通過抄寫員仔細刻下的用作書寫的線略見一斑。《溫徹斯特圣經》是12世紀諾曼底政權的宗教象征,是英國最優秀的藝術作品之一,同時是世界上裝飾最美的圣經版本。
細密畫:趨于象征意味的“方寸”藝術
細密畫(miniature)是中世紀的主要藝術之一,一般認為起源于歐洲的手抄本和小型木板蛋膠畫,是一種精細刻畫的小型繪畫,畫于羊皮紙、紙或書籍封面的象牙板或木板上。在帖木兒帝國(約1370—1507)時期達到鼎盛,18世紀后因歐洲殖民者入侵而幾乎消亡。
繪制細密畫使用的工具比較簡單,由于其多為典籍或者圣經的抄本插圖繪畫,尺寸一般非常小,由此得名“方寸”藝術。由于工業技術上的限制,細密畫顏料講究,多采用礦物質,甚至以珍珠、藍寶石磨粉作顏料。顏色并不復雜,但是被處理得和諧自然,質樸典雅,品位油然而生。形式上也不注重體積空間,大多是平涂技法。從整體風格來看,細密畫融合了波斯工藝、日耳曼傳統乃至中國宋元的工筆畫風,極具藝術史學價值。
基督教通過羅馬傳教團的本篤會僧侶再度傳入英國,傳教士們為了傳教布道把大量的書籍帶到了英格蘭,這些書籍的到來也對英國本土的書籍插圖繪畫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在風格樣式上英國的圣經細密畫繼承了凱爾特-日耳曼的傳統,主要用線條,其主要特征是多運用各種動物和植物相關的隱喻性圖案,比如,以鴿子寓意圣靈,以老鷹象征約翰。畫面大面積運用金色、藍色、紅色搭配,有些地方輔以暗褐色的細線勾勒,使得整個畫面既和諧文雅,又質樸莊重。
1147年威德里卡斯修道院院長制作的《威德里卡斯福音書》(The Gospel Book of Abbot Wedricus)手抄圣經中有一幅插圖《傳福音者約翰》(St.John the Evangelist),畫面內容豐富,人物形象清晰,故事情節完整,著色細致和諧,可謂細密畫的巔峰之作。8個圓盤單元由渦卷的莨菪(天仙子)葉飾串聯,構成一個整體的邊框;四角的四個圓盤描繪了圣約翰生平的故事,中部左側圓盤里的鷹是約翰的象征;畫面中間是坐在高大的寶座上的約翰,上方圓盤中上帝手中象征圣靈的鴿子為他帶來寫作的靈感,中間右側圓盤則是修道院院長在為他提供墨水。這樣的兩個圓盤使邊框與框內人物融為一體。寶座的座邊是連續的圓形紋樣;座下是兩層不同形式的連環拱廊;座上還有厚厚的軟墊。靠背的頂部呈半圓形,飾以纏繞的植物圖案。從插圖中人物衣服的褶皺和家具造型可以看出,這幅畫明顯受到拜占庭藝術的影響。

尼德蘭林堡兄弟(Limbourg brothers)以制作細密畫著稱,其細密畫《逐出樂園》(藏于尚蒂伊孔德博物館,尺幅29cm×20.5cm )以其精密的建筑設計,生動的人物體態,成為再現伊甸園神話的藝術佳作。畫面表現的是天、水之間圍墻狀的伊甸園。哥特式建筑是設計的一大亮點,包括中間的生命之泉和右邊的門樓。畫面從左到右以連環形式描繪了原罪的故事情節:夏娃受蛇誘惑偷食智慧果,之后將其遞給亞當;上帝因此震怒,屈指管教、降罪;最后亞當、夏娃被逐出伊甸園。留意把守伊甸園出口的天使,其六翼在門內,臉部在門外。畫家把伊甸園繪制成懸于空中的絕倫掛盤。仔細觀察,我們發現圓形的封閉空間內,兩座哥特式建筑彼此呼應,高聳入云,畫家有意將人置于可見的醒目位置,這種安排似乎既不合比例,也不合乎構圖的自然結構,這正說明畫家重在突出人,突出人體,突出人的故事。整個畫面人物比例勻稱、體態優美、神情生動。因此,此畫堪稱15世紀初人體繪畫的杰作。
多雷的銅版畫:凸顯立體感的“視覺”藝術
歐洲版畫歷史悠久、創作題材豐富、種類繁多,是具有強烈視覺效果和獨特審美價值的一種藝術表現形式。1534年,德國宗教改革家、圣經翻譯家馬丁·路德翻譯的德文圣經印刷出版,里面插有150幅精美的彩色木刻圖。2003年,為了紀念“圣經年”(Year of the Bible)德國的TASCHEN出版公司重印了馬丁· 路德1534年版的圣經,分《舊約》和《新約》兩本。還原了馬丁·路德的好友、著名畫家、雕刻家盧卡斯(Lucas Cranach, 1472—1553)的彩色木版畫插圖。
古斯塔夫·多雷(Gustave Doré, 1832—1883),法國版畫家、雕刻家,他的作品涵蓋《圣經》、但丁《神曲》、彌爾頓《失樂園》等,所繪插圖人物幾乎成為文學作品角色的形象模板。1866年,多雷因為英文版圣經繪刻插圖而名聲大噪。實際上,多雷創作的240幅銅版插畫最初印制于1865年的法語圣經,隨后重印于各種德文版、英文版及其他版本的圣經。有的出版商甚至將多雷的圣經插畫單獨出版,取名《多雷圣經畫冊》(Dorés Bible Gallery)。多雷的圣經插圖風格對20世紀的圣經電影的場景制作產生了很大影響,如美國導演格戴米爾(Cecil B. DeMille)執導的《十誡》,不少場面與多雷的插圖十分相似。多雷的作品多是黑白兩色,以銅版畫為主。整體而言,其作品充實飽滿、層次分明、質感強烈,表現了理性與情感相互交融的繪畫理念。具體來講,有以下特點:首先,素描特征突出。在陰影之處發掘素描語言所展現的藝術趣味,擺脫畫面的單調乏味,在簡潔的素描關系中呈現出的是豐富多變的色調與旋律,加強了作品的閱讀性和完整性。其次,善于把握畫面中整體與局部的關系,點的組合與排列也相當有序,富有規律又不呆板,顯得有條不紊。第三,對線條的運用特色獨具,對線的使用不再簡單劃一,而有了更豐富的內在變化,和所繪內容相得益彰。第四,光感色彩到位,人物造型嚴謹,比例結構準確,且人物與背景自然融洽,立體感很強。正是這自然的色調使得畫面富有美感,蘊含著復雜多變的視覺效果,將圖像融入文字,使讀者文字與圖像的把玩中,獲得全新審美體驗。
安妮的簡筆畫:凝練簡約的“寫實”藝術
為了讓圣經貼近大眾,圣經翻譯的功能從聽寫式記錄上帝之言,轉變為以讀者接受為旨歸的動態對等圣經翻譯,即從形式對應的直譯哲學轉向功能對等的動態哲學,這使得新譯本的語言表達趨于簡單。與這種趨向“簡單”的圣經翻譯認識相配合,瑞士藝術家安妮(Annie Vallotton)為20世紀70年代制作的英文版《福音圣經》制作了500余幅簡筆畫。安妮堅持“用簡約的筆觸表達最豐富的內容,如表現約伯無辜受難時對上帝公義產生動搖與質問的畫面,以簡潔的筆觸,寫實的意境,表現約伯的痛苦與堅強、無奈與不屈:雙膝跪地,但頸項挺直,表明絕不屈服于命運的安排;左臂撐地,承受重壓,卻透露出受挫中的堅強;右手抬起,向下捶地,宣泄內心的痛苦和憤懣;眉目緊縮,百般憂傷,但卻凝神思考。約伯面對天降之禍的百般思考,全部濃縮于這方寸之間。

安妮的插畫常常簡潔到令人拍案叫絕,《耶穌受難》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上方用兩個直角勾勒出沉重的十字架;中間用兩條曲線勾勒出耶穌倒懸的雙臂,下方用一個圓形勾勒出耶穌頭上的荊棘冠。觀眾雖然看不到耶穌的雙手,也看不到耶穌的臉,但是完全能夠通過十字架、雙臂和荊棘冠“補上”畫家未畫出的“細節”:被釘在十字架上流血的雙手、痛苦卻堅毅的臉龐,甚至可以把遭受殘酷折磨后耶穌的所有身體細節和面部細節完全填補入畫。這就是簡約的力量!
另一幅必須提及的插畫是《呵靜海浪》。《呵靜海浪》展示了兩個場面:風高浪急、小船幾近傾覆(前景),耶穌呵斥海浪,一切頓然轉為平靜(后景)。畫家用重疊的波浪形曲線來描繪激怒的海浪,具有動態效果;船中耶穌及其十二門徒的身影也進行了適度再現,但只是點到為止。在后景中,平靜的海面映照著岸邊的遠山和小船的桅帆和船里的人;船中的人影分為兩組:穩穩站立的耶穌張開雙臂在講天國的信息,而十二門徒安靜地坐著,洗耳恭聽。這幅插圖兼容了粗獷和細膩兩種風格,既有“大風大浪”的場面感,又有“海上泛舟”的剪影感,令人嘆為觀止!“場面感”最強烈的要算這幅數千人集聚岸邊聆聽安坐于小船上的耶穌講道的《海濱布道》插圖。聽眾由遠及近;或站立,或端坐,或下跪,或俯臥,或仰臥,形態各異。船中的耶穌伸出右手,指向岸邊的人群。小船與海岸間,漣漪層層疊疊,將船上布道的耶穌與岸上的聽眾連接起來,“人山人海”的宏大場面躍然紙上。

馬佐里插畫:“違背”常規的表現主義藝術
擅長表現主義畫風的意大利畫家馬佐里(Dino Mazzoli, 1935— ),從2004年到2014年,馬佐里手抄了1500多頁基督教圣經,創作插圖多達5000余幅,形式包括水彩畫、拼貼畫、蠟筆畫。2015年5月《馬佐里手抄手繪圣經》(The Holy Bible - Handwritten and Illustrated by Dino Mazzoli)發行了電子版。馬佐里的圣經插圖帶有畢加索的印象主義和野獸派創始人馬蒂斯的影子:狂野的色彩和強烈的視覺沖擊,常給人不合常理的感覺。
馬佐里為圣經每卷書做了介紹,并配有表達主題的插畫。《士師記》插畫,馬佐里用粗獷和夸張的筆調來表現健碩、勇猛、敢于擔當的士師,粗大的利劍和厚實的盾牌頗有“磨刀霍霍向敵人”的氣概。
“論古列說:‘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悅的。”出自《以賽亞書》第44章第28節。馬佐里的據此而做的插圖筆觸猛烈粗重,人臉不全是人臉背景也不單純是背景,顏料似乎是隨便抹上去的。這明顯與抽象表現主義靈魂人物威廉·庫寧(Willem de Kooning 1904—1997)的風格相似,只不過,馬佐里還比不上庫寧那么“混亂”。

“我與父原為一”出自《約翰福音》第10章30節,意思是作為“神之子”的耶穌與“圣父”上帝因目標相同而合為一體了。馬佐里以此為靈感創作了這幅上帝和耶穌“合二為一”的畫。這怪異奇妙的兩張臉很明顯是在模仿畢加索。
為圣經文本貢獻出藝術才華的插圖作者,以自己對圣經文本的解讀和獨到的藝術理念,為后世留下了珍貴的作品。這些插圖在“美化”圣經的過程中,客觀上激發了藝術家的創造力,豐富了圣經的文化內涵,催生了自成一體的插圖藝術。圣經簡約的文字,配上潤飾精致的插圖,可謂對圣經的擴寫,彰顯了圣經的動態經典價值。與圣經簡約風格相契合的簡筆畫插圖,可謂與圣經簡約風格相媲美,彰顯著圣經簡約體的魅力與力量。這些插圖藝術無疑是圣經制作工藝和書籍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因其異彩紛呈的創作風格和自成一體的藝術品質流傳于世,成為獨一無二的藝術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