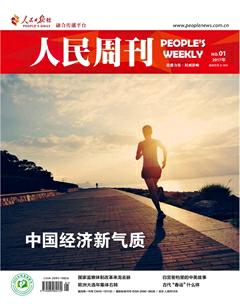剔除體制成本應作為改革戰略重點
宋則
剔除隱形體制性成本是一項難度大、影響廣、極具挑戰的艱巨任務,不能僅僅當作為企業解困的權宜之計,而應在全面深化改革總進程中始終作為戰略重點。
2016年8月8日,國務院印發《關于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工作方案的通知》,是黨中央、國務院為有效緩解實體經濟企業困難、助推企業轉型升級做出的重要決策部署,也是對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密集出臺深化改革、降本增效系列舉措的再梳理和再提升。工作方案制定的路線圖、時間表和責任分工定將有助于鞏固前期成果,并取得更大的實質性進展。
消除體制成本提高經濟效益
從體制和政策視角看,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可以劃分為競爭性成本與體制性成本。前者屬于企業正常經營活動中注定要發生、需要補償的合理成本;后者則是由于管理體制陳舊、政府行為失當、政策設計缺陷引發的不合理成本。競爭性成本是在技術管理創新的競爭中不斷降低的問題,體制性成本則是必須深挖細找、堅決剔除的問題。工作方案從全面深化改革的高度立意,所列舉降成本的六大重點40多項措施,即稅費負擔、融資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人工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等,大都集中指向體制性成本。這類成本背后都有著源遠流長、盤根錯節的深層原因,并導致國民經濟總成本增加,總效率和總福利損失。
我國經濟運行成本高、效能低、浪費大,固然有企業自身的原因,但主要來自弊端叢生、利益固化的經濟體制和政府機構內部。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代表中央所做的《關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決定的說明》指出:“沖破思想觀念的障礙、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解放思想是首要的。在深化改革問題上,一些思想觀念障礙往往不是來自體制外而是來自體制內。思想不解放,我們就很難看清各種利益固化的癥結所在,很難找準突破的方向和著力點,很難拿出創造性的改革舉措。”這一基本判斷在降成本的體制性阻力問題上表現尤為突出。體制性成本不可等同于、混淆于一般所說的競爭性的企業經營成本。因為“體制性成本”破壞公平競爭和企業預期,帶有純粹人為性質和既得利益背景,在極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設計中,往往憑借手中權力,巧立名目,為企業硬性植入大量原本可以避免、剔除的行政性額外負擔,充斥著“體制機制弊端”和“利益固化的藩籬”,因而是“最冤枉的成本”。在現行統計核算框架下,體制性成本帶有極大的隱蔽性和主觀隨意性。因為衍生出來的成千上萬、名目繁多、貌似合理的審批、規定、條款,大都諱莫如深、層層包裹、極不透明,也極易做手腳,不僅在技術上難以識別認定,還常被主觀故意加以掩蓋。
在我國,說不清道不明、難以識別的隱形成本一直長期大量存在,人們早已習以為常,見怪不怪。對此,只有從改革視角,對比改革之前和改革之后的成本效能變化,那些很詭異、難識別的成本真相,才會大白于天下。大量典型案例和事實證明了隱形體制性成本的嚴重存在,而剔除這些成本,立即帶來了巨額的改革紅利和經濟效率。據中國政府網的不完全統計,自2013年3月組成本屆政府以來,國務院相繼取消和下放了800多項行政審批事項,并公布取消了211項職業資格,減輕企業稅費負擔670多億元;中央層面累計取消、停征、減免了420項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每年減輕企業和個人負擔約920億元;將失業保險費率由現行條例規定的3%統一降至2%,每年就減輕企業和員工負擔400多億元,對社保“五險”中企業應繳納的工傷保險平均費率、生育保險費率做出下調,每年能給企業減負約270億元;新的一輪“定向減稅”,為小微企業減輕稅負40多億元,通過減稅降費對小微企業的支持達到1000多億元;從2012年啟動試點,4年來,營改增已累計減稅6400多億元,惠及592萬戶試點納稅人。改革全面推開后,2016年減稅將超過5000億元,總體上,營改增涉及1100多萬戶試點企業,涉及稅收總規模超過19000億元。
上述情況顯示,中共十八大特別是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后,在大刀闊斧改革行政體制、大力度“清障、降本、增效”的過程中,各級政府機構中陳舊不合理的審批制度和行政收費亂象,才終于得到遏制,并像“擠牙膏”似的被一批接一批曝光消除。這些真金白銀不僅數額巨大,觸目驚心,而且與一些政府機構的不作為、官商勾結等不無關系。企業和公眾從政府改革舉措的“紅利可得感”中才有所感悟。人們終于發現:原來人為設置的那么多看上去天經地義、花樣迭出的繁瑣審批、條條款款和巨額收費竟然是可以在一夜之間取消的;原來長期承受非常冤枉的沉重負擔,竟然是可以不用繳納、不應繳納的;原來眾多管理機關經年累月、主觀隨意自我授權的繁瑣規定和做法,都是在有意無意地尋租,給企業設置時效成本障礙,完全顛倒了“誰該為誰服務”的關系。
深化改革必須轉變政府職能
降成本中央決心大,成就也大,但還任重道遠。國家統計局發布最新工業企業財務數據顯示:雖然多措并舉,2016年7月每百元主營業務收入成本仍然高達86.08元,同比僅降低了0.42元,還有巨大的壓縮空間。實體經濟企業從建設到投產面臨的收費項目繁多,如電力配套費、消防費、房屋建設稅等等,讓企業尚未進入生產程序就已不堪重負,更令有心于實體經濟的投資者望而卻步。外貿企業面臨的進口環節收費多,且收費不規范,收費項目設置和費用標準混亂,尤其是港口碼頭收費項目多,拖車費、報關費、訂艙費等多達十幾種,都是涉及到部門利益、地方利益的“肥肉”。因此,從源頭上鏟除體制性成本會觸及“體制機制弊端”和“利益固化的藩籬”,任重道遠,不可能一帆風順、沒有阻力。傳統體制賦予了各級政府機構和官員支配稀缺資源的極大權力,憑借手中掌握的行政權力,凌駕于企業、市場之上,不再是公仆為企業、為公眾、為社會服務,而是千方百計創造條件、設置門檻,要大家眾星捧月,感恩戴德,有求于己。久而久之,權力被異化為牟取私利、尋求回報的稀缺資源,使得相當一批官員本末倒置、居高臨下、擺不正自己的位置,沉醉于權力欲和滿足感,滋生了根深蒂固的恩賜施舍心態,辦事情即使“不要你的錢,也要念我的好”。可以說,體制性成本與官本位恩賜施舍心態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內在聯系。長期習慣于制造審批、自我擴權的不少機構和官員,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時刻,仍舊習慣成自然地把中央責令大刀闊斧進行改革的簡政放權、轉變職能,當作私產來吝嗇地恩賜施舍。
要深化改革,降本增效,必須轉變心態,牢固樹立正確的權力觀、責任觀、政績觀。體制機制和政府職能轉變必然要求心態轉變。面對以往的體制機制弊端、利益固化藩籬和官本位造成的嚴重后果,面對中央降成本的堅強決心和三令五申,以往心存雜念、高高在上的傲慢態度,推一推動一動的“擠牙膏”施舍心態,必須轉變為對權力、對企業、對群眾發自內心的公仆思想,形成真誠的服務意識。
觀念決定行動,不可小覷。“能攻心則反惻自消”,心態轉變對于深化改革、降本增效、消除“中梗阻”是釜底抽薪,至關重要。沒有真心,心態不端,雜念叢生,遺患無窮。越往后,鏟除體制性成本遇到的越是硬骨頭,相當一批機構和官員,并不愿意主動作為,而是中央三令五申、巡視督察嚴令之下很不自覺、很不情愿、迫不得已的無奈之舉,稍有放松,就會走樣變味。對已經鏟除的名目繁多的審批權等各項規定,若不加以警惕,還會卷土重來。因此,必須率先破除官本位、父母官恩賜施舍的心態,才可能克服阻力,防止反彈。
按照經濟學成本理論,一切節省最終都歸結為時間成本的節省,即經濟節奏加快,經濟流程順暢。通盤算下來,鏟除體制性成本減輕企業和公眾長期承受的沉重負擔,可達幾萬億元之巨,更大的改革紅利還在后面,需要乘勝追擊、趁熱打鐵,不能松勁。按照時間表和路線圖,經過一兩年努力,實體經濟企業減負降本增效有望取得初步成果,三年左右可實現企業綜合成本大幅下降,盈利能力和企業競爭力顯著增強。當然,也要充分估計到,剔除隱形體制性成本是一項難度大、影響廣、極具挑戰的艱巨任務,不能僅僅當作為企業解困的權宜之計,而應在全面深化改革總進程中始終作為戰略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