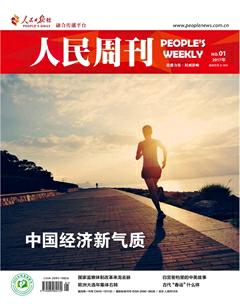茅盾:從“商務”走出的文化巨擘
劉一穎++逄春階
商務印書館總經理于殿利說,茅盾是從商務走出的文化巨擘,商務十年,培養了茅盾;反過來,茅盾在商務的編輯工作和革命活動,推動了商務的改革,使得商務在新文化的潮流中,成為百年商務歷史濃墨重彩的一章。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魯迅先生說,要改造國人的精神世界,首推文藝。舉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園,都離不開文藝。當高樓大廈在我國大地上遍地林立時,中華民族精神的大廈也應該巍然聳立。我國作家藝術家應該成為時代風氣的先覺者、先行者、先倡者,通過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文藝作品,書寫和記錄人民的偉大實踐、時代的進步要求,彰顯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鼓舞全國各族人民朝氣蓬勃邁向未來。”
文運同國運相牽,文脈同國脈相連。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1917年初開始發起的文學革命,反對文言,提倡白話,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樹起中國文學史上一個鮮明的界碑,標示著古典文學的結束,現代文學的興起,在推動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鑒往知來,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中,需要堅忍不拔的偉大精神,也需要振奮人心的偉大作品。
習近平總書記11月30日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指出,“文藝要反映生活,但文藝不能機械反映生活。茅盾說過:‘文藝作品不僅是一面鏡子——反映生活,而須是一把斧頭——創造生活。”茅盾是商務最早的黨員,張聞天受其影響特別大。張家非常殷實,父母困惑,“為什么去搞革命?”
剛剛于8月5日當選的中國茅盾研究會會長、華東師大教授楊揚說:“茅盾晚年說過,如果不是到商務印書館來工作,可能就沒有他自己文學上的成就。商務印書館對茅盾來說,具有特殊的意義。在上海龍華烈士陵園,可以直觀地看到為什么茅盾在商務獲得這么大的成就。就茅盾的事業來說,在商務主要有兩方面,一個是在革命這條線上跟陳獨秀取得了聯系,進入到政治領域;一個是在文學這條線上跟文學研究會建立了聯系,從而開始從文學上進入主流。在龍華烈士陵園里面有大量的照片,商務是早年中共在上海活動的一個重要集中地。我要說,張聞天受茅盾影響特別大,張聞天是上海人,家境非常殷實,他搞革命以后,父母不認同,‘你為什么去搞革命?我們家里日子這么好過,過年時候不允許回家,張聞天就跟著茅盾到烏鎮的家里熬過最困難的時期。”
作為茅盾的同鄉,中國茅盾研究會原副會長、浙江省新聞出版局原局長鐘桂松先生,四十多年來,長期埋首于以茅盾為主的現代文學研究,他是新版《茅盾全集》(42卷)的主編,寫出了《茅盾評傳》等十多部茅盾研究作品,最近剛剛出版了《起步的十年——茅盾在商務印書館》,他說:“100年前,茅盾20歲,走進了商務印書館,1926年茅盾因為革命而離開商務印書館。茅盾走上社會的第一個十年,是在商務印書館度過的。他從翻譯‘衣、食、住通俗的科普作品起步,到中共1921年成立前為《共產黨》雜志翻譯國外共產黨黨綱等建黨理論和學說,為我們黨的早期建設提供建黨知識;從翻譯世界文豪的作品,到翻譯世界少數民族作家的作品,茅盾孜孜不倦。翻譯是貫穿于茅盾商務十年的一個重要內容。我們現在看到的《茅盾譯文全集》,10本書里面,有8本是在商務印書館十年間翻譯的,200多萬字。所以,這十年他從翻譯起步,從翻譯國外文藝作品、國外的文論、政論里面,他逐步認識了解了馬克思主義,最終成為信仰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
24歲主編提“三條方針”革新《小說月報》,與舊文學決裂
鐘桂松說:“茅盾當年是從烏鎮小地方來的年輕人,在商務印書館沒有背景,他不認識商務印書館董事長張元濟,但是他沒多長時間就嶄露頭角、脫穎而出,這個成才環境值得我們探討。除了茅盾才華橫溢以外,商務印書館的前輩對這個年輕人的關心和愛護,值得我們今天所敬仰。”他指的是,讓24歲的茅盾擔任《小說月報》主編的事兒。
隨著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傳統《小說月報》因內容與時代脫節,銷量直線下滑。為解燃眉之急,商務印書館開始尋找更合適的人選。茅盾被張元濟、高夢旦(編譯所所長)看中。1920年11月下旬,高夢旦等找茅盾談話,希望由茅盾擔任《小說月報》《婦女雜志》兩本雜志的主編。考慮到精力有限,茅盾表示只擔任《小說月報》的主編,并在了解《小說月報》存稿情況以后,提出“上任條件”——就是現代編輯史上有名的三條革新《小說月報》的方針。一是現存稿子(包括翻譯)都不能用,二是全部改用五號字(原來的《小說月報》全是四號字),三是館方給主編全權辦事的權力,今后不能干涉雜志的編輯方針。高夢旦代表館方全部接受,于是茅盾開始對《小說月報》進行全面革新。
鐘桂松認為,這三條要求反映出茅盾把握住了新文學發展規律。“就第一條而言,現存稿子不能用,表達了與舊文學決裂的決心和勇氣。要宣傳新文學,絕不能與舊文學藕斷絲連,否則新文學就沒有戰斗力,沒有戰斗力也就沒有生命力。至于第二條四號字改為五號字,粗看起來是一個技術性的要求,其實也是茅盾為新文學的發展提供了盡可能大的舞臺。五號字發表容量更多了,讀者對象也發生變化。字號變小,將失去中老年讀者群,吸引廣大年輕讀者。第三條則是關鍵,沒有商務印書館當局給予全權處理編輯事務的授權,就無法實施《小說月報》的全面革新,自然無法讓新文學作家在這個文學陣地上發表作品。”
茅盾接受《小說月報》主編之任不久,1921年1月4日,以“研究介紹世界文學,整理中國舊文學,創造新文學”為宗旨的文學研究會在北京中央公園來今雨軒(今中山公園內)正式成立,作為發起人之一的茅盾因在上海未能參加。革新后的《小說月報》“無意”中與文學研究會的文學主張相呼應,推動中國新文學的發展與進步。對此,鐘桂松也十分贊同,“我們現在回過頭來看,如果當年沒有文學研究會,沒有茅盾革新的《小說月報》,中國新文學運動的進程會遜色不少或者延緩。”
利用《小說月報》陣地鼓吹新文藝,茅盾不遺余力。早在1922年初,魯迅的《阿Q正傳》在《晨報副刊》上連載時,茅盾就以《小說月報》編者的名義,對其進行了很高的評價,稱這部作品“實在是一部杰作……是中國人品性的結晶”。
作為“共和國的文壇保姆”,
他拯救了一朵即將枯萎的“百合花”
新中國成立后,茅盾擔任文化部長、中國作協主席,還兼任《人民文學》雜志主編,被譽為“共和國的文壇保姆”。第13任《人民文學》主編施戰軍談到茅盾先生,他說:“最近茅盾的一篇文章比較火,叫《談最近的短篇小說》,就是給1958年6月的《人民文學》所寫的一篇文章。那張手稿后來外流出去,拍出了1000多萬元的價格。在‘大躍進的社會背景下,那么喧嘩的一個時代下,他能從藝術、節奏、速度、情感等方面分析了幾篇小說。一位作家能在巨大時代命題下,非常關注藝術的發展、藝術的邏輯和藝術的享受,這是只有了不起的大文人才能做到的境界。”
正是這篇《談最近的短篇小說》拯救了一朵即將枯萎的“百合花”。1958年的一天,正在翻看《延河》文藝雜志的茅盾忽然眼前一亮,就像在沙漠里突然發現了綠洲。這片“綠洲”就是茹志鵑的《百合花》。茅盾從故事展開、人物塑造、手法布置等角度,結合小說原文的語言和細節,對這篇小說進行剖析。他寫道,“我以為這是我最近讀過的幾十個短篇中最使我滿意,也最使我感動的一篇。它是結構謹嚴,沒有閑筆的短篇小說,但同時它又富于抒情詩的風味。”
茅盾不知道的是,《百合花》發表不久,作者茹志鵑的丈夫被戴上“右派”的帽子,被開除黨籍、軍籍,這朵“百合花”正面臨著嚴峻的考驗與磨難。當茹志鵑于1958年6月在《人民文學》上第一次讀到茅盾的評價時,激動不已。茅盾的這篇評論如及時雨一般,滋潤了“百合花”的心田,讓她重燃斗志。1980年,百花文藝出版社準備出版茹志鵑的短篇小說集《草原上的小路》。茹志鵑第一次張口向茅盾求序,正忙于寫回憶錄的茅盾沒有推拒,寫下了文采飛揚的序言。商務印書館總經理于殿利說,茅盾是從商務走出的文化巨擘,商務十年,培養了茅盾;反過來,茅盾在商務的編輯工作和革命活動,推動了商務的改革,使得商務在新文化的潮流中,成為百年商務歷史濃墨重彩的一章。一百前播種的新文學的小樹,如今已經長成枝繁葉茂的森林。茅盾走過的道路,作出的開創貢獻,值得我們永遠追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