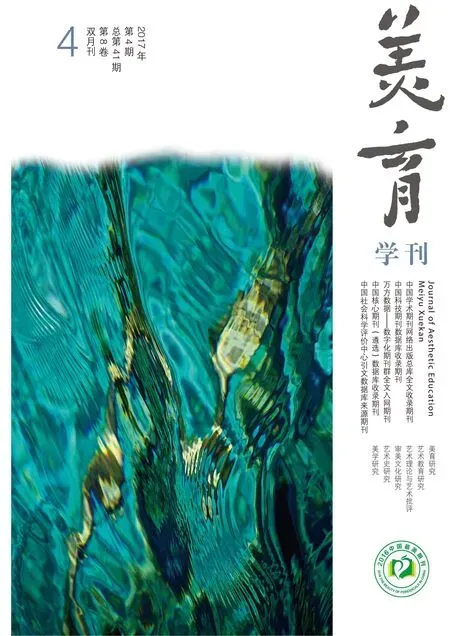文學美育的可能:在人與世界的審美把握中形塑健全人格
葉繼奮
(寧波大學 教師教育學院,浙江 寧波 315211)
?
文學美育的可能:在人與世界的審美把握中形塑健全人格
葉繼奮
(寧波大學 教師教育學院,浙江 寧波 315211)
當下社會功利化、世俗化以及學校教育的唯知識化傾向,對青年學生健全人格的形成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顯而易見。文學將視界投注于人與自然、人與自我、人與他人、人與社會多個層面,是對人與世界的審美把握。文學美育為形塑健全人格提供了可能:在盡享自然的博大精深中詩化和強健了人類自身;通過閱讀更新視界得以認識、否定和超越自我;補償與滿足人的虛擬性體驗并以此形式聯結他人;將想象的翅翼自由地伸展于歷史與未來及個人、民族與人類的多維時空,并通過具體的生活圖景昭示人生的意義,回答人類普遍的存在困惑和價值追詢。
文學美育;可能;人與世界;審美把握;形塑;健全人格
所謂“健全人格”,包括健康強壯的體格、自由充實的心靈、 充沛豐盈的感性、清朗明澈的理性、富有教養的意志力以及奉獻人類的情懷等要素,也即在生理、心理方面發展良好的并能協調平衡個人與他人、社會關系的一種優化人格。 “健全人格”是人類個體全面發展的理想標準。但當下社會的功利化、世俗化以及教育的過度理性化等因素影響了健全人格的形成與發展。審美教育為之開辟了通途。“如果說以感性教育界說美育是偏重于美育的根本特性,那么,以人格教育界說美育,則是偏重于美育的根本目標。”[1]文學對此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文學藝術“將自己的視界投注在人與世界的整個體系,即人與自我、人與他人、人與社會(人類)、人與自然四個層面上”,這個體系幾乎囊括了人與整個世界的豐富而復雜的層面,能夠最廣闊而深刻地展示人性。不僅如此,文學藝術通過審美體驗的方式能夠對人產生深刻影響,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顯示了文學藝術審美價值的本質特征——“藝術價值不僅在于完成作品,而且更在于完成人的靈魂的鑄造,從而改造人的個性心靈,影響他的感覺、情感、理智和想象”[2]。 教育的人文價值在于:通過學習認識自然、認識社會、認識自我,達到人與自然、人與自我、人與他人、人與社會的和諧,從而最終實現健全人格的形塑。文學特有的美育功能以及作為教材載體的文學作品,為形塑青年學生的健全人格提供了可能。
一、人與自然:“吾善養吾浩然之氣”
人與自然具有最為天然密切的關系,人“生于斯,長于斯,歌哭于斯,也必死于斯”,自然是人的襁褓和歸宿。愛默生在《論自然》中,以其詩性睿智的筆調闡述了自然給人類帶來了諸如美、語言、紀律(理性)、精神等種種恩惠,將自然尊稱為人類的“慈母”“舒適甜蜜的家”,認為大自然之于人類的真正地位在于,“所有正當的教育都力圖在此位置上確定人類的存在價值,并且依此樹立人類生活的目標,即人類與自然的關系”[3]。《課程標準 》提出要在文學閱讀中“體味大自然和人生的多姿多彩,激發珍愛自然、熱愛生活的感情”,即學會正確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通過與自然和諧相處達成個體人格的和諧發展,旨在致力于人的感性和理性的均衡發展。
文學書寫的“第二自然”給我們帶來了有關人與自然的諸多啟示。文學使人領略到自然的“不言之言”:在荒原落日中,我們感受到它的仁慈、眷戀以及死亡的壯麗神圣,甚至歷史的昨日和未來;文學啟示我們生命短暫、自然永恒:“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取之無禁,用之不竭”。在英國19世紀浪漫主義詩人華茲華斯、濟慈、雪萊的華彩詩篇中,人們在山林鳥鳴、田野草原、清晨黃昏、秋風冬雪中,聆聽來自天堂的啟示,感悟生命如隨四時轉換而生生不息,放聲謳歌理想和自由。我國“京派文學”則以淡雅疏朗的筆墨虛擬了一個寧靜單純的理想家園。富有意味的是作者偏要把人物安置于偌大的山水中,而主人公的故事總要等到美景風情鋪敘之后才舒緩而適時地推出,自然與人的親切關系在此得到了生動演繹。文學還生動地再現了人類開發自然的歷史情景,并同時啟示人與自然如何保持適度關系。當人類從迫于生存之慮開墾拓荒及至無節制的占有和攫取時,在瓦爾登湖享受慵懶陽光和無憂青春的夢幻結束了:“這惡魔似的鐵馬,那震耳欲聾的機器喧囂聲已經傳遍全鄉鎮了,它已經用骯臟的工業腳步使湖水渾濁了,正是它,把瓦爾登湖岸上的樹木和風景吞噬了。”(梭羅《瓦爾登湖》)而狼的“從一個山崖蕩到另一個山崖,回響在山谷中,漸漸地消失在漆黑的夜色里”的“一聲深沉的、驕傲的嗥叫”,以及它被大量捕殺之后山林的荒蕪、草原的疲憊、沙塵暴的降臨等種種災難,留給人類有關人與自然的無盡思考。(奧爾多·利奧波德《沙鄉年鑒》)后來的事實證明了奧爾多·利奧波德的隱憂并非杞人之憂,但足以令他安慰的是,這個來自荒野的隱藏在狼的嗥叫之中的啟示已被人類所領悟:人類學會了“像山那樣思考”。在利奧波德離世半個世紀后,隨著人與自然關系的日趨緊張,中國當代文學刮起了一陣急遽強勁的“狼風”,標志著“非人類中心主義”的“生態文學”的興起,它同時也標志著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在新時代的進一步深化。總之,文學不僅以神奇的語言將人們見所未見的優美、崇高的山川風光攝入筆端,而且還立體地展現了人類與自然相互間的對立與融合、依存與抗衡等多種關系。人在與自然的相處中,領悟到來自天地宇宙間神秘超然的哲學啟示,得以從容地再度打量人類自身留下的歷史足跡。
文學作品中描述的優美自然使我們如沐春風,不知不覺地培養起對于自然的感情,人們從文學作品提供的間接世界中感悟人與自然的真諦。欣賞自然的人堅信:“大自然不僅是我們的衣食父母,而且對于培養我們的審美心胸,對培養我們的高尚情懷,對于我們健康人格的形成,大自然都具有一種不可替代的珍貴價值。”[4]欣賞自然的人也必然是一個追求“詩意的存在”的人。 但由于近代工業文明帶來的功利原則以及分工細化,使人在智力高度發展的同時導致人格的畸形與殘缺。“人文”與“工具”的對立,“感性”與“理性”的失衡,已經成為現代教育必須正視和研究的深層次問題。對大多數青年學生而言,想象力、閑情逸致是一種奢侈的追求。一些事實表明了他們與自然的隔膜及感性的缺失:他們漠視明麗的春光與飄飛的楊花;他們驚喜于冬日的初雪卻因表達的無能而尷尬;他們無法破譯大自然千姿百態的表現形式的密碼。過度發達的抽象理性和務實功利的價值取向擠壓了人的感官和情緒。 “在現代化進程中誕生的西方現代美育理論的一個歷史性貢獻在于對現代社會中人性異化的揭示和批判,從而使得現代美育理論成為了一種現代文化批判理論的思想資源。這種批判是從‘理性壓抑感性’這一歷史現實出發的,其正題是人的感性生存和個性的完整。”[5]
如果說文學以其生動形象的描述使人感受自然,那么,通過審美“移情”則有助于恢復人的感性。威廉·沃林格“把移情解釋為來自在機體和生命中發現的一種合理的快感,它不僅想模仿自然對象,更要‘把原初生命的線條和形式投射……出來,進入理想的獨立自在和完美之中(并因此)在每一次創造中為人自身生命感知自由無阻的行為提供一個舞臺(競技場)’”。[6]206-207由于“內摹仿”作用,審美“移情”使人不自覺地根據自己喜好有所選擇地摹仿自然,在潛移默化中移入個體生命中以滋養精神提升氣質—— “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此外,“移情”并不只是人的情感“外射”到自然萬物,而是人與自然萬物“情感投射”的互動游戲,即人在“移情”于萬物的同時,也在自然萬物的濡染中得到種種恩惠:撫慰、美感、愉悅或者啟示等。總之,“優美的山野令人心曠神怡,它使我們的精神從人生的憂愁中解脫出來,賦予我們以勇氣和希望。奔流不息的大河,使僵化的思維活躍起來,得以擴展死板的思維范圍。郁郁蔥蔥的大森林還誘發出對萬象之源——生命的神秘感謝,喚起對生命的尊重意識。”[7]此外,審美“移情”的心理機制是“同情”,它能改善人的德性。“移情”已“無法成為今天藝術理論的一個有用的或描述性的詞匯”,“但它被精神分析學挪用過來,指‘某一個體感受他人的需要、渴望、挫折、歡樂、悲傷、焦慮、傷害以及真正的饑渴的能力,似乎這些東西就是他自己的一樣’(阿恩海姆語);因此,‘移情’是一種超級同情”。[6]203-204然而,即便不是因為精神分析學的研究證明,“移情”本身具有的廣泛的同情作用也是顯而易見的。“移情”消除了主客體之間的存在界限,主體完全投入到客體中去,在對象中流連忘返,進入忘我境界。對客體而言,它與生命顫動的主體融為一體,實現了無情事物的有情化,無生命事物的生命化。“移情”就是“宇宙的人情化”,它有助于養成人對世間一切事物博大的仁愛同情之心,從而達到健全人格之目的。通過“移情”,“我們這種對于人類社會的同情,還可以擴充張大到普遍的自然中去。”把自然草木鳥獸都當成人的眷屬和同胞,這樣就能發生極高的美感。[8]我們也可以把通過審美“移情”而提高的同情心廣施于整個社會和人類,實現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總之,“移情”不但能恢復人的“感性”,而且還具有倫理價值。它是心靈的藝術體操,有助于柔化被理性壓扁了的感性“結節”;它以神奇的力量使人投入到“第二自然”中,從而在盡享自然的博大精深中詩化和強健了人類自身。
二、人與自我:從“自己所是的東西中解放出來”
認識自我是實現自我的前提。但認識自我是困難的,尤其對于人生閱歷及理論修養不深的青年學生而言。人如何認識自我?在克里希那穆提看來:“‘我’并不是一個抽象的存在,‘我’無法透過抽象的思考來認識自己,‘我’必須在我的具體存在中,認出我之為我,而非理想的我。”[9]因此,觀察“我”自己在關系中的表現,會發現自己的真相。克里希那穆提的描述無疑是睿智的。但是,實際生活又會在不同時空和獨異的體驗場景等方面給人帶來限制,從而使人局限于個體自我的單方面了解,而無法對真正的自我獲得真知。
文學給人提供了得以突破局限的廣袤時空,以它整體的、感性的、可體驗的形式,將一切都描繪得栩栩如生,使人仿佛置身其中,從而獲得了在多維關系中認識自我的可能,因而 黑格爾認為欣賞就是“在藝術作品里重新發現自己”。此外,文學所描繪的生活是一種“應然性圖景”, 作家的生命意識與人生態度自然地流泄或包孕在場面、細節之中,包含著“應該如此”的價值取向。優秀的文學典型集中體現著人類的至善至美,散發著人性光輝,是人類精華之集萃。文學給讀者以清澈的眼光,用來分辨高尚與卑下、崇高與滑稽、善良與丑惡;使讀者養成規范而優雅的情感,從而使靈魂超越庸常升華到純凈而美好的境界。因而文學不但是人們認識自己、認識世界的一個“參照團體”,而且還有判斷和選擇功能。
文學給讀者提供了“陌生世界經驗”,從而可以通過閱讀更新視界打量自我。 伊瑟爾在解釋讀者自我提高的內部活動時這樣表述:讀者在接近文本所顯示的陌生世界的經驗時是向文本敞開的:當他適應對象(本文)的召喚結構時,他疏遠和超越了先前的經驗和期待視界,這時“區別就不在主體和對象之間,而在主體和自身之間”,這種吸收陌生的經驗而更新主體的視界,仍是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產生的自我意識的提高”。反過來說,自我意識的提高來自于主體視界的更新,主體視界的更新需要吸收陌生世界的經驗,而“吸收”的關鍵是主體向文本“敞開”。如伽達默爾所言,審美理解的基本模式是“對話”,“理解是在對話中進行的”。讓文學作品進入自己的生命中,通過文學典型反觀自己,發現自己,并通過揚棄達到“超越”。“否定”是其中的關鍵環節。對此,伊瑟爾在《隱含的讀者》中這樣論述:讀者發現文本的意義,以否定來作為他的出發點:“他通過一部分至少是部分不同于他即己所習慣的世界的小說而發現一個新的現實;他在流行的規范中和他自己受約束的行為中發現了內在固有的缺陷。……發現是審美愉快的一種形式,因為他提供給讀者兩種獨特的可能性:第一,使他自己——即使是暫時地——從他自己所是的東西中解放出來,逃離他自己社會生活的束縛;第二,積極地操持他的各種官能——一般是情感的和認知的官能。”文學閱讀使人浸潤于文本特定的審美氛圍并尋找到一個新的世界,在欣欣然向往與渴慕中與舊的自我告別。“告別”,即“否定中的超越”。青年學生正處在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塑形階段,且激情充沛易于感動,文學閱讀使他們在審美愉悅中不知不覺地認同了作家傾向,并通過對這個藝術世界學會了對于自身的理解和自我提高的目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藝術就是認識。通過文學閱讀,人更加深刻地認識自我和社會,最終實現人性的自由和解放。
三、人與他人:“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
一些調查表明,由于激烈的學業競爭,青年學生屬于自己支配的時間和空間相當有限,情感態度也比較淡漠。此外,經濟發達帶來的物欲追求導致人的價值取向趨于自私功利,而由于人對網絡的依賴和網絡對人的控制,也淡化了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使得個體逐漸疏離群體而陷入孤獨,人與人之間的同情和關愛日漸喪失。文學閱讀以審美體驗的方式成為聯結人與人之間情感的紐帶。
文學能夠拓展人的視野,補償與滿足人的虛擬性體驗,認識他人和世界。優秀的文學作品總是為人們拓開著一個廣闊的“第二世界”,它使人超越時空,追溯荒古又展望未來;它啟迪人們領略各色人等,體驗生活百味。從人與他人的關系而言,文學能幫助人突破自身對人生體驗的有限性,根據人“從人生經驗、精神(包括情感)體驗兩方面產生的延展要求,分別在時間的過去與未來、空間的天地與異域等維度上全面展開,從而構成了文學內涵的巨大豐富性”[10],補償和滿足了人對未曾親歷生活的虛擬性體驗。
文學通過情感體驗聯結他人和世界。“善是通過行為和行動,在關系中體現的。”[11]30僅憑理性認識,人與世界的交往就停留于“我與它”的二元對立的關系,彼此處于陌生隔膜狀態。僅以旁觀者的身份,對作品中描述的人和事冷眼相看,那么,文學閱讀也不會使我們與之產生密切關系,我們在作品中讀到的一切,與路過某地碰巧目擊了一起事件幾乎沒有二致。文學閱讀以審美體驗和想象的特殊方式,產生一種推己及人的作用,不知不覺地改變了讀者與主人公之間原本彼此分離的關系,它以一種強勁的力量把你拖曳進去,與書中人物一起經受甜蜜與痛苦、歡樂與憂傷,從而體驗他人的生存狀況。“情感生活激發人的自我意識和生存自覺,使人具有自由意志和道德人格,而在自己身上實現個人性和社會性的統一。”[12]反復多次的感受和體驗可以使人的心靈變得細膩敏感。這種柔弱的力量使人通過想象體察陌生世界,感受他人精神上的痛苦,推己及人,以心比心,溝通自己與他人情感上的聯系。認識到世界是一個整體,人不是彼此孤立互不相關,而恰恰是密不可分相互依賴的。那些河流、山川、森林屬于人類,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生存于廣袤的土地上。盡管每個人在生理和物種方面存在很大差異,但是,人類對于喜怒哀樂的感受大致相同。“一個人就是整個人類。他不只是代表人類,他就是人類這個物種的全部。本質上,他就是人類的整個心智。……你對整個人類負有責任,而不是作為個體對自己負有責任,那是一個心理上的幻覺。作為整個人類物種的代表,你的反應是整體的,而不是局部的。于是責任具有了一種完全不同的含義。”[11]17人與世界聯系的思維方式,可以使我們對周圍的人和事產生深刻的愛,從而逐漸養成博大深厚的摯愛情懷,形成把自我與他人、個體與世界聯系在一起的思維方式:“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13]這在社會經濟高度發達及人與人之間競爭激烈的當下顯得尤為重要。
四、人與社會:“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
每天機械地做題和頻繁的測試,幾乎是高中學生的生存常態,做題的最終目的指向升學,之后是“就業”。生存空間狹窄化,人生目標短期化,價值取向功利化,等等,捆綁了理想的翅膀,讓人往世俗的地面下墜。如何腳踏實地地籌劃事務又堅定地超拔出來,讓心靈指向“無限”與“自由”;如何掙脫自我外殼的束縛,即使身處斗室也能與大千世界息息相通;如何解放學生的心靈,使學習成為自我塑造與審美享受的“自由自覺”行為?“文學與人生”是一個永恒的話題,文學必然涉及“人與社會”這個深度命題。
人與社會的關系,簡而言之就是“人是社會的人”“社會是人的社會”這兩種互相依存關系。人與社會的聯系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政治經濟、倫理道德、文化宗教乃至錯綜復雜的人際關系,“都附著和載負于現實的活生生的社會的人的身上。人只能也必須生活在這些關系中”[14]。人與社會的密切關系,決定了人的發展一刻也離不開社會的發展。人對存在現狀的不滿是社會革命發生的直接動力。文學生動地展示了社會的人如何以其睿智、雄心和強勁的力量推動歷史車輪向前滾動,促進人類社會不斷發展的動態畫卷。文學展現了革命以排山倒海摧枯拉朽之勢,掀起巨瀾轟毀舊社會根基創建新社會的恢宏圖景,使人領略到通過社會的人的努力如何推進社會的迅猛發展,從而創造了更適合于人的生存的社會,使人在這個合理的生存狀態中得以提升人的社會屬性,促進人的社會性和社會的人的雙重發展。
與歷時性動態的時間角度相對應,文學還從共時性的靜態的空間角度,在更廣闊的界面上展現了自然宇宙、歷史文化、道德風俗、戰爭苦難等宏大景象,把人的視野引向大千世界,思考有關區域經濟、人口爆炸、全球一體化等人類面臨的重大問題,在更深刻層次上觀照人性、本原與社會人生,引導人對自然、人類、宇宙萌生出一種大關懷。文學展示了不同膚色的人種、不同文化信仰的民族、不同政治主張的國家以及經濟發展不平衡的不同區域的全方位生態圖景,這使我們得以置身于世界大格局中,審視和思考一系列問題:我們自己得以生存其中的民族、國家所處的地位;我們作為其中一員身負的責任;我們如何把個人發展和民族、國家甚至人類的同步發展結合得更好。
與科學闡述和歷史記載不同,文學更深地觸及人的靈魂,多層面地展示了不同社會地位、階層、身份的人在社會巨大變革中不同的價值觀和人生選擇,細膩地刻畫了人的迷惘、痛苦、焦慮、矛盾和掙扎的復雜心理,經歷大浪淘沙后把正確答案告訴人們。文學總是以具體的人生故事演繹普泛真理:人生道路的選擇以及對人生價值的確認,并不純粹屬于個人私事,人的社會屬性已不由自主地把單個的人與社會整體緊密而又復雜地纏繞在一起。宏觀地講,人作為社會活動主體籌劃、忙碌并決定著社會發展總體水平,而社會發展的同時又提升了人類精神新的質態,社會的人的發展是與人的社會的發展相同步的。唯其如此,文學感人的力量及其對人的心靈發揮著如此巨大而又持久、深刻的影響。
總之,“個人發展和社會發展是互為因果的。個人的發展、個人有意識有目的的活動是受社會發展的客觀必然性支配的,而社會生活、社會關系中的一切又都是發展著的個人創造和改變的。社會的任務就是最大限度地滿足和推動個人的發展,個人最大限度地發展自己,適應、配合社會的發展,即在自由全面地發展個人中發展社會,在充分發展社會中發展個人,并盡可能使個人發展與社會發展協調起來,從而達到社會和個人共同發展的目的。”[15]文學以強大的藝術感召力引導人進入歷史與未來。每一個歷史轉型的關鍵時刻,也往往是偉大文學家誕生之時。他們以其高尚的藝術良知和崇高的使命感,采取積極介入的人生姿態,向著時代和社會進言吶喊,他們的政治觀點、態度和傾向,以及自身體認到的對民族、國家、社會以至人類的認同感,以審美表達的方式滲透在字里行間,噴射出動人心魄的藝術感染力,鼓舞人們滿懷豪情勇敢地投身時代洪流,在為民族解放和人類和平的偉大事業中書寫壯麗的人生詩篇。偉大的文學家也必然是深刻的思想家,能夠預測人類歷史的發展趨勢,因而文學能以其特有的浪漫引發人對美好未來的熱烈向往,使人即便處在艱難困厄的逆境中也始終抱持光榮與夢想。文學自由地將想象的翅翼伸展于過去、現在、未來,伸展于你、我、他也即個人、民族與人類的多維時空,并通過生動具體的生活圖景昭示人生的意義和價值,回答人類普遍的存在困惑和價值追詢,引導人在社會歷史的時空中確立自身的人生坐標。文學拓寬了人的精神視閾,提升了人的生存境界,使人立足于大地又堅定地超拔其上,翱翔在“自由”與“無限”的遼闊天空,從而將僅僅滿足于生存所需的卑微勞作上升為表現人的尊嚴的自由自覺的審美創造。
我們處在一個波瀾壯闊的偉大時代,一個古老的民族懷著青春的夢想正在大步向前。它需要每一個中國人,更需要一代又一代年輕的中國人投入生命與激情,點燃熊熊的理想之火。因而,通過文學審美形塑健全人格在今天就有了鮮明的時代特征和特別的現實意義。
[1] 杜衛.美育三義[J].文藝研究,2016(11):9-21.
[2] 胡經之.文藝美學[J].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131-132.
[3] 愛默生.論自然·美國學者[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53.
[4] 樊美筠.中國傳統美學的當代闡釋[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85.
[5] 杜衛.論中國美育研究的當代問題[M].文藝研究,2004(6):4-11.
[6] 迪薩納亞克.審美的人[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7] 王治河,樊美筠.第二次啟蒙[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440-441.
[8] 宗白華.美與人生[M].北京: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12:20-121.
[9] 克里希那穆提.重新認識你自己[M].深圳:深圳報業集團出版社,2010:23.
[10] 朱壽桐.文學與人生十五講[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96.
[11] 克里希那穆提.教育就是解放心靈[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
[12] 王元驤.拯救人性:審美教育的當代意義[M].文藝研究,2012(3):5-12.
[13] 魯迅.魯迅全集:第6卷[M].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624.
[14] 陸貴山.人論與文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75-76.
[15] 劉遠碧,稅遠友.論人與社會的關系[M].遼寧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6):13-16.
The Possibility of Literature as Aesthetic Education:Forming a Healthy Personality in the Aesthetic Grasp of Man and the World
YE Ji-fen
(Teacher Education College,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At present, social utility, secularization and the knowledge-only tendency in school education have brought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formation of young students′ healthy personality. Because literature is the aesthetic grasp of man and the world, which focuses on multiple levels of man and nature, man and self, man and others, man and society, literary aesthetic education provides the possibility of forming a healthy personality by poeticiz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human self while enjoying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nature; recognizing, denying and overstepping the ego by updating one′ s vision via reading; compensating and satisfying man′s virtual experience to connect with others; stretching the wings of imagination freely in the multidimensional space-time of history and future, individual and nation; revealing the true meaning of life through the unfolding of concrete life and responding to man′s pervasive existentialist bewilderment and quest for values.
literary aesthetic education; possibility; man and the world; aesthetic grasp; form; healthy personality
G40-014
A
2095-0012(2017)04-0049-06
(責任編輯:紫 嫣)
2017-04-26
江守義(1972—),男,安徽廬江人,安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文藝學、美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