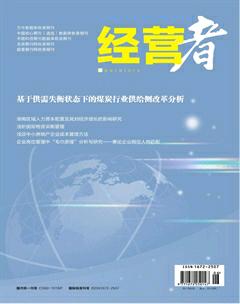淺談德國勞動法中的解雇保護制度
劉揚
摘 要 自工業革命以來,機器化大生產代替手工作坊,近代嚴格意義上的勞動關系開始出現。勞動關系在一開始,受傳統意義上的私法的調整,遵循意思自治的原則。但是隨著工業的發展,勞動者對國民經濟的貢獻日益突出,無論在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雇員與雇主(或稱為工人與工廠)之間的關系都成為最主要的社會關系。如何恰當處理這對關系,事關社會穩定與國家經濟發展。縱觀各國勞動法的發展歷史,無不是一個引入公法調整、限制意思自治的過程。德國勞動法雖未能成典,但相關法律、法條卻幾近完備,可為我國立法與法學研究提供參考。本文通過比較法,對比中、德兩國解雇保護制度的異同,簡述德國解雇保護制度對其勞動關系、社會發展的影響及其發展趨勢,旨在為勞動法學研究作出貢獻。
關鍵詞 預告解雇 非預告解雇 《解雇保護法》 《勞動合同法》
一、德國解雇保護制度與中國解雇保護制度的區別
(一)德國解雇保護制度的基本內容
解雇,顧名思義,指的是在勞動關系中,雇主一方基于單方意思表示,通知雇員結束勞動關系的行為,其本質為繼續合同的終止。所以,在法律權利類別中,應當歸為形成權。由于勞動法具有社會性,因此解雇不能僅以傳統的合同法規制,其“單方面性”必然受到更為嚴格的限制。
在德國,根據是否需要遵循一定的期限,可將解雇分為預告解約和非預告解約。民法典第622條和第626條分別就預告解約的期限和非預約解約的成立條件、行使時效作了詳細的規定。以此為基礎,可將解雇保護制度分為解雇前保護機制、解雇中保護機制與解雇后保護機制三類。這些機制大部分規定在《解雇保護法》之中,同時還散見于《母親保護法》《聯邦教育補助金法》《職業培訓法》《勞動崗位保護》《企業組織法》等。
1.解雇前保護機制。所謂解雇前的保護機制,主要是通過立法措施對解雇中可能出現的非法解雇雇員的情況進行規制。法律所具有的指引作用,使得雇主在解雇雇員時需要遵循相關法律規定,否則會因實體性或程序性問題而導致解雇無效。立法的保護又大致可分為三類,即解雇期限的規定、解雇無效條款的規定以及針對解雇保護問題而專門頒布的《解雇保護法》中的規定。
第一,解雇期限的規定主要適用于預告解約,規定在德國民法典第622條,縱觀該條6款規定,除第4款主要涉及工資協定之外,解雇期限根據私法自由的原則又可分為法定預告解約(1~3款)與約定預告解約(5~6款)兩種。而約定預告解約期限也有限制,即不得短于辭職期限(4周的基本期限),否則將因違反法律法規而歸于無效。
為了緩解處于被動地位的被解雇人因失業而承受的壓力,使其有相應的時間來尋找新的工作機會,盡快適應新的社會環境,解雇期限雖不能直接達到阻止雇主解雇的效果,卻也間接保護了雇員的利益,因此應當被視為解雇保護的一部分。
第二,解雇無效的條款散見于與勞動法相關的法律法規和法條之中。《母親保護法》第9條第1款規定了在預約解約和非預約解約情況下,對于孕婦(包括在解雇后2周內發現自己懷孕)以及分娩4個月內的母親的保護。《聯邦教育補助金法》第15條、第18條規定了對子女年齡不超過3歲的父母享受父母假期且不得僅因此而被解雇。《勞動崗位保護法》第2條第1款規定了對依法服兵役期間的雇員,雙方得暫停勞動關系,且在服役期間不得預約解約。德國民法典第611a條規定了禁止歧視原則,除了證明性別區分是必要且適當的,雇主在預告解約時不得因性別而歧視雇員。隨著女性生產潛力的激發,女性對于自身的經濟地位、政治地位提出了更高要求,禁止就業中的性別歧視在世界范圍內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并得到認可。聯合國《1958年消除就業和職業歧視公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對這一原則作了詳細的闡述和規定,為各國的職業就業立法提供了參考。德國民法典613a條第4款規定了在工場轉讓或部分轉讓時,原雇主、新的所有權人不能解除原有的勞動關系,雇員不必承擔由于企業所有權變化帶來的失業風險。
第三,《解雇保護法》是德國針對解雇保護制度進行的專項立法,有很多值得借鑒的原則和制度。該法第13條厘清了其所規制的解雇形式與其他解雇形式的關系,非常解雇、其他形式解雇不能適用于本法,反之,預告解約形式的正常解雇則要受到本法的規范。
在該法律中,有兩項十分重要的原則,即正當理由原則和社會選擇原則。分別規定在第1條的第1款、第2款和第3款。
從法條來看,正當理由原則分為雇員本身、個人行為和企業緊急需要三種情況。法條雖然沒有對此三種情況的具體內涵加以明確,但根據實踐過程中勞動關系解除的案例我們不難總結出,所謂雇員本身原因是指雇傭過程中,雇員因個人原因喪失其賴以建立勞動關系的條件,無法繼續以勞務為對價獲取報酬的情況。常見情形為因病、專有技能喪失或其資格被取消。個人行為是指雇員在完成其工作過程中,故意或過失違反勞動合同義務,嚴重違反規章制度的行為使得雇主有理由認為勞動合同無法或者不適宜繼續履行的情況。企業緊急需要是指企業因經營原因導致需要減少雇員,如為了保證企業正常運轉而進行的裁員,常見原因有企業經營不善或技術革新等。
社會選擇原則是在因企業緊急需要而解雇的情況下需要遵循的另一項原則,即企業在決定解雇的時候需要考慮的社會因素,包括工作年限、撫養義務等。該項原則的適用有較大的限制,除解雇情形之外,其適用的雇員也有一定的限制。“如因為企業技術、經營或其他的原因須繼續雇傭某個或某些雇員而不能根據社會因素挑選被解雇人員時,第一句不適用”,這其實是對于解雇保護制度的一種反限制,是企業自主經營權的一種體現,企業在一定情形下可以不必考慮社會因素而留用對企業發展有利的雇員。
2.解雇中保護機制。解雇中的保護機制主要是指解雇必經的程序保護措施。德國《企業組織法》第102條第1款:“任何解雇必須經由企業委員會聽證。雇主必須向企業委員會說明解雇理由。沒有經過聽證的解雇為無效解雇。”這種聽證制度的設立對于雇員的保護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為未經聽證的解雇無效,其二則是企業委員會在聽證后所出具的反對解雇意見書。雖然不能阻止解雇效力的發生,但是對于之后雇員提起解雇保護訴訟時,法院是否認定雇主解雇有“正當理由”則有很大的影響。這種情況下,雇主不得不審慎考慮解雇事宜,以免承擔不利后果。當然,此項機制也有其限制,《企業組織法》第102條第2款對企業委員會提出反對解雇書面意見作了一定的限制。
3.解雇后保護機制。解雇后的保護機制主要是雇員通過提起解雇保護訴訟來獲取司法救濟,已達到確認解雇無效或者以獲得解雇賠償金為前提同意與雇主達成和解解除勞動關系的目的。《解雇保護法》第5條、第6條規定了在3周解雇保護起訴時效之外的特殊時效:延誤起訴之允許和可延長之起訴期限來保護雇員。雖已盡到最大努力,但仍未能及時提起訴訟的情況和以其他原因提起確認解雇無效之訴后,可在一審口頭審理結束前根據本法第1條的第1款、第2款、第3款來補正訴訟理由。需注意的是,第5條所規定的保護能否得到實現,仍要法院以決議的形式得出,而非當然取得。
除確認解雇無效之外,實踐中更為常見的是解雇補償金制度。勞動關系所具有的人身隸屬性決定了雇主與雇員雙方之間的和諧與信任對于勞動合同順利履行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司法救濟往往是雙方幾經協商談判未果而采取的一種手段,此時雙方之間的矛盾已然到了需要法律介入才能平息的地步,其和諧、信任早已消磨殆盡,所以在很多時候,單純判決解雇無效、勞動合同繼續履行并不能合理地解決此類問題。解雇補償金制度是指雇員和雇主在法院確認解雇無效的情況下,不愿繼續維持勞動關系而提出申請,由法院解除勞動關系并判決雇主支付適當的一次性補償金。《解雇保護法》第9條、第10條分別對解雇補償金的適用條件和補償金額確定作出了規定,在這種類似和解的程序下,雙方的利益得到了有效的平衡。
(二)中國解雇保護制度基本內容
中國解雇保護制度的社會背景較之德國有鮮明的區別。在計劃經濟時代,中國企業缺乏經營自主權,就業特點主要是對勞動力的計劃配置、統包就業、行政調配、城鄉分割。在這種情形下,解雇保護制度似乎并沒有存在的意義。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政企分開的改革,企業的經營、用工更加自由,勞動力在市場上自由流通,用人單位與員工之間的利益矛盾逐漸暴露出來,解雇保護制度才得到生發和重視。
《勞動合同法》的頒布實施,標志著我國解雇保護制度有了系統性的進步。解雇保護制度規定在《勞動合同法》的第四章“勞動合同的解除與終止”中有所規定。縱觀法條第39條到第43條,中國的解雇可以分為過錯性解雇和非過錯性解雇。過錯性解雇,即第39條所列6項內容,試用期被證明不符合錄用條件的、嚴重違反用人單位規章制度的、嚴重失職、徇私舞弊給單位造成重大損害的、勞動者建立多重勞動關系給用人單位帶來嚴重影響或經用人單位提出拒不改正的、因勞動者原因導致勞動合同無效的、被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的。這些均是因勞動者自身原因而導致的解雇,對于此類解雇,我國法律給予的保護力度較小。非過錯性解雇,法條的第40條、第41條規定非因勞動者主觀過錯導致的用人單位可以解除勞動合同的情形。在這種情形下解雇勞動者,《勞動合同法》對其作了較為詳細的限制,第41條第二款裁員時優先留用人員的規定,第42條不允許解除勞動合同情形的規定,第43條解除勞動合同時需要通知工會的程序性規定,第46條和第47條對于勞動者經濟補償金支付情形和支付金額的規定。這些規定均表現了勞動法的社會法性質和對于勞動者的傾斜保護,是我國解雇保護制度的集中體現。
相較于德國的解雇保護制度,我國在這方面的規定還比較簡略,還需要加強相關的立法工作,積極出臺司法解釋,并在實踐中不斷探索、總結、完善。
二、德國勞動法中解雇保護制度存在的必要性
(一)確保雇傭者和被雇傭者雙方的合法權益
解雇保護制度的存在,其目的是平衡雇傭者與被雇傭者之間的利益。主要是通過對被雇傭者的傾斜保護,來修正勞動關系中因雇員對雇主實質上的人身隸屬性而產生的不平等性。企業是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市場經濟的充分發展,調動企業的生產積極性。雖然隨著社會的發展,要求企業承擔一定社會責任的呼聲越來越高,但其本質仍然是要以營利為目的,所以在保證生產效率的前提下,盡可能地節省雇工成本,或者用更高質量的勞動力來替換原有勞動力,是企業在經營過程中無可厚非的選擇。但企業的這種選擇勢必會影響勞動關系的穩定,如果僅依靠《合同法》契約自由原則來調整這一關系,雖然主觀上雇員有權拒絕簽訂不利于自己的合同,但是客觀上多數迫于生計的雇員只能選擇接受。相對弱勢的雇員被迫忍受雇主無理的用工條件和解雇風險,其勞動權遭到嚴重的損害。德國的解雇保護制度從解雇的各個階段對雇主的解雇權進行了限制,使其不能隨意解除勞動關系,充分體現了對雇員勞動權等合法權益的保護。
(二)緩和德國民眾之間的社會關系
德國社會法僅指社會保障法,并不包括勞動法,但是解雇保護制度所具有的保護弱者利益的理念卻與社會法的本質要求不謀而合。在社會關系中,有天生的弱勢群體與強勢群體,而市場經濟的發展會自發導致強者越強、弱者越弱。如果沒有公權力的介入來保護弱者的利益,將使社會關系的失衡狀態加劇并最終導致嚴重的社會問題。如前所述,解雇保護法通過傾斜保護處于弱者地位的雇員的合法權益,緩和了雇主與雇員之間的矛盾,使雙方的社會關系天平趨于平衡。
三、結語
本文主要通過介紹德國解雇保護法在解雇的各個時段的具體制度設計,并與中國的解雇制度進行比較,從而對德國相關制度有更為直觀的感受,同時反思我國制度有待完善之處。對于德國解雇保護制度的法律價值、社會價值的闡述,希望能引起相關學者對于此項制度的發展趨勢的思考。文中對所提德國具體法律法條內容并未原文摘抄,一來因為所關注的乃法條背后之制度精神,二來諸法條人人皆唾手可得,實無羅列之必要。
(作者單位為西南政法大學)
參考文獻
[1] 黃賁.德國勞動法中的解雇保護制度[J].中外法學,2007.
[2] 姜維真.德國解雇保護法律制度述評[J].華北水利水電學院學報,2011.
[3] 王倩.德國特殊解雇保護制度及其啟示[J].德國研究,2014.
[4] 李瑩瑩.我國解雇保護制度探析[J].知識經濟,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