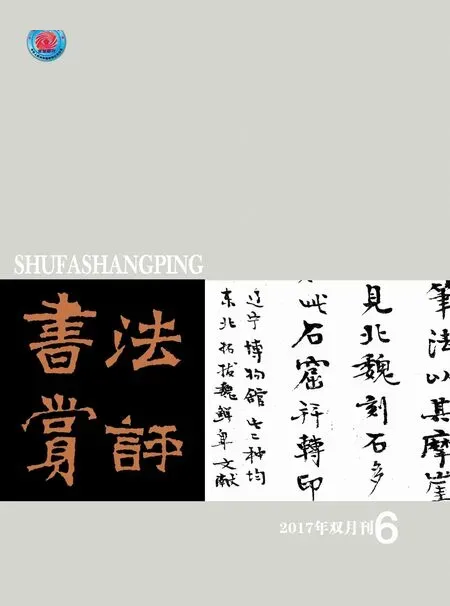出以己意 與古為徒
——石濤題款書法藝術(shù)之我見
■程仲霖
清初石濤善書畫,工詩文,具有豐富的人生閱歷和藝術(shù)想象力,以其風(fēng)格多樣的畫風(fēng)與書風(fēng),成為清初最富有創(chuàng)造性的書畫家,對后世影響巨大。吳冠中先生認(rèn)為石濤的題跋幾乎也就是繪畫,[1]更尊奉石濤為 “中國現(xiàn)代藝術(shù)之父” (吳冠中 《我讀石濤畫語錄》)。本文擬就其題款書法談點兒粗淺的看法,以請教于諸方家。

《梅竹》 出自楊成寅 《石濤》人大出版社
一、書畫融匯一體
作為一個偉大的畫家,石濤特別強調(diào)以畫意入書,以字法入畫,講求變化,不拘一格。 《石濤畫語錄》兼字章第十七曰:
“字與畫者,共具兩端,其功一體。”
意為書法與繪畫不是截然不同的兩類,在功能上密切聯(lián)系并是一致的。書法具有高度的抽象性,而繪畫始終是具象的,二者當(dāng)然不同,但它們又有共同性,都要用線條表現(xiàn)出不同形勢或體勢的變化,給觀者以美感。石濤在他的作品中,始終注意兩者的完美結(jié)合。如 《梅竹》 (紙本水墨,61cm×29cm),[2]畫面中的梅干僅
寥寥數(shù)筆,由右下端斜入左上部,頂端一小枝斜向左右上方,花開數(shù)朵,而一枝綴滿花朵的枝條凌空折下。然最妙處在題款,畫面上端從右至左滿滿的詩句直接落上枝頭花叢,字跡大大小小,筆畫牽絲連帶,方筆如枝,圓筆如花,全任自然,感覺枝繁花茂,芳香撲鼻。此乃字融畫里,畫入字間,絕妙至極,石濤一氣呵成的作品給觀者的感覺是如此的真切。現(xiàn)藏美國波士頓博物館的 《山水冊十二開》第八開題:“種閑亭上花如字,種閑主人日多事。多事如花日漸多,如字之花太游戲。客來恰是種閑時,雨雪春寒花放遲。滿堂晴雪不經(jīng)意,砌根朵朵誰為之。主人學(xué)書愛種花,花意知人字字嘉。我向花間敲一字,眾花齊笑日西斜。”不正是這幅畫的寫照嗎?
中國畫有山水、花卉、人物等不同種類,又有寫意、水墨、沒骨、淺絳等不同形式的區(qū)別,那么題款上就要求書體有別,大小適宜,意趣相合,恰到好處。石濤頗善運用畫法與字法的融合,在他的作品中,長款不厭其長甚至以不同的書體題之又題,如現(xiàn)藏天津博物館的 《巢湖圖》 (紙本淺絳,96.5cm×41.5cm),有兩段隸書款,一段行書款在隱隱的波濤上頗為壯觀。窮款至于全無,只有一枚印章而已,甚至印章也不是蓋在空白處,而是隱在樹石間。如旅居美國的王季遷家藏 《為禹老道兄作山水冊》之三 《巖壑幽居圖》 (紙本設(shè)色,24cm×28cm),書法一樣的線條給人以悅動飛舞的感覺,題款顯然多余。從字體上看,篆、隸、楷、行草皆備,作為畫中有機的一部分,又幾乎不可省移,這正體現(xiàn)了石濤高明的藝術(shù)境界。
李驎受石濤所托而作 《大滌子傳》[3]一文載:
“所作畫皆用作字法布置,或從行草,或從篆隸,疏密各有其體。”

《巖壑幽居圖》出自 《為禹老道兄作山水冊》紐約 王季遷家藏

《西園雅圖集圖卷》題跋 上海博物館

《黃山游蹤冊》之二 題款 北京故宮博物院

《初至一枝閣書畫卷》題款 上海博物館藏
如此而言,石濤是以字法中參悟畫法,或以前述作 “兩端” “一體”論,實際上他完成了引書入畫的過程。我們不能牽強附會,說石濤某某題款與繪畫主體內(nèi)容多么一致,但這種無論哪種書體、哪種風(fēng)格總給人以恰到好處的感覺恰當(dāng)卻是實在的。下面試看幾種類型:
風(fēng)格多樣的楷書。一類盡得鐘、王小楷之法,如現(xiàn)藏上海博物館的 《西園雅集圖卷》 (虉本設(shè)色,36.5cm×328cm),石濤全文抄寫米芾 《西園雅集圖記》于卷后,因畫卷中雅集人物古雅率意自然,所以款字用鐘、王厚重拙樸一路,使畫的意境顯得更加幽靜,與其時其境頗為相合。這類書體大概是石濤上追晉魏的直接表現(xiàn)。另一類頗合點畫疏朗秀麗的倪瓚楷法,以現(xiàn)藏北京故宮博物院的 《黃山游蹤》冊 (虉本水墨,33.5cm×23.7cm)為典型,該冊題款完全脫胎于倪瓚,正如石濤自言:
“倪高士畫如浪沙溪石,隨轉(zhuǎn)隨立,出于自然,而一段空靈清潤之氣,冷冷逼人,后世徒摹其枯索寒儉處,此畫之所以無遠(yuǎn)神也。”[4]
還有一類字形較大的楷書,頗具顏體寬博厚重的精神氣象,如現(xiàn)藏上海博物館的 《初至一枝閣書畫》卷 (紙本水墨,29cm×350cm)題款,筆畫剛勁,結(jié)體寬博,斬釘截鐵,十分穩(wěn)健。據(jù) 《大滌子傳》載,石濤早年“尤喜顏魯公”,可見這一學(xué)書經(jīng)歷對他的影響。
書寫意味較強的隸書。石濤很多重要作品的標(biāo)題都以隸書或篆書題款為主,字?jǐn)?shù)不多。前文提到 《巢湖圖》,題有兩段隸書長款,他的隸書受到當(dāng)時隸書家鄭簠的影響,而古樸厚重稍顯不足,所以徐利明先生說其 “頗近簡牘趣味”。[5]而佳士得公司所藏 《祝允明詩意冊》之二 《桃花源》 (紙本水墨,27.3cm×20.3cm)隸書款,似取法于晚明 《方氏墨譜》一類用隸書書寫的文字說明中的字體,[6]說明晚明隸書也對石濤產(chǎn)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雖然明末清初碑學(xué)思想尚屬發(fā)蒙,但敏銳的石濤還是抓住并有所表現(xiàn),是比較可貴的。

《巢湖圖》題款 天津博物館

《桃花源》出自 《祝允明詩意冊》佳士得公司

《方氏墨譜 序》出自 《傅山的世界》
融合各家的行草書。一類尚存蘇軾遺法,側(cè)筆取勢、扁平肥重,如現(xiàn)藏上海博物館的 《山水人物花卉冊》之 《漁翁》 (紙本水墨,24.5cm×38cm)。石濤曾說:“是年三十矣,得古人法帖縱觀之,于東坡丑字,法有所悟。遂棄董不學(xué)。” (《大滌子傳》),可見蘇字給了他多么大的啟發(fā),關(guān)于東坡丑字,下文還要述及。董書雖然遭棄,但早年學(xué)董的痕跡大概從稍微秀麗的風(fēng)格中還能感覺到。另一類,與王鐸的用筆和用墨特點相合,如筆畫聯(lián)屬、大膽運用漲墨法等,使人有痛快淋漓之感。如 《漁翁》落款三行中, “水” “際”等字的漲墨,與水汽濛濛的湖面相合。漲墨法的運用,尤其在行草書、楷書中為多,實際上這已經(jīng)逐漸顯示出石濤的膽識與藝術(shù)風(fēng)格。
融合了隸、楷、行草的真正屬于石濤的自家書體。這種書體,充分展示了石濤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力,并且對后來的揚州八怪都產(chǎn)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如現(xiàn)藏波士頓美術(shù)館的 《為劉石頭作山水冊》 (紙本設(shè)色,47.5cm×31.3cm),其一 《春風(fēng)吹月起》,題款字體糅合了楷、隸、行、草多種書體,開張大氣,用筆方圓結(jié)合,體勢比較平緩,款字大小參差錯落,行間距幾乎化為零,真如 “大珠小珠落玉盤”,憨拙中又透著靈巧。同冊中第十二幅 《山徑漫步》款曰:“此道見地透脫,只須放筆直掃,千巖萬壑,縱目一覽,望之若驚雷奔云。屯屯自起,荊關(guān)耶,董巨耶,倪黃耶,沈趙耶,誰與安名,余常見諸諸名家動轍仿某家,法某派。書與畫,天生自有一人職掌一代之事,從何處說起。”傲氣十足的石濤是多么的自信。他還曾在題款中稱: “畫有南北宗,書有二王法。張融有言:不恨臣無二王法,恨二王無臣法,今問南北宗,我宗耶?宗我耶?一時捧腹曰:我自用我法。” (《山水花卉八開》之八)石濤的 “我法”,是在學(xué)習(xí)傳統(tǒng)后自創(chuàng)的新法。我們都知道其后的鄭板橋創(chuàng)六分半書,實取法于石濤 (參現(xiàn)藏普林斯頓大學(xué)美術(shù)館藏 《人物花卉冊》之四 《芙蓉》題款)。

《漁翁》出自 《山水人物花卉冊》上海博物館
這一類的字體,在用筆上隨意而又頗富想象力,或藏或露,或粗或細(xì),或連或斷,在結(jié)體上十分自由但又不失法度;或大或小,或松或緊,或開或合,或正或斜,或扁或長,或方或圓,在章法上一如其畫灑脫自如;或疏或密,或齊或缺,尤其是依照畫面主體構(gòu)圖而作自然的伸縮與變形,極富浪漫情調(diào)。 “將人性化了的自然風(fēng)采中的神韻化入其書,這種書法情境是明季、清初文人書畫家的新創(chuàng)造,有其重要的風(fēng)格學(xué)價值和風(fēng)格史的意義。”[7]我想這個定位并不夸張。

《春風(fēng)吹月起》題款 出自 《為劉石頭作山水冊》 波士頓美術(shù)館

《山徑漫步》題款 出自 《為劉石頭作山水冊》波士頓美術(shù)館

《芙蓉》出自 《人物花卉冊》普林斯頓大學(xué)美術(shù)館藏
其實,石濤的繪畫與書法相互滲透,融為一體,題款已不是獨立的一部分。上面就石濤的書體所言僅僅就事論事,實際上無法把石濤的書法與畫作分開來講。因為石濤不僅以題款的形式參與到構(gòu)圖中,其書法的用筆和構(gòu)字方式也影響到其繪畫的線條和布局。再看題款詩詞的意境,契合完美得令人驚嘆。如現(xiàn)藏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十開 《金陵十景冊》 (紙本水墨,30.8cm×21.2cm),其一 《紫氣滿鐘山》,畫面中枯筆勾勒一山脊斜貫上部,而題款亦依其勢,作傾斜狀,行間寬窄全不在意,疏密自然,端詳之中覺得恰如眼前的山梁,上部傾斜的字緣像是一排茂密的松樹,而下部松松散散的字跡,如同松濤陣陣的松林,正襯托出遠(yuǎn)處紫氣中的山脊,令人驚嘆不已。而同冊中的另外一幅題為 《傷心玄武湖》,構(gòu)圖平緩,湖面中的小嶼與幾條幾乎看不出移動的小船,顯得湖面靜而重,題字下方是對岸緩緩的山,以短短的淡墨寫出,不施皴擦,題字便也采用柔軟纏繞的筆法,濃墨兼以枯筆,緩緩寫來,連綿不絕,真似一片陰云覆蓋在空中,使人心情凝重了。
二、注重筆墨情趣
石濤繪畫的風(fēng)格和題款書法的風(fēng)格往往十分契合,表現(xiàn)出相同的筆墨情趣。石濤 《畫語錄》中專辟 “筆墨”一章:

《紫氣滿鐘山》出自 《金陵十景冊》 北京故宮博物院

《傷心玄武湖》出自 《金陵十景冊》 北京故宮博物院

《山溪石橋》題款 出自 《為劉石頭作山水冊》波士頓美術(shù)館

《花卉冊》之三 上海博物館
古之人有有筆有墨者,亦有有筆無墨者,亦有有墨無筆者……山川萬物之具體,有反有正,有偏有側(cè),有聚有散,有近有遠(yuǎn),有內(nèi)有外,有虛有實,有斷有連,有層次,有剝落,有豐致,有飄緲,此生活之大端也……茍非其然,焉能使筆墨之下,有胎有骨,有開有合,有體有用,有形有勢,有拱有立,有蹲跳,有潛伏,有沖霄,有崱屴,有磅礴,有嵯峨,有巑岏,有奇峭,有險峻,一一盡其靈而足其神。
石濤認(rèn)為描繪這各具情態(tài)的自然萬物,要靠筆所描繪出的線來表現(xiàn)客觀形象,同時要靠墨的揮灑來渲染氣氛,筆與墨亦當(dāng)千變?nèi)f化。這里強調(diào)的是充分發(fā)揮筆墨描繪客觀對象的功能,二者要恰到好處,否則便是有筆無墨、有墨無筆,不能充分表現(xiàn)審美對象的內(nèi)在生命力。前面提到石濤 《為劉石頭作山水冊》其五 《山溪石橋》,款曰:“丘壑自然之理,筆墨遇景逢緣,以意藏鋒,轉(zhuǎn)折收來,解趣無邊。”正是他所謂 “所作畫皆用作字法”,他在描繪對象時極盡各種筆法,包括題款的字跡也要變化多端,使二者渾然成為一體。又如現(xiàn)藏上海博物館的十二開 《花卉冊》 (紙本設(shè)色,31.2cm×20.4cm),描繪了桃花、芍藥等十二種花卉菜蔬,用較為豪放的沒骨寫意法,間以水墨雙鉤,尤其是題款書法,有行楷,亦有行草,并大膽使用漲墨法,我們看到畫面上畫如字法,字亦同畫,濃淡干濕,一任自然,顯得水墨淋漓,色墨交融,奔放灑脫的筆墨之中顯出高雅的風(fēng)格。“漲墨”,石濤謂之 “誤墨”,題 《潑墨菊花》:“昔人作畫善用誤墨,誤者無心,所謂天然也。生煙嚙葉,似菊非菊,以為誤不可,以為不誤又不可。”誤墨在他的各種書體中都有運用,在畫面上更是駕輕就熟,可見石濤于此頗為會意。石濤還十分重視題款中的淡墨與枯筆。這些方法的靈活運用,一方面使墨色豐富多彩,另一個方面可以使畫面達(dá)到高度的和諧與統(tǒng)一。

《丑墨丑山》出自 《山水十開》之八
三、審美取向獨特
據(jù)《大滌子傳》:“嗟乎,古之所謂詩若文者創(chuàng)自我也,今之所謂詩若文者剽賊而已!其于書畫亦然。不能自出己意,動輒規(guī)模前之能者,此庸碌人所為耳,而奇士必不然也。然奇士世不一見也。予素奇大滌子,而大滌子亦知予,欲以其生平托予傳。”李驎接受石濤的委托,一因其 “奇”。文中描述石濤學(xué)書不甚喜董,疑因離其未遠(yuǎn),盡是流行時趣,想必與石濤的審美取向和超然個性有所不合,所以后文又曰:
得古人法帖,縱觀之,于東坡 “丑”字,法有所悟,遂棄董不學(xué),冥心屏慮,上溯晉魏,以至秦漢,與古為徒。
東坡所謂 “丑”,來自稱頌文同的梅竹石圖:“梅寒而秀,竹瘦而壽,石文而丑。”此 “石文”,乃 “石紋”,指石表的皺折紋理, “丑”字實形容其飽含滄桑歲月的印痕,那是一種清雅的高級審美情趣。石濤于此 “法”有所悟,這個 “法”字在他的 《畫語錄》中反復(fù)講到,歷來研究石濤畫論者各抒己見。我以為來自于對“高古”[8]意蘊的審美追求,石濤 《與吳山人論印章》詩:“書畫圖章本一律,精雄老丑貴傳神。”視 “丑”與“老”并列作為傳神的手段。上海博物館藏十開 《山水》 (紙本水墨,26.5cm×33.2cm)之八題款: “丑墨丑山揮丑樹,不知多向好人家。”同樣提到 “丑”字,畫面上的山、樹用濃墨、誤墨為之,則是一種敢于突破常規(guī)的美。從近處講,其正來自于傅山 “四寧四勿”的觀念,傅山是求 “奇”最為激進(jìn)的藝術(shù)家,[9]而李驎亦稱石濤為“世不一見”的奇士,二人前后相差未遠(yuǎn),傅青主高風(fēng)亮節(jié)誓不仕清,石濤為明宗師后裔,亦懷前朝,他對傅山某種程度上的認(rèn)同應(yīng)很自然。當(dāng)然,石濤是以 “上溯晉魏,以至秦漢”為落腳點,里面隱含的是對自然樸拙之意的心領(lǐng)神會,而 “皆自出己意為之,神到筆隨,與古人不謀而合者也。” (《大滌子傳》)這是一位有開創(chuàng)之功的書畫家的獨到之處。
注釋:
[1]吳冠中.《我看書法》,見邱振中 《書法與繪畫的相關(guān)性》,北京: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11.293.
[2]楊成寅.《石濤》,北京: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9.155.圖版。
[3](清)李驎.《虬峰文集》卷一十六,62-65頁,見 《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131,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本文引用 《大滌子傳》皆本此。
[4]俞劍華.《中國古代畫論類編》,北京: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2007.164.
[5]徐利明.《中國書法風(fēng)格史》,北京: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2009.288.
[6]白謙慎.《傅山的世界》,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9.231.
[7]徐利明.《中國書法風(fēng)格史》,北京: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2009.288.
[8]《大滌子傳》:“書畫皆以高古為骨,間以北苑、南宮,淹潤濟之,而蘭菊梅竹尤有獨得之妙。”
[9]白謙慎.《傅山的世界》,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9.4.